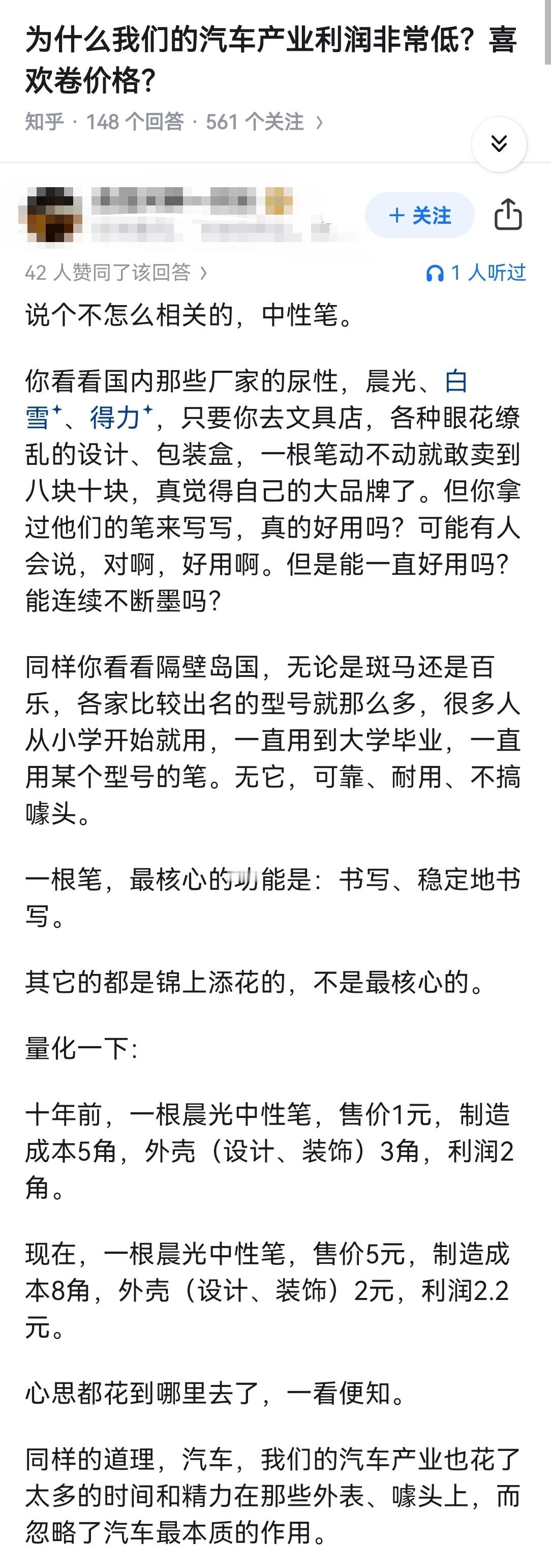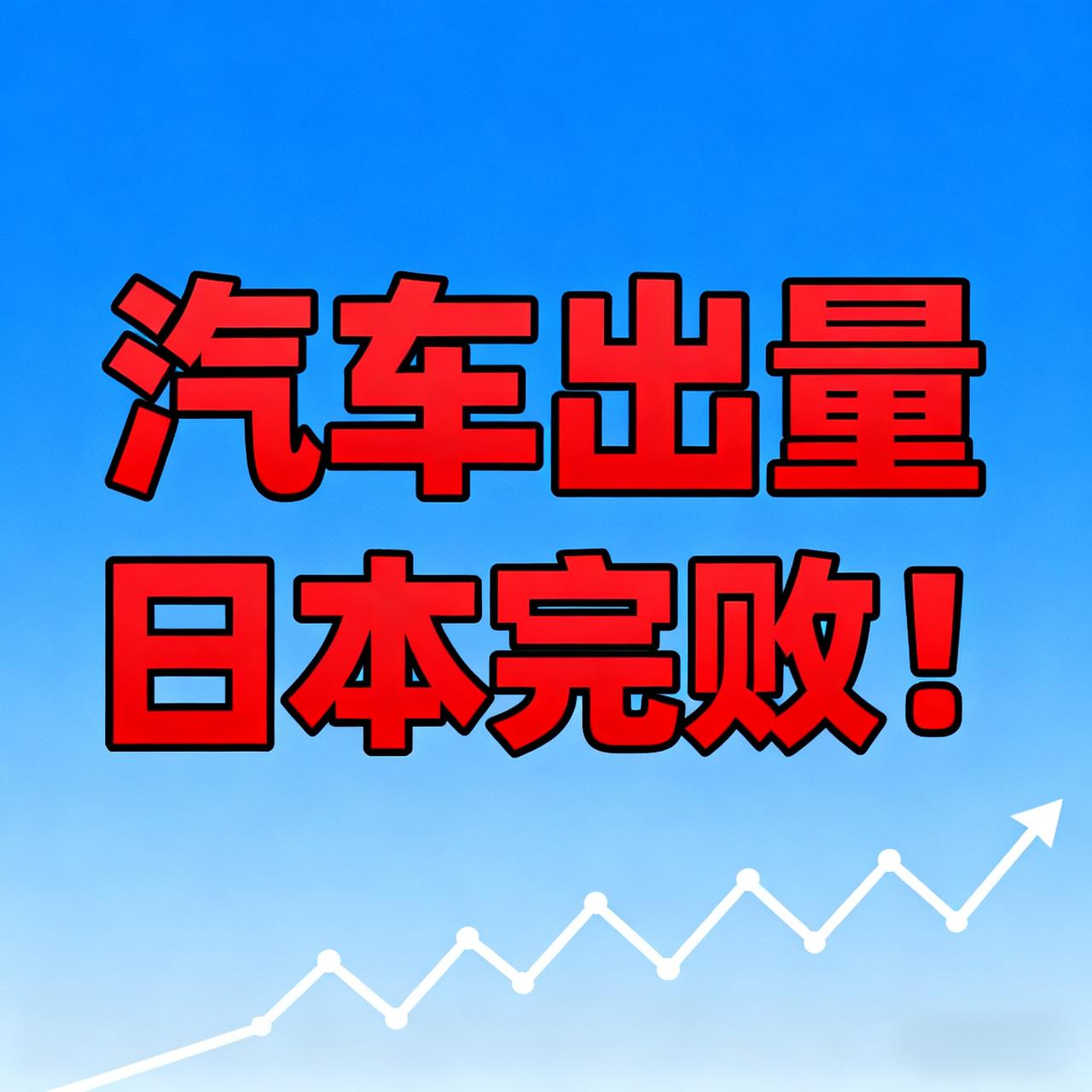"宁死不向中国低头!”6年前,一日企表示就是死,也不会向中国市场低头,随后便以1块的价格,把50%股份卖给了长安,就这样退出了中国市场,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现在怎样了? 2025 年印度新德里车展,铃木 Suzuki eVX 展台前冷冷清清。 不远处比亚迪 Atto 3 被围得水泄不通,而这款铃木纯电车,续航不足 400 公里。 六年前铃木决绝退出中国时,绝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新能源赛道陷入如此窘境。 这窘境的根源,或许要从铃木前社长铃木修的创业经历说起。 1963 年,29 岁的铃木修进入铃木汽车,从基层销售员做起。 当时铃木主打小型摩托车,在日本市场份额不足 5%,濒临淘汰。 铃木修骑着摩托车跑遍日本乡镇,发现 “百姓需要便宜耐用的代步工具”。 他向社长建议转型小型汽车,顶着 “不务正业” 的质疑,推动研发 Suzuki Fronte。 这款车售价仅 38 万日元,比同级车低 20%,上市即热销,奠定铃木小型车基因。 1983 年铃木修升任社长,更是将 “小型车战略” 刻进铃木骨子里。 他提出 “让每个家庭都买得起汽车”,主导推出铃木 Alto,排量仅 0.8L,油耗极低。 在他看来,“小型车是最符合大众需求的产品,无需追逐大尺寸潮流”。 这种执念,影响了铃木此后半个世纪的产品路线,包括进入中国市场的选择。 时间回到 2018 年 6 月,长安铃木 “1 元转让 50% 股权” 的公告震惊车圈。 重庆工厂里,最后一辆奥拓下线后,生产线的灯光被逐一熄灭。 这款曾年销 20 万辆的 “国民神车”,正是铃木修小型车战略在中国的缩影。 当时铃木高层对外宣称 “聚焦优势市场”,实则延续着铃木修的固有思路。 2017 年长安铃木销量仅 11.3 万辆,较 2011 年巅峰暴跌 70%,份额不足 0.5%。 其实早在 2015 年,铃木的危机就已埋下伏笔。 那年中国 SUV 市场增速达 45%,哈弗 H6 月销突破 3 万辆,而铃木无一款主流 SUV。 消费者开始追求大空间、智能互联,雨燕的 “灵动操控” 不再是卖点。 长安汽车曾多次提议联合研发紧凑型 SUV,均被铃木以 “偏离小型车战略” 拒绝。 这拒绝的背后,是铃木修时代形成的 “小型车即核心” 的思维定式。 2016 年是铃木扭转命运的最后机会,可惜它选择了放弃。 长安提出共同开发新能源车型,共享三电技术,铃木却担心 “技术外泄”。 彼时中国已出台新能源补贴政策,蔚来、小鹏等新势力也开始布局。 铃木高层仍秉持铃木修 “燃油车技术最可靠” 的理念,坚持加码燃油小型车。 这一年,长安铃木新能源车型研发计划彻底搁置,与中国市场渐行渐远。 铃木修在任期间,曾让铃木靠小型车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 1998 年他推动铃木进入印度,与马鲁蒂合作推出小型车,迅速垄断市场。 2005 年铃木在印度市场份额突破 50%,成当地 “国民汽车品牌”。 这种成功让铃木修更加坚信 “小型车战略放之四海而皆准”,无需调整。 也正是这种成功,让后续管理层在面对中国市场变化时,难以跳出固有框架。 退出中国后,铃木将所有资源投入印度、东南亚市场。 在印度,马鲁蒂铃木推出 Alto 800,延续铃木修时代的低价策略,以 2.5 万人民币抢占市场。 2024 年,其印度市场份额达 41%,几乎垄断小型车领域,看似重回巅峰。 在东南亚,铃木的小型商用车凭借低成本优势,成当地中小企业首选。 2024 年泰国、印尼市场份额分别达 8.2% 和 7.5%,短期收获颇丰。 但这种 “红利依赖” 很快显露出弊端,技术迭代彻底停滞。 在印度的五年里,铃木未推出一款全新技术平台,仅对老车型做小改款。 这与铃木修时代 “靠技术优化降成本” 的思路不同,如今只剩简单模仿。 如今的铃木,正陷入两难境地。 铃木修时代的小型车战略曾让它辉煌,却也成了如今转型的枷锁。 在印度、东南亚,新能源转型滞后,面临比亚迪、特斯拉的挤压。 想重返中国市场,却发现技术差距已拉大,中国车市新能源占比超 30%。 回望铃木的六年历程,铃木修的创业经历既是荣光,也是羁绊。 他奠定的小型车基因让铃木崛起,却也让后续管理层固守成规。 固守既有优势,忽视市场变化,再好的品牌也会被时代抛弃。 而中国车市的快速迭代,也证明了 “顺势而为” 才是生存之道。 未来,若铃木仍无法突破铃木修时代的战略束缚,其在新兴市场的优势,或许也将成为过往。 信源:第一财经——铃木汽车前社长铃木修去世,曾缔造日本小型车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