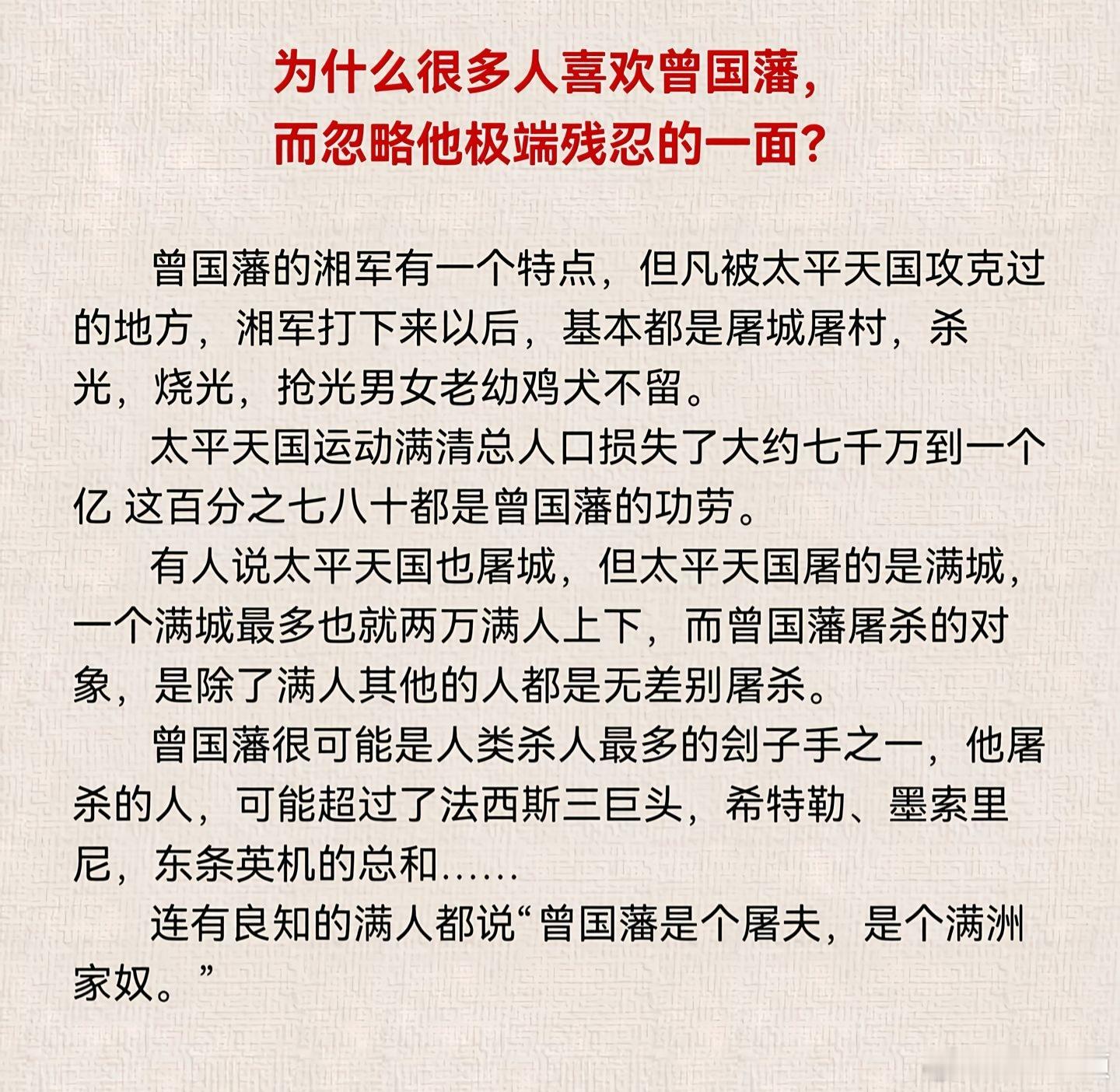1923年,61岁的曹锟强娶19岁少女刘凤威。面对可以当爷爷的丈夫,刘凤威是万般不情愿。谁料,卦师一句话,她对曹锟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1923年的保定,寒风卷着雪沫子打在曹家大院的朱漆大门上,门环冻得发僵。门房老赵揣着怀炉刚走到二门口,就被曹锟的副官拦住。 内宅暖阁里,曹锟正对着铜炉烤手,见老赵进来,把一张洒金红纸往桌上一拍,纸角被炭火烤得微微发卷:“再去趟刘家,把那姑娘的八字核仔细了,时辰、属相,半点不能错。” 老赵弯腰去看,红纸上“刘凤威”三个字写得秀气,底下“癸亥年九月初七卯时”一行小字,刺得他眼仁发疼——总统今年六十一,属虎;这姑娘十九,属猪,差着两轮还多,说句不好听的,当爷爷都绰绰有余。 “是。”老赵不敢多嘴,揣着红纸往城南赶。雪片子越下越大,落在他的毡帽上,没一会儿就积了层白。 此时的刘凤威正在自家针线铺里,帮母亲绕缠线板。她穿着件月白布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灵巧地转着线轴,棉线在木板上绕出整齐的圈。窗台上摆着盆腊梅,刚绽开两朵,香得清冽。 “凤威,歇会儿喝口热水。”母亲把茶碗往柜台上推,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汽车“突突”的响声,在这全是马车、洋车的老街里,格外扎眼。 两个穿军装的副官掀开车帘,军靴踩在积雪里“咯吱”响。为首的那个敬了个礼,语气却带着不容分说的硬气:“刘小姐,总统请您去府里听戏,车备好了。” 刘凤威手里的线轴“啪”地掉在地上,棉线散了一地。她听说过曹锟——那个靠着枪杆子当上大总统的人,报纸上的照片看着满脸横肉,怎么会突然请她去听戏? “我不去。”她往后缩了缩,攥着母亲的衣角,指尖冰凉。 副官却笑了,笑得不阴不阳:“小姐别为难我们。总统说了,去不去,可不是您说了算。” 被塞进汽车时,刘凤威的棉袄沾了雪,冻得她直打颤。车窗蒙着水汽,看不清外面的街景,只听见引擎轰鸣,像要把人往不知名的地方拖。 曹家大院的戏楼里,锣鼓已经敲了三通。曹锟穿着锦缎袍子,坐在前排太师椅上,见刘凤威被带进来,眯着眼上下打量,像在看件刚到手的宝贝:“丫头别怕,来,坐这儿。” 刘凤威没动,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她瞥见戏台上正演《穆桂英挂帅》,穆桂英的翎子甩得威风,可她只觉得满眼都是晃眼的红,刺得人想哭。 散戏后,曹锟的姨太太把刘凤威领到后院佛堂,说是“请卦师给合合婚”。卦师穿着蓝布道袍,捧着罗盘转了三圈,又捏着两人的八字排了半天,突然对着刘凤威作揖:“姑娘好福气!您这八字,正合总统的命格,是天定的旺夫相,将来必能富贵双全,子孙满堂。” 刘凤威猛地抬头。她爹早逝,母亲拉扯她和弟弟不容易,针线铺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弟弟冬天还穿着单鞋。卦师的话像根针,刺破了她心里的不情愿——富贵双全?是不是意味着母亲不用再熬夜做针线,弟弟能穿上棉鞋? “你再说一遍。”她的声音发颤。 卦师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说得斩钉截铁:“姑娘放心,这是天意。” 从佛堂出来,刘凤威看着院里的积雪,突然不抖了。曹锟派人送来的狐裘大衣裹在身上,暖得让人发困。她想起母亲鬓角的白发,想起弟弟冻裂的脚后跟,咬了咬嘴唇。 三日后,曹家大院挂起了红灯笼。刘凤威穿着红嫁衣,坐在镜前,看着镜中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没哭,也没笑。有人给她戴上凤冠,珠翠压得头皮发麻,她却觉得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送亲的队伍走过城南老街时,刘凤威撩开轿帘,看见自家针线铺的门开着,母亲正站在门口抹眼泪,弟弟举着她新做的棉鞋,对着轿子的方向挥手。 雪还在下,把街景染成一片白。刘凤威放下轿帘,指尖抚过嫁衣上的金线——不管卦师的话是真是假,她知道,从今天起,日子该换个过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