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得了癌症,亲大哥一面没露,电话也没有,最后却收到一个大信封。 前两天同事老李生病住院了,我前去探望。 老李躺在白得刺眼的床单上,眼含热泪轻声哽咽着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儿女双全,儿女都出息,工作也赶上了好时候,退休后待遇也不错,就是有件事让我死不瞑目。” 我握着他的手问道:“老李,别想太多了,你这个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你怎么如此消极了?” 他抹了一把泪说:“我老家还有个哥哥,可是年轻时发生了矛盾,多年都不来往了,我就这一个大哥,我不想到了那边没法跟父母交代。” 我正要再次宽慰他的时候,突然门被推开了。是一位年轻的护士,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有些褶皱。 护士说:“李大爷,有一个自称是您老家亲戚的老人,看着与您长得有几分相像的模样,让我给您的。” 老李一下子激动了起来,赶紧接过信封,打开一看是大大小小票子攒起来的5万元钱。 老李哇的一下子就泪流满面了,或许他已经知道了那个人是谁了。 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急忙说道:“快,帮我把人叫回来。眉骨上有道疤痕。” 十五分钟后,我找到了老李口中的大哥。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一开始他犹豫不决,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最后犹豫再三才跟着我进了医院。 门被推开时,带进一股走廊消毒水味儿。然后是脚步声,沉、缓,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拖沓。 只见老李费力地偏过头,看见了那张脸。或许比记忆里黑了,皱得像老核桃,但眉骨上那道疤还在。 其实,哥哥李建国就站在了医院门口,手里拎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兄弟两人对视了足足半分钟,谁也没说话。 最后是哥哥先动,他走到床前,声音粗嘎,像砂纸磨过木头,“弟,这5万你拿着,我没太多,卖了两头猪,加上棺材本儿。” 老李喉咙发紧,想说什么,却先咳起来。哥哥笨拙地倒了杯水,递过去时手有点抖。水温刚好,是李明习惯的、不烫不凉的温度。 “还记得吗?”老李喘匀了气,“咱爹那三间瓦房。” 那是他们闹掰的根源。父母走后,为那三间漏雨的破房,两个刚成家的兄弟吵翻了天。 老李觉得哥哥是长子该让,哥哥李建国觉得弟弟读了书心就野了。最后房卖了,钱平分,两人三十年没说过话。 “记得。”李建国在凳子上坐下,摸出旱烟,又想起是在医院,讪讪地收回去,“房梁是咱俩一起换的,你当时在底下扶梯子,吓得腿哆嗦。” “你还笑我。” “后来你考上师范,我卖了半扇猪给你凑学费。” 这话像把钥匙,突然打开了锈死的锁。 老李想起那个夏天,哥哥推着自行车送他去车站,车把上挂着个网兜,里面是煮熟的鸡蛋。他上车时,哥哥塞给他一卷毛票,汗湿的。 “哥……”老李张了张嘴,后面的话被涌上的哽咽堵住了。 大哥李建国摆摆手,从包袱里又掏出个铁皮盒子,打开,是几块硬邦邦的芝麻糖。“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他掰了一小块,递过去。 糖在嘴里化开,甜里带着芝麻的焦香,还有股淡淡的铁锈味。老李慢慢嚼着,眼泪就这么无声地滚下来,渗进鬓角花白的头发里。 大哥李建国别过脸去,望着窗外。良久,他说:“老二,咱不吵了。没意思。” “嗯,不吵了。”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挨得很近,像小时候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时那样。 两个走过大半辈子的老人一个躺着,一个坐着,手不知什么时候握在了一起。 窗外,梧桐树的影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叶子已经黄了大半,但还有几片固执地绿着,在秋阳下亮得像翡翠。 《诗经·小雅》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兄弟间的争执如同在自家围墙内的摩擦,而当真正的危难如疾病从外部降临时,血缘深处的情感便会超越往日的嫌隙,重新联结。 苏轼在《水调歌头》中感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兄弟数十年的疏离,是生命中无法回避的“缺憾”。然而,正是这种长久的缺憾,让晚年的和解显得格外珍贵与完整。 亲情的纽带或许会被岁月拧成死结,却很少会被真正割断。 最终你会发现,有一个深刻的生命真相:时间与死亡,是最伟大的调解者。 当生命的终点依稀可见,往日的得失对错会突然失去重量,唯有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牵挂与不舍,会浮出水面,成为照亮最后旅程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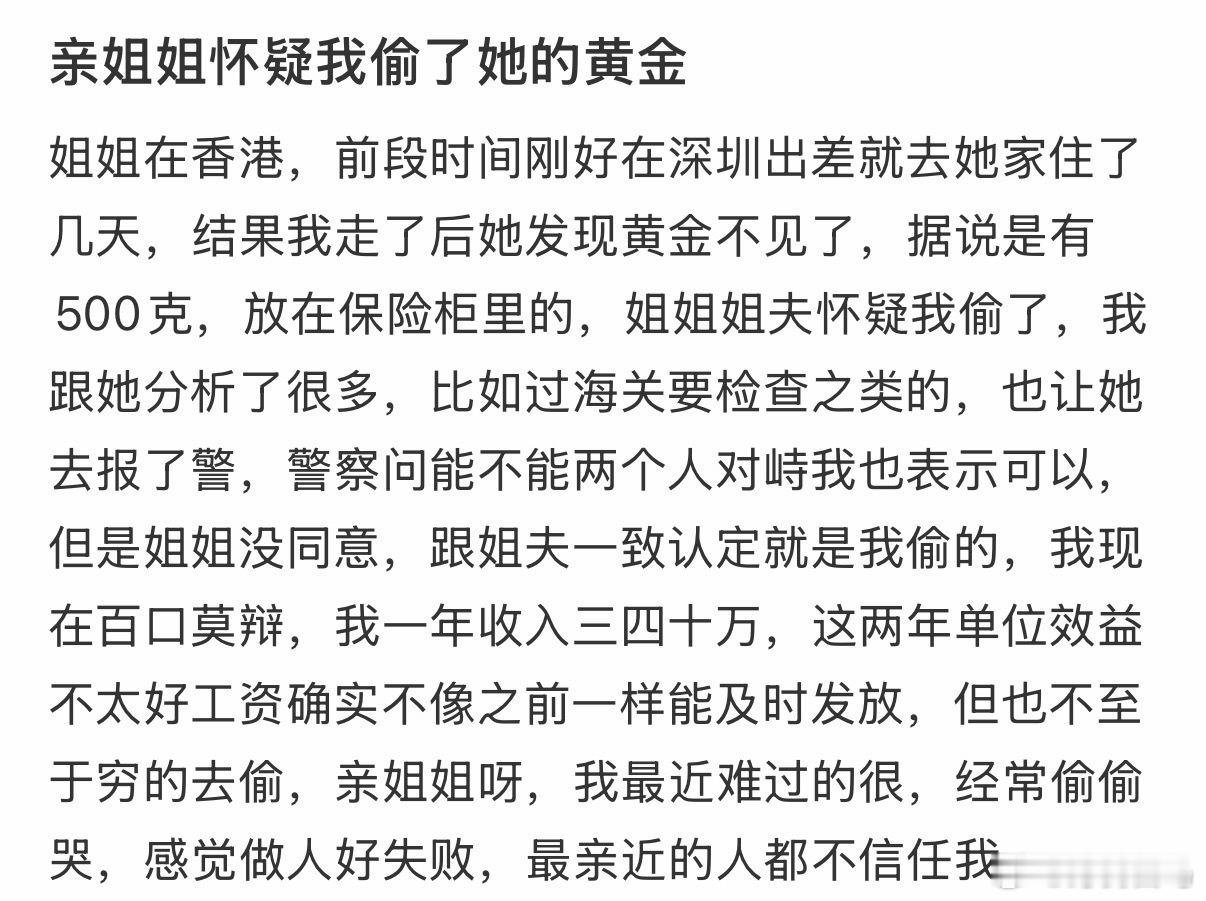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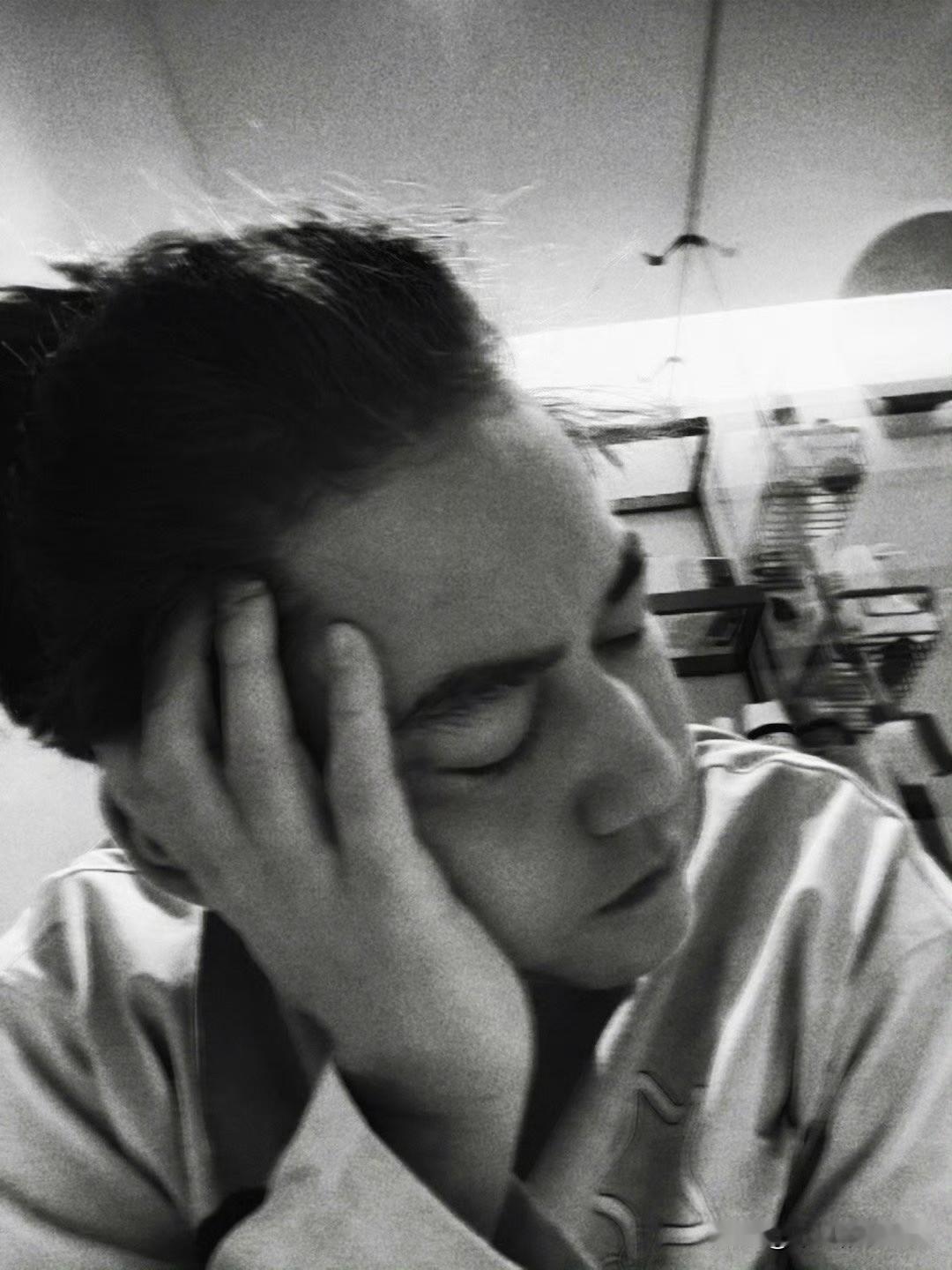
![大哥好执着啊这份爱都能感天动地[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9454701724161150490.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