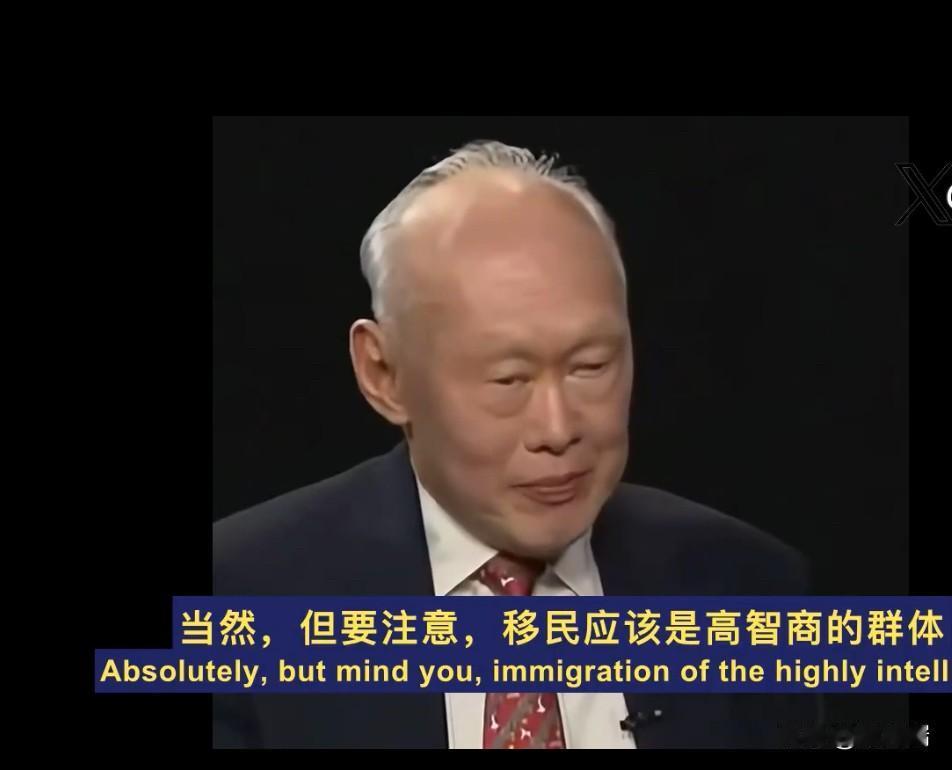“李光耀谈到治理贪腐,李光耀说:这个很容易,你一个官员拥有工资之外的巨额财富,这就是贪污来的,你解释不了,就抓你。”一句话,把新加坡反贪的路数捅开:少讲空话,多看账本。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成为一种社会基因,根深蒂固地侵入这片弹丸之地的每一个毛孔。 日本占领时期,高通胀和低收入迫使新加坡民众普遍用行贿换取生存权,而战后英国统治时期,行政管理毫无公开透明可言。 当时的新加坡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公务人员收入低,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 贪污调查局虽然在1952年就已成立,但直至1959年英国人离开新加坡,这个机构几乎无所作为。 李光耀剖析其中缘由,主要有二端:其一,贪污调查局所需资源匮乏;其二,该机构未获法律赋予的权力。如此情形,亟待改善。 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后,李光耀迅即磨砺“双锋利刃”:一方面大力完善并强化法律体系,另一方面精准调整贪污调查局的职能定位,以雷霆之势推动国家治理。 往昔,贪污调查局虽为独立机构,然于调查政府官员之际,因权限匮乏,常遇重重阻挠。诸多举报线索,亦在波折中渐渐湮灭,终至无果而终。 在法律完善进程中,李光耀强化了打击贪腐相关条款的力度,为贪污调查局提供坚实法律支撑,让法律在惩治贪腐上更具效力,营造更廉洁的社会环境。 备受瞩目的“有罪推定”法律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引人关注,它明确指出,“异常财富”可作为指控证据,那些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财产,将被视作贪污所得。 新加坡高级外交官韦尔盖塞·马修斯阐释道:若身为月薪500新元的公务员,却开宝马、让妻子驾奔驰,还坐拥价值500万新元的宅邸,就必须明晰交代财产来源。若说不清,财产充公,且会受法律严惩。 根据新加坡《防止贪污法》,贪污调查局被赋予了特别调查权力,可以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买账户、报销单据或任何其他账目。 更关键的是,法律授权该局有权要求被调查人详细说明其子女家属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每项财产的获得途径与准确日期。 贪污调查局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它可以不需要逮捕证而逮捕违法犯罪的嫌疑人,或检查被调查的人的银行账户和保险柜。 对于财产来源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多余”部分,无须再找证据,就可以确证而受到指控。 李光耀在1985年提出要消灭官员贪污的动机,并为此出台一系列政策,1989年和1994年,新加坡对公务员薪资进行大幅度上调。 在新加坡,高薪常与严管并行。《公务员指导手册》明确规定,政府官员外借资金不得收取利息,向他人借款时,亦不可凭借自身职务进行各类交易,以此规范官员行为。 官员收受的礼品要一律上交,若要留作纪念,可由专人估价后自己出钱买下,收受红包或礼品超过80新元就属违法,政府官员严禁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 高薪养廉的目的在于排除贪腐的需要,让公务员不必为生计所迫而走上贪腐之路,这种思路与严厉的反腐法律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反腐体系。 新加坡治贪的严厉程度,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上,更体现在对违法者的严厉惩处上,贪腐者不仅会倾家荡产,还会身败名裂。 1991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因贪污罪名成立,被判处1.7万新元罚款和1天监禁,尽管监禁时间只有一天,但这足以让他失去工作,失去全部养老金。 据新加坡媒体消息,往昔居于别墅、坐拥私人泳池的格林奈,一朝获刑,时光流转,直至2009年,他仍栖身于出租房内,境遇之变令人唏嘘。 1986年,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因被指控收取两笔各50万新元的贿赂而接受调查,尽管他是李光耀的多年老友,但李光耀并未干涉调查过程。 此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立了严格的品格考核制度,除了考录前的品德调查之外,被录用后的公务员还要接受政府经常性的品德考核。 每位公务员在受聘之际,需填写财产清单,前往法院设立的公证处接受审查,且须由指定的宣誓官签字确认,以确保程序规范、责任明确。 公证处的正式文本交由工作人员所属部门的人事机关保存,副本保存在法院公证处。 此后的每年7月1日,公务员必须填写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申报内容包括自己所拥有的股票、房地产、存款和其他方面所获得的利息收入等,还包括配偶和依靠他抚养的子女名下的产业和投资。 李光耀曾用“面子问题”诠释郑章远之死:“郑章远宁可结束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 在新加坡反腐体系里,法律的高压线让贪腐从“高风险、低回报”的犯罪行为。 贪污调查局的权力至今仍在加强,最新版的《防止贪污法》授予调查人员检查银行账簿的特别权力。 而这一切,都起步于那个简单的理念——解释不清的财产,就是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