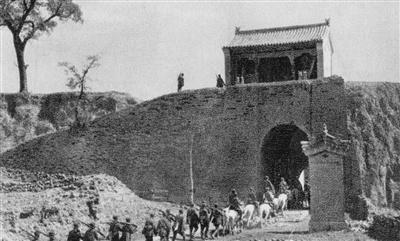在滕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没说一句话,而是举起了自己的枪,只听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阵地上先是静了一瞬,紧接着爆发出压抑的欢呼声——不是那种张扬的呐喊,是士兵们攥着枪杆、喉咙里挤出的激动声响,有人甚至忘了擦脸上的硝烟。王铭章盯着那匹失去主人的战马慌乱跑远,伸手拍了拍副官的肩膀,掌心能触到对方因握枪而紧绷的肌肉。 没人多说话,可所有人都明白这三枪的分量:龟尾寿三是日军主攻滕县的联队指挥官,此前几天,正是他带着部队一次次冲破外围阵地,用炮火轰塌了城墙上的多处垛口,不少兄弟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倒在血泊里。 那会儿的滕县早已是座孤城。王铭章率领的122师,大多是川军子弟,装备差得可怜——步枪多是老旧的“汉阳造”,子弹每人平均不到20发,重武器更是没几门。日军却带着坦克、重炮,白天用炮火犁地,晚上组织冲锋,城墙上的士兵往往刚补上去,就被新一轮轰炸掀翻。 龟尾寿三敢在一千多米外骑马督战,就是料定中方没有能精准打击的武器,这份嚣张像根刺,扎在每个守城将士心里。副官这三枪,不仅打掉了日军的指挥官,更戳破了对方的狂妄,让阵地上快被压垮的士气,一下子提了上来。 副官没炫耀枪法,只是把枪收起来,弯腰捡起刚才掉落的弹壳,仔细揣进兜里。他知道这不是逞能的时候,龟尾寿三一死,日军肯定会疯狂报复,接下来的进攻只会更猛烈。 果不其然,没过半个时辰,日军的炮火就铺天盖地砸过来,城墙缺口处的尘土被掀得像浓雾,碎石子砸在钢盔上“叮当”响。王铭章站在指挥部外的土坡上,望着被烟火笼罩的城墙,声音沙哑却坚定地对身边参谋说:“告诉各团,人在城在,就算剩最后一个人,也得把口子堵上。” 其实谁都清楚,滕县守不住。上级的援军还在百里之外,日军的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赶来,城里的粮食和弹药越用越少,连伤员都没地方安置,只能躺在城墙根下,稍微能动弹的,就拖着伤腿往阵地上送弹药。 可没人提撤退,川军子弟从四川跋山涉水来抗日,就是抱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念头,王铭章更是早就下了决心——他给家人写的绝笔信里,已经写明“誓与滕县共存亡”,这不是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 副官那三枪带来的士气,撑着将士们扛过了最艰难的两天。日军后来换了指挥官,攻势更狠,坦克直接撞向城门,城墙最终被撕开一道大口子。 王铭章带着卫队冲上去堵缺口,身上多处中弹,鲜血浸透了军装。他倒在城墙下时,还攥着望远镜,视线依然盯着日军进攻的方向。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没退后半步,就像他当初对士兵们说的那样,用生命守住了“人在城在”的承诺。 这场保卫战,122师几乎全军覆没,却为台儿庄战役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后来有人问起副官那三枪,他只说:“不是我枪法好,是军长(王铭章后追赠陆军上将)和兄弟们的骨气,给了我准头。” 这话没错,那三枪里藏着的,是中国军人面对侵略者时,宁死不屈的硬气——哪怕装备不如人、兵力不如人,也绝不低头,哪怕用生命作代价,也要让敌人知道,中国的土地,不是那么好踏的。 如今再想起滕县保卫战里的这一幕,想到的不只是三枪击毙敌酋的痛快,更是无数像王铭章、像那位副官一样的英烈,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家国”。这种精神,从来不是历史书页里的文字,而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传承,提醒着后来人,如今的和平,是用怎样的牺牲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