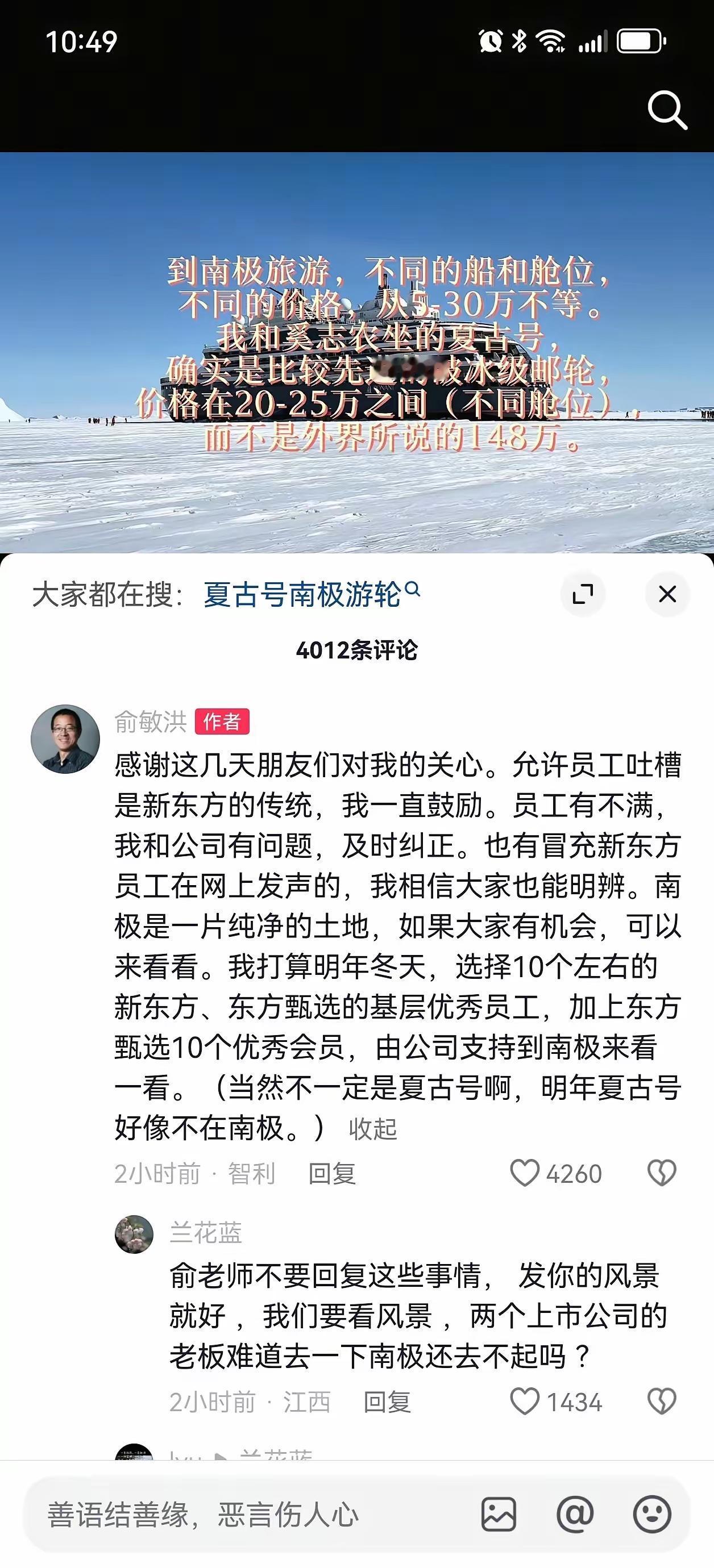温铁军的“中国工人不会再形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一判断,并非拍脑袋的情绪宣泄,而是建立在他对全球产业链、技术结构、空间布局、国家治理方式四重变迁的追踪之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几十年前,人们提起工人,总能想到热火朝天的车间、排列整齐的宿舍和一群群穿着蓝色工服的人,那时候,工人队伍庞大集中,身份标签清晰,大家干着类似的工作,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可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和技术进步,工人的世界悄然发生了变化。 现在,谁是“工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简单答案,工厂里调试机器人程序的技术员,外卖平台上的骑手,直播行业的助播,甚至远程写代码的工程师,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工人队伍里,这些人有的穿工服,有的穿骑手马甲,有的连工位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新职业、新工种不断涌现,身份的流动和多面性是当下最显著的特征,有些人在工厂上夜班,白天兼职送外卖,有人在制造业做数据分析,空余时间还做电商客服,就业方式灵活,工人不再是过去那种“一辈子只干一份活”的群体,身份背后有着复杂的交集。 不同工种、不同平台上的工人,利益诉求也不再一致,流水线计件工资让大家重视个人产出,外卖骑手的收入取决于抢到多少订单,算法分配让每个人都成了“对手”,订单有限,谁接多了谁就能多赚,工厂的普工们关心工资和加班,平台骑手关注单量和路程,远程技术员关注项目和绩效,利益的分化让大家很难出现共同发声的需求,平台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和固定岗位的工人之间也有不少隔阂,一些人从未进过工厂,只在手机上完成工作,线下见不到同事,大家习惯各自为战,遇到问题更愿意自己想办法,很少有组织起来的冲动,过去那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谊,正逐渐被个人忙碌所取代。 空间的分散也是工人之间距离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前的工厂往往和宿舍、社区连在一片,工人下班可以一起吃饭、聊天,生活圈子高度重合,现在,大量工厂搬到郊区、县城,产业园区里有成百上千家企业,但同一个车间的人都可能住在不同地方,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更是全城流动,今天送东城区,明天跑到西郊,路线变化随时调整,还有一些新职业者根本没有固定办公场所,靠网络在家上班,空间上的分散,让工人之间很难聚在一起,即便住得近,工作时间也未必同步,通勤时间长、生活节奏快,每个人都只想着赶紧回家休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自然难以建立。 在这种背景下,工人组织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工会、职工小组等传统组织,在新型就业形态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很多灵活就业者因为没有固定单位,很难纳入现有的组织体系,为了适应变化,很多地方探索了新型的服务站点和线上平台,比如城市里出现了劳动者服务站,为快递员和骑手提供休息、维权和技能培训等服务,有的线上平台还组织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和技能提升课程,虽然这些新组织不像过去那样大规模聚集,但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更有针对性,更贴近工人的日常需求,行业协会、技能认证、平台仲裁等也成为工人连接利益的新纽带,大家不再依靠大集体行动,而是通过更灵活的小组织、小圈子,获得保障和支持。 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算法管理的普及,给工人的工作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平台经济下,算法成了“无形的管理者”,负责派单、计酬、考核,每个骑手、司机、客服人员的工作进度、服务评价、收入结算,都紧密地和算法绑定在一起,算法让资源配置更高效,但也把工人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数据点”,每个人的工作被精细量化,绩效考核标准明确,收入多寡一目了然,算法既让工人之间的合作变得稀少,也让大家更加依赖平台规则,与此同时,技术也在催生新的合作方式,比如部分行业会通过线上社区分享经验,远程技术员之间组建兴趣小组,外卖骑手会利用社交软件交流路线和避坑技巧,虽然这种联系松散,但也为工人提供了新的互助空间。 中国工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只是表达方式更隐形、更灵活,技能升级、制度保障、小型组织成为新趋势,许多工人把精力投向提升个人能力,通过学习新技术、考取证书来增强职业竞争力,越来越多的行业建立了细致的劳动标准,保障工人权益,维权方式也变得多样,遇到问题可以找服务站、行业协会、线上平台协助解决,新生代工人更愿意通过法律途径和制度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依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大家习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变化,依靠技术和制度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