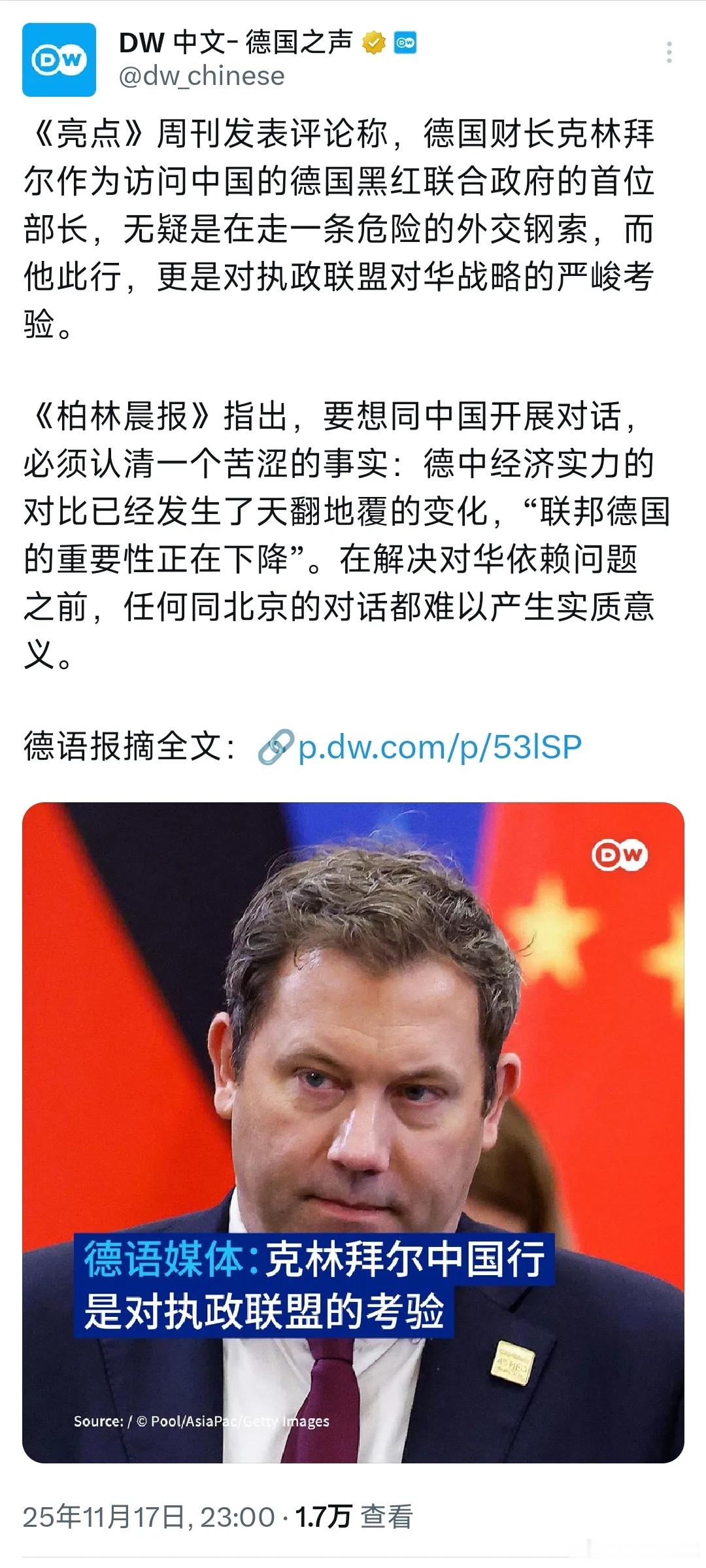基辛格早就说过,俄乌打久了,最先倒霉的不是美国,不是小国,是德国。德国这么多年,基本靠的是俄罗斯便宜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没有这玩意,德国的工业根本支撑不住。默克尔搞的北溪管道,直接是德国经济的命脉,没了它,德国就完了。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时,99岁的基辛格直言:“这场战争拖得越久,德国会比美国和小国更先垮掉。” 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到2025年10月,德国工业数据断崖式下跌,能源账单涨幅达三倍,人们才意识到这位老人早已看透德国的命门。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默克尔推动“能源转型”,在关闭核电站的同时,与俄罗斯敲定北溪管道项目。截至2021年,俄罗斯天然气占德国进口量的55%,且价格较欧洲其他国家低30%。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当年能源成本优势为德国工业节省近200亿欧元,支撑起奔驰、宝马、巴斯夫等巨头的全球竞争力。 北溪1号、2号先后因爆炸停摆后,德国转而从美国、卡塔尔进口液化天然气,仅运输成本就比管道气高两倍,2024年德国工业天然气采购价达每千立方米380欧元,为2021年的4.2倍。 能源危机最直接的表现是工业企业外迁潮,2025年德国联邦经济部报告显示,上半年有138家大型工业企业迁出生产线,较2022年增长210%。 其中,西门子能源将燃气轮机生产线迁至中国成都,其理由明确:“当地天然气价格仅为德国的1/5,且靠近亚洲市场。” 中小企业受冲击更为严重,巴伐利亚州中小企业协会调查显示,2024年该州23%的机械制造企业倒闭,倒闭率为往年的三倍,企业主普遍表示“能源成本过高导致无法开工”。 寻找替代能源并非易事,德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但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较大,稳定供电所需的“调峰”仍依赖天然气。 2025年德国联邦能源署数据显示,可再生能源占比虽提升至48%,但冬季用电高峰时仍有35%的缺口需通过天然气填补。 煤炭能源则受环保政策严格限制,2024年重启的10座煤电厂因排放超标被欧盟罚款12亿欧元,无法满负荷运转。 这一困境与地缘政治紧密相关,默克尔时期,德国通过“能源换和平”策略与俄罗斯保持平衡,既获得廉价能源,又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调解作用。 德国曾经历类似能源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中,依赖中东石油的德国工业停产30%,GDP暴跌4.7%。但当时石油供应来源多元,存在补救空间。 此次能源危机与1973年存在本质区别,俄罗斯天然气的性价比与运输稳定性均无替代者。德国央行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德国工业增加值下降7.2%,跌幅超过1973年石油危机时期,核心原因是天然气供应短缺问题尚未缓解。 能源危机引发连锁反应。德国作为欧盟经济引擎,其经济疲软直接拖累整个欧元区。2025年二季度欧元区GDP环比下降0.3%,其中德国贡献0.2个百分点的跌幅。 法国、意大利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因德国供应商断货被迫停产。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欧元区失业率升至7.8%,德国失业率突破6%,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 一个易被忽视的细节是德国军工产业同样受波及,2025年德国国防部向议会提交的报告显示,豹2坦克生产线因高温锻造环节天然气供应不足,月产量从15辆降至8辆。 截至2025年10月,德国仅向乌克兰交付42辆坦克,未达成100辆的承诺。军工作为德国少数优势产业,其产能受限更凸显能源问题的致命性。 德国当前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2025年9月,朔尔茨派遣经济部长访俄,试图重启北溪管道谈判,但俄罗斯提出解除所有制裁并以卢布结算的前提条件,德国无法接受。 美国同时从中阻挠,特朗普政府威胁“若德国与俄罗斯和解,将削减驻德美军”,朔尔茨政府被迫维持现有政策。 德国并非毫无应对之策,但均远水难救近火。例如,德国与挪威合作建设的输气管道预计2027年才能完工;氢能替代方案中,2025年德国氢能产能仅能满足5%的工业需求,且成本为天然气的3倍。 德国的困境本质是战略短视的结果。默克尔时期的能源布局具备显著优势,但朔尔茨政府为迎合美国,放弃了这一优势。 基辛格的预判之所以准确,核心在于其洞察到德国经济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而俄乌冲突恰好引爆了这一潜在风险。 2025年的德国正面临核心竞争力缺失的危机:依赖美国将面临高价能源,与俄罗斯和解受政治因素制约,自主解决能源问题短期内难以实现。这一案例为各国敲响警钟:大国发展进程中,能源安全必须掌握在自身手中,依赖外部供应将埋下重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