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志愿军炮兵排长王宗重发现,美军坦克每天都来破坏我军工事。于是他主动执行猎杀任务,靠近后用无后坐力炮击毁敌人坦克。没想到,他用3发炮弹打出了奇迹。 1951年的朝鲜战场,硝烟与焦土覆盖着每一寸山川,在三号公路附近的狭窄谷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7军的战士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每天傍晚六点整,大地开始震颤,美军第7师的四辆M26“潘兴”重型坦克准时出现,像移动的钢铁堡垒,沿着固定路线缓缓推进。 它们用90毫米主炮对准志愿军苦心经营的工事,一发接一发地轰击,沙袋、圆木和泥土构筑的掩体在爆炸中四分五裂,战士们连夜修复的成果往往在几分钟内化为乌有,更让人焦虑的是,躲在坦克后的美军步兵总会趁机推进,迫使志愿军阵地不断后撤。 时任炮兵排长的王宗重站在观察哨里,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这个1929年出生的山东汉子,18岁参军,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成长为出色的炮兵指挥员,辽沈战役时,他操作的山炮曾精准摧毁国民党军的暗堡。如今面对美军坦克的嚣张气焰,他内心的怒火与职业本能同时燃烧。 “它们就像踩着钟点来上班。”王宗重对身旁的参谋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望远镜,连续两天的观察让他发现了规律,坦克总是从同一片树林后出现,沿着之字形路线前进,在距离阵地八百米处开始射击,每次停留不超过二十分钟。 最让他揪心的是战士们的状态,工兵连的小战士李满仓,才十七岁,双手因为连夜抢修工事而布满血泡,前一天傍晚,当坦克的炮火再次摧毁刚修好的掩体时,王宗重看见这个年轻人把额头抵在焦黑的断木上,肩膀微微颤抖。 第三天下午,王宗重推开指挥部木门,径直走到参谋长面前:“给我一门无后坐力炮,三个晚上,我端掉这些铁乌龟。” 参谋长抬头,看着这个满脸硝灰却目光如炬的排长:“说说你的打算。” 王宗重摊开手绘的地图,指着一条干涸的水渠:“他们每天走这条路,我提前潜伏到涵洞。无后坐力炮的有效射程只有四百米,我必须放近到三百米内。” “四辆坦克,你带几发炮弹?” “三发。” 指挥部里一阵沉默。无后坐力炮虽然轻便适合潜伏,但面对重型坦克,必须击中要害才能奏效。三发炮弹意味着几乎不容许任何失误。 王宗重打破沉默:“头两辆我来打,第三辆如果来得及也打。要是第四辆反应过来,同志们用手榴弹和爆破筒解决。” 参谋长最终点头时,夕阳已经西斜。王宗重立正敬礼:“今晚六点,让他们尝尝咱们的炮火。” 1951年10月23日下午五点,王宗重带着四名战士悄然出发。副射手赵大山肩扛无后坐力炮管,弹药手刘福贵背着三发炮弹,另外两名战士携带冲锋枪和爆破筒。五人小组沿着交通壕潜行,最后一段路必须爬过开阔地。 “排长,要是美国兵发现我们……”刘福贵低声问。 “那就省下炮弹,用这个。”王宗重拍拍腰间的刺刀,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训练场。 他们最终钻进预定位置的涵洞。这个半塌的混凝土管道仅容三人藏身,王宗重让两名战士在侧翼灌木丛中建立掩护点。所有人检查装备:炮膛清洁,炮弹引信正常,冲锋枪保险打开。 五点五十分,远方传来引擎的轰鸣。王宗重轻轻拨开伪装在洞口的树枝,望远镜里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坦克的炮管正缓缓摆动。 “记住,”他回头对炮组说,“我打第一辆,装填后立即打第二辆。如果第三辆转向我们,赵大山负责掩护。” 当第一辆坦克进入三百米射界时,王宗重深吸一口气,无后坐力炮的瞄准镜中心稳稳套住坦克车体与炮塔的结合部。 “轰!” 炮身猛地后坐,炽热的气浪把涵洞里的尘土卷起。几乎在同时,远处坦克爆出一团火球,炮塔在爆炸声中歪向一侧。 “命中!”赵大山一边装填第二发炮弹一边低吼。 但意外发生了——第二辆坦克没有停留,反而加速冲来,机枪子弹泼水般扫向涵洞方向。更糟的是,第三、四辆坦克开始向两侧迂回,试图形成包围。 此时第三辆坦克已经绕到左翼,炮口正对着他们的方向。王宗重听到装填声——赵大山把最后一发炮弹塞进炮膛。 王宗重几乎没有瞄准,凭肌肉记忆完成击发。炮弹直接钻进坦克的驾驶舱,剧烈的爆炸把炮塔掀飞起来。 幸存的第四辆坦克慌忙后撤,胡乱发射烟雾弹。王宗重抓起冲锋枪:“同志们,追!” 王宗重的战绩当晚传遍整个战线,志愿军司令部通令嘉奖,给他记二等功。更重要的是,美军第7师从此再不敢让坦克单独行动,三号公路地区的压力骤减。 1952年底,王宗重作为战斗英雄代表回国汇报。在北京的报告会上,他举着那颗金达莱花压成的书签说:“我们不是在为战争而战,是为了让祖国的孩子们能在和平年代里,安静地看一朵花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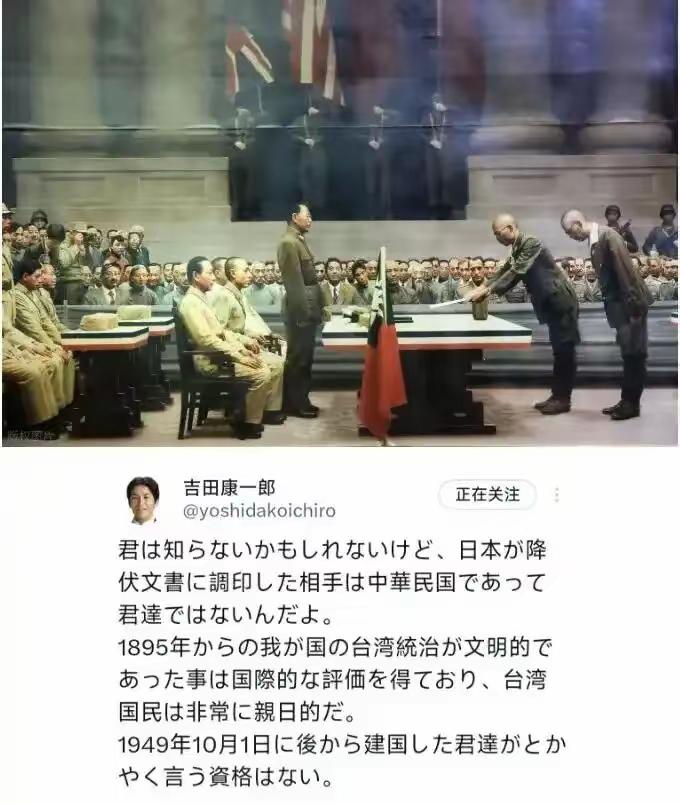




墨里春秋
向英雄致敬,致敬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