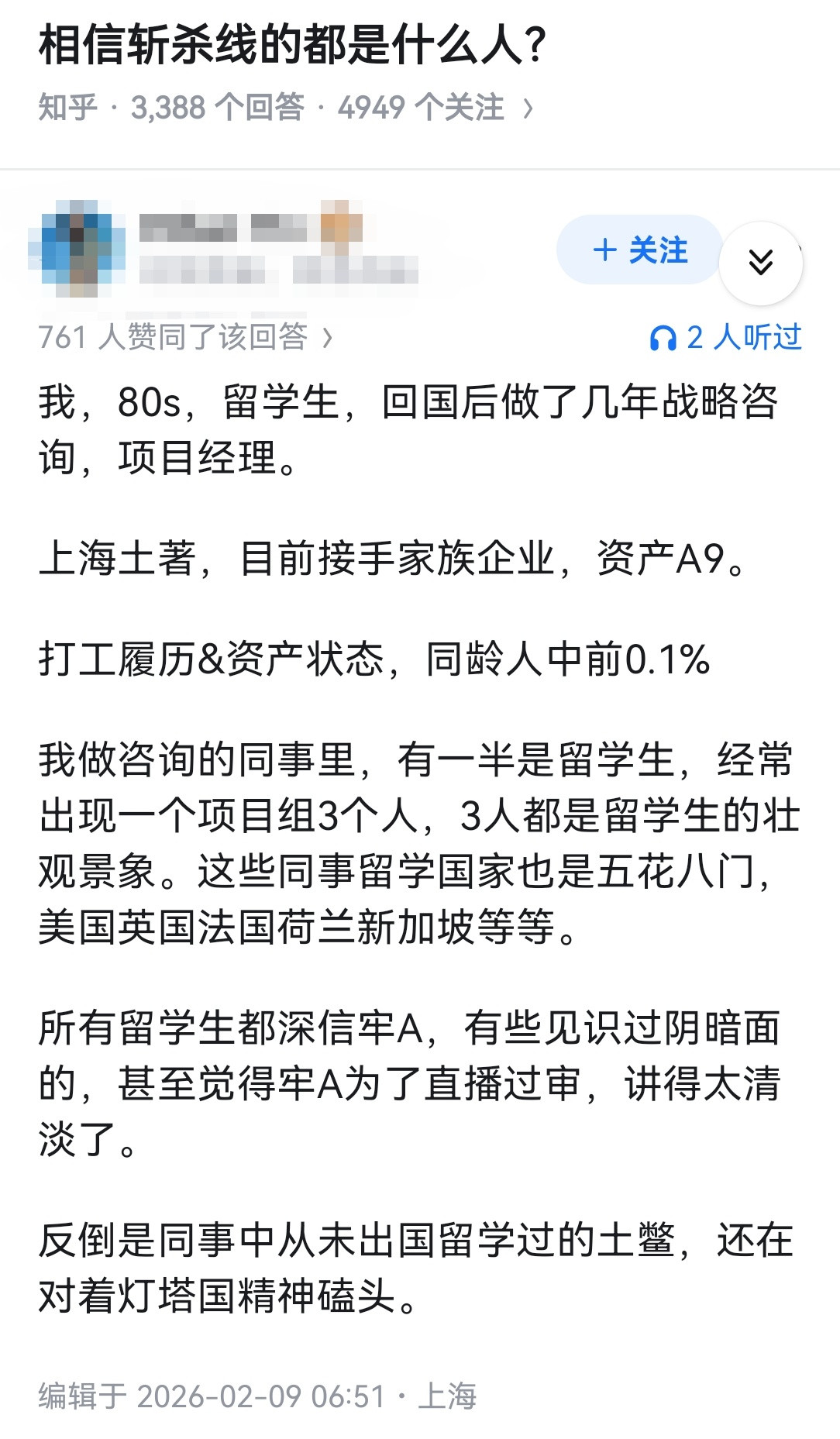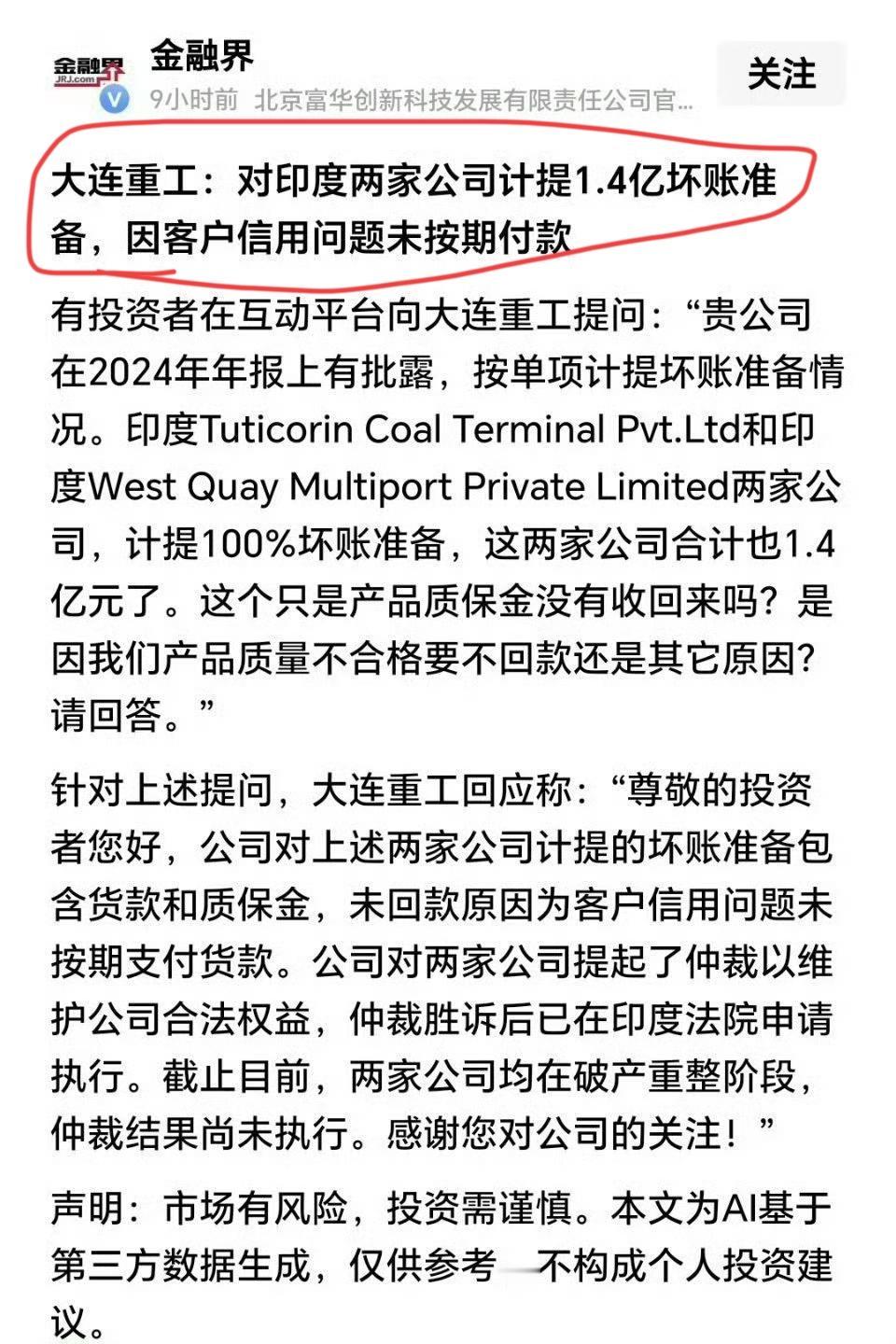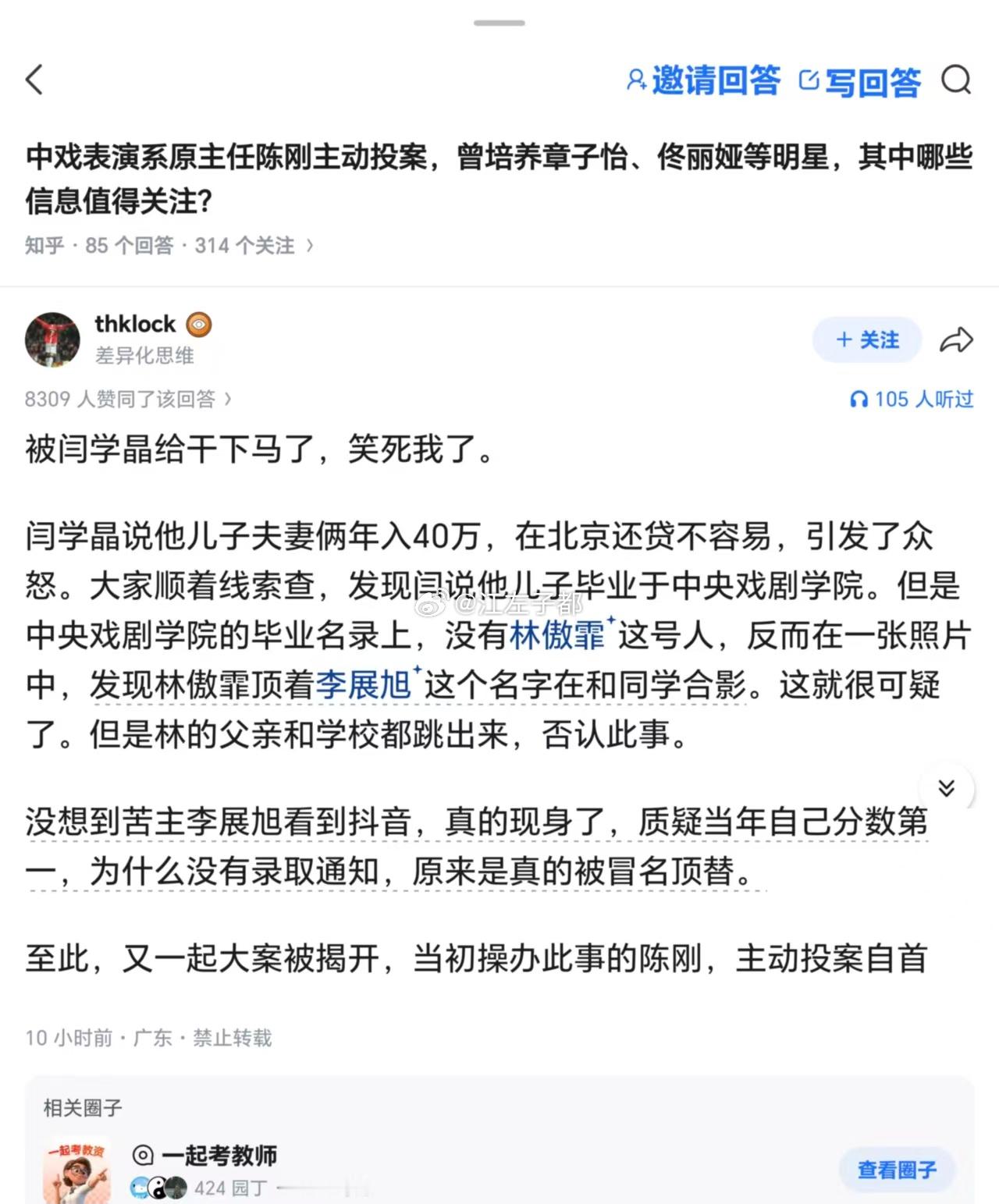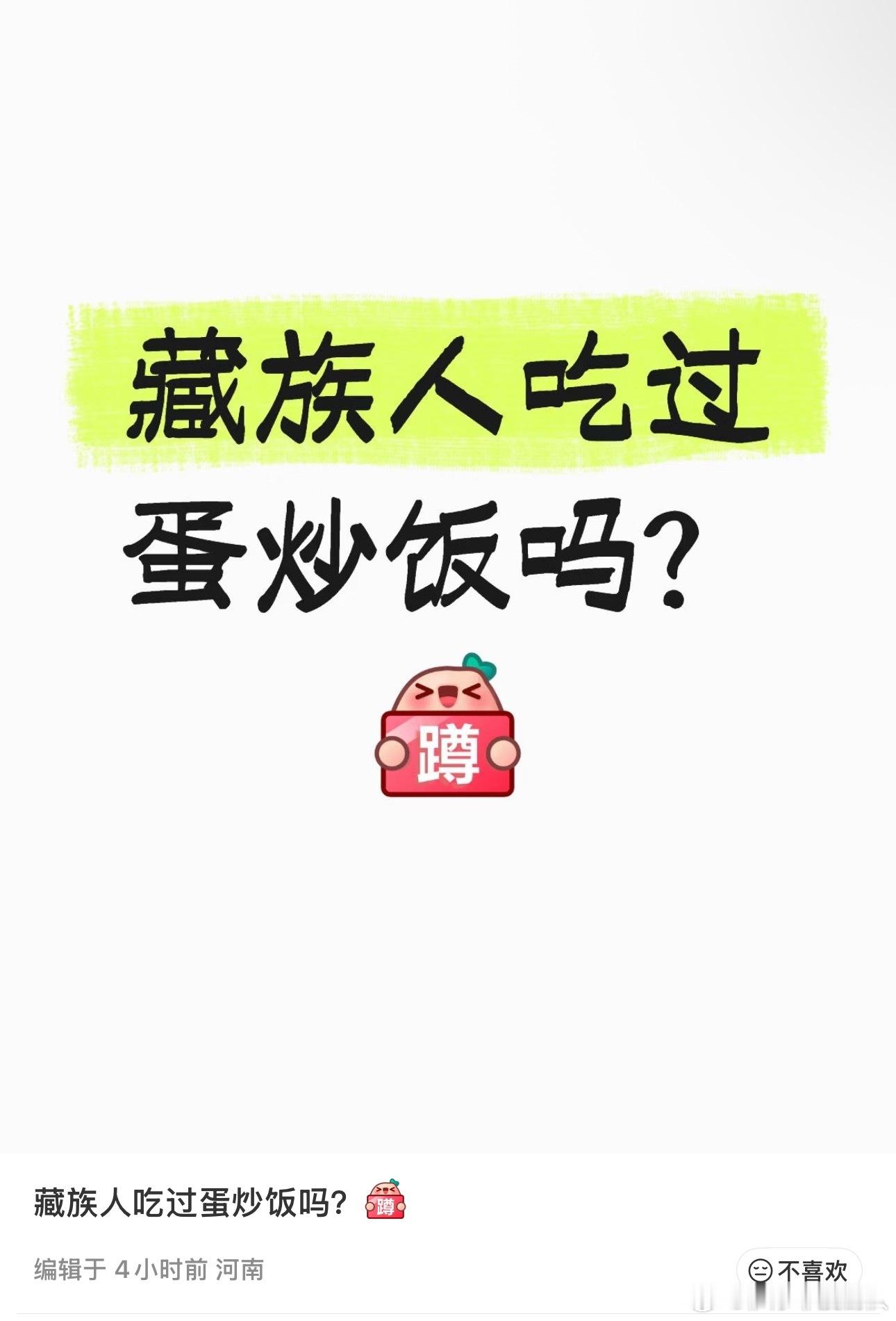2006年,51岁的林肯霍尔成功登顶珠峰,却在下山途中停止呼吸,众人只能丢下他离去,可没想到,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那天晚上把他丢下的时候,夏尔巴人其实犹豫过。 他们不是冷血。只是氧气没了,天黑了,雪盲症让眼前只剩白茫茫一片,那个叫林肯·霍尔的澳大利亚人已经没有脉搏、没有呼吸、瞳孔散开。在海拔8700米的地方,你没法给这种状态的人开死亡证明,但你心里清楚,这就是死人了。 他们把遗体靠在雪坡上,用登山杖固定了一下。有人摘下他的手套,看了几秒,又戴了回去。没用,手指已经硬了。 然后他们往下撤,谁都没说话。 整整十二个小时。 零下二十五度,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我查过资料,那种环境里,大部分人二十分钟意识模糊,两个小时心肺功能停摆。十二小时,足够让一个正常人冻成冰雕。 可他没死。 第二天早晨七点,美国登山者马祖尔路过,踢到了什么。低头一看,雪地里露出来一张脸。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吓得连退好几步,那张脸不是白的,是粉红色。活人才有的粉红。 霍尔睁开眼,说:“我渴。” 这事后来被叫做“珠峰奇迹”,但我重读当年的报道时,有个细节怎么也绕不开,霍尔下山途中累倒在雪地里,向导们架着他走了九个小时,只往下挪了一百米。九个小时,一百米。夏尔巴人不是不想救,是真的拖不动。 这时候队长从大本营传来指令:放下他,你们下来。 指令没有错。八百米之上每个人都在用秒计算氧气,耗下去只会多添几具尸体。可放下他之后,队长转头就在登山网站上发了讣告。 他们都认定他是死人了。 包括霍尔自己。 他苏醒后告诉医生,那一夜他做了很长的梦,梦到小时候在墨尔本的海边,海水是温的。这是典型的失温症濒死体验,身体在最后一刻把所有血液撤回心脏,四肢凉透,大脑却幻觉出热带的阳光。 所以他根本没挣扎,没恐惧,甚至没觉得冷。 真正让我不舒服的,是这件事发生后一周,媒体铺天盖地讨论登山伦理,人们反复质问:为什么见死不救?为什么把同伴丢在山上? 可霍尔本人说,他不怪任何人。 他说,换作是他,也会走的。 这种原谅听起来很豁达,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后来想明白了,这不是原谅,是认命。在八千米以上,人和人的关系被压缩到最原始的状态:你走得动,你就是同伴;你停下了,你就是地形。登山者管这叫“八千米法则”,很残酷,也很诚实。 我们坐在有暖气的房间里指责别人冷血,但那个夜里,夏尔巴人陪了霍尔九个小时,直到自己双眼失明才下山。这不是冷血,是极限。 其实这事儿有个更扎心的镜像。 就在霍尔被“遗弃”的一周前,英国登山者夏普同样困在珠峰附近,四十多个人从他身边经过,没一个人停下来。 四十多个人。不是被迫丢下他,是选择绕过他。 那四十多人里有谁被指责了吗?没有。他们照样登顶,照样接受采访,照样在社交媒体晒照片。夏普的尸体至今还在山上,成了路标。 霍尔比夏普幸运,仅此而已。 我每次想到这个对比都觉得荒唐。同样是生命,有人被无奈放弃,有人被视而不见,结果前者奇迹生还,成了新闻主角;后者孤独死去,成了海拔数字。 山从来不审判人,审判人的永远是山下的看客。 这二十年,珠峰南坡的商业攀登涨了十倍,登山许可证从几千美元涨到一万多。越来越多的“登山体验者”被向导拖着拽着拉上峰顶,再像行李一样运下来。他们不需要会认路,不需要会判断天气,甚至不需要会给自己系冰爪。 这帮人路过濒死的夏普时,大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冷血,是失能。 他们从来没学过怎么在八千多米判断一个人还有没有救。向导公司也没教过,因为这不是客户付费范围内的事。 所以你看,问题不在“要不要丢下同伴”,而在,当我们把登山变成流水线服务,把登顶包装成人生打卡,那人与人之间那点原始的羁绊,到底还剩多少? 霍尔活下来了。他冻伤了手指,患了脑水肿,失忆了几个月,但命保住了。 可他的队友韦伯死在同一条路线上,就在他登顶后三小时。 这世上没有公平的山,只有被随机挑中的生,和未被挑中的死。 珠峰脚下有许多玛尼堆,石头垒起来,上面压着旧冰镐、褪色的经幡、氧气管。有些是真墓碑,有些是纪念品。 我不确定霍尔的故事该归到哪一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