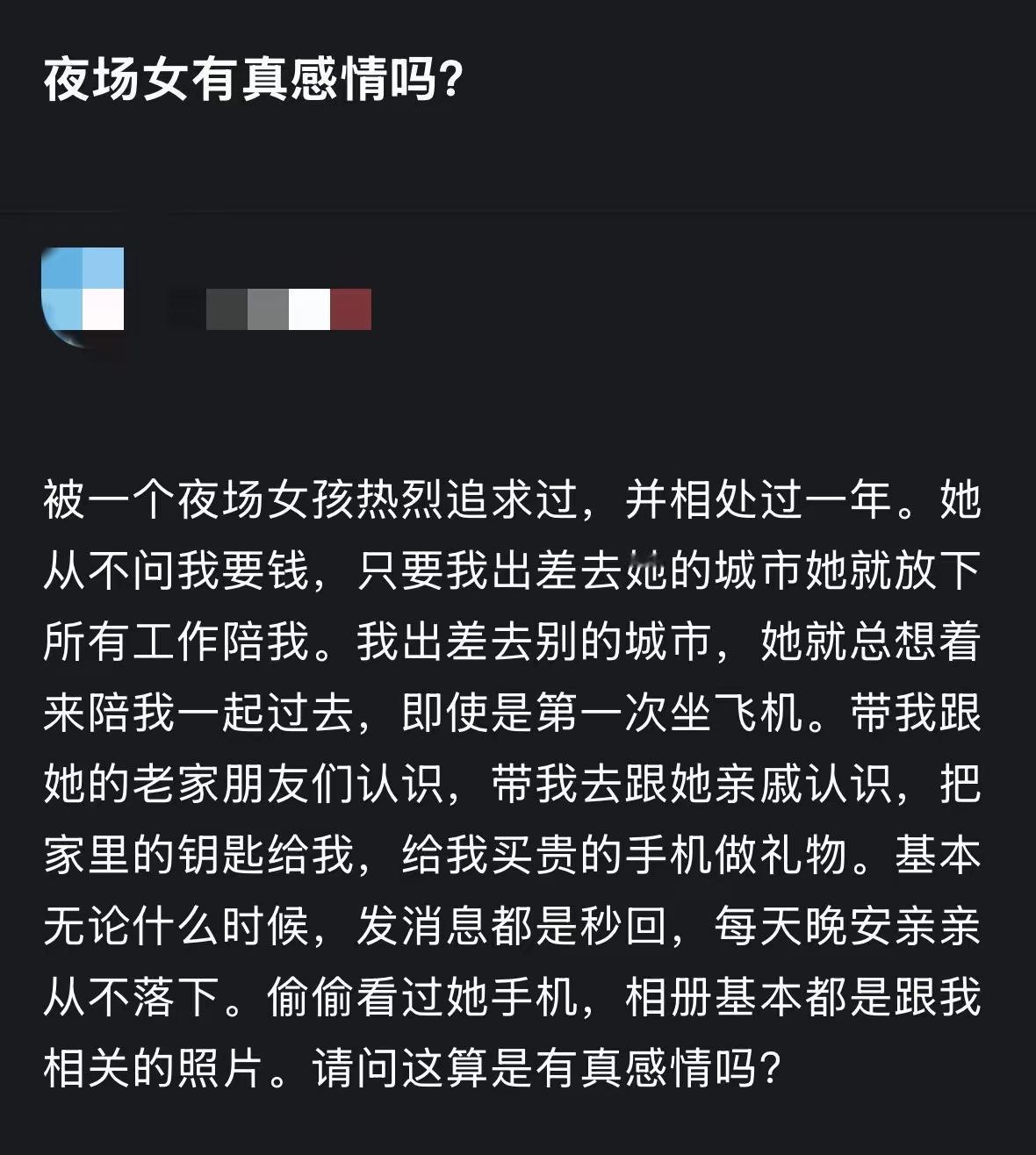1975 年我去县里卖木材,晚上借宿的地方凑合,和一个陌生女人分了一张床。睡到半夜,她忽然悄悄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了我一句:“你是哪儿人?” 我没睁眼,回了句:“靠山屯的。”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屋里黑,只有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一点,照出她坐起来的轮廓。风扇在墙角吱呀呀地转,没什么风。 过了好半天,我以为她睡了,她却忽然又开口,声音轻得像怕吵醒空气。“大哥,你身上……有没有吃的?” 我这才觉出不对劲。我摸黑坐起来,从搭在床头的衣服里掏出半个硬饼子,是白天没吃完的。递过去的时候,碰到她的手,冰凉。 她接过去,没立刻吃,攥在手里。黑暗里,我听见她吸了吸鼻子。“我两天没吃东西了,”她说,“不是饿得受不了,不会开这个口。” “你一个人?”我问。 “嗯。来找人,没找着。”她咬了一小口饼子,嚼得很慢,很仔细。然后她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说:“我其实不是河湾村的。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我愣了一下。那年头,女人家跑出来,可不是小事。 “我爹要把我嫁给邻村一个老光棍,换他家的猪和彩礼。那光棍喝酒打人,前一个婆娘就是被他打跑的。”她说得很快,声音却平静,“我半夜翻墙出来的,走了三天路,想到县里找我姨。可地址丢了,找不着。” 她说完,屋里只剩风扇的吱呀声。我不知道该说啥,摸出旱烟袋,想了想又放下。 “那你接下来咋办?” “不知道。”她说,“走到哪儿算哪儿吧。总比回去强。” 我摸到裤子口袋,里面是卖木材的钱,用橡皮筋扎着。我抽出一张五块的——那会儿是很大的数目了——又拿了两张一块的,卷在一起,伸手递向她那边。 “这钱你拿着。不多,应个急。” 她的手在黑暗里碰到了我的,僵住了,没接。“我不能要。咱非亲非故的。” “拿着吧,”我把钱塞进她手里,“就当我借你的。哪天你日子过好了,再还我。” 其实我心里明白,这钱借出去,八成是没得还了。 她没再推辞,把钱紧紧攥住。我听见很轻的、压抑的抽气声。 后半夜,我们都没睡。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打了个盹。等鸡叫三遍睁开眼,她已经走了。我枕边整整齐齐放着那半个饼子,下面压着皱巴巴的五毛钱。饼子上,有个小小的、整齐的牙印。 我拿着那五毛钱和半个饼子,在床边坐了很久。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了。
我跟你说,我发现有些女人真把婚姻这事儿玩明白了。有个女的,离婚三年,一个月能往
【5评论】【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