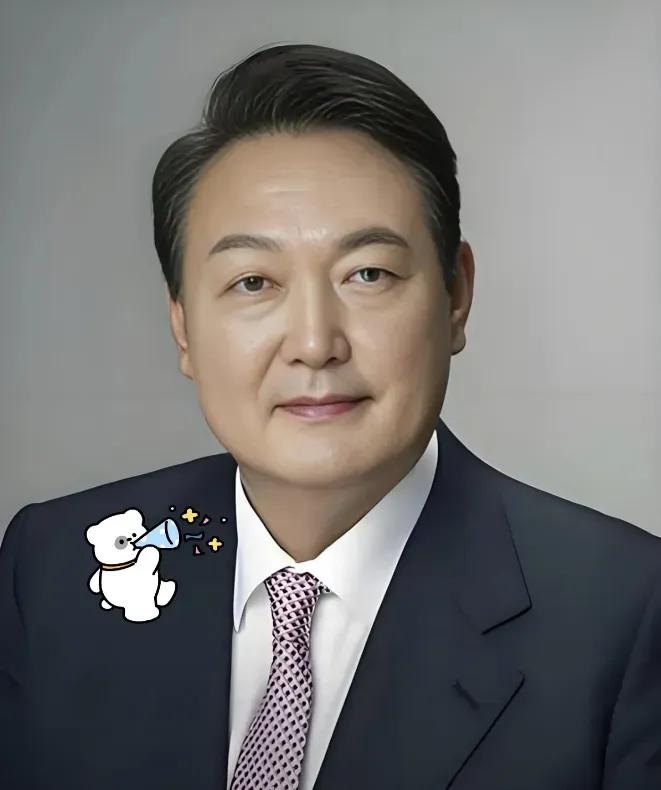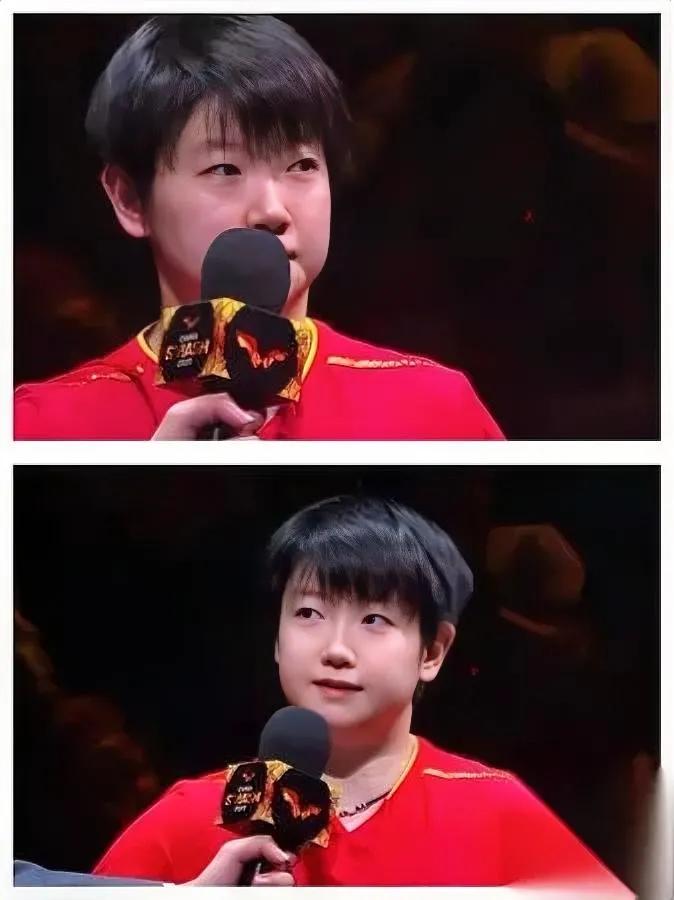看《老舅》,看到郭小雪,我后背直发凉。 她爹在牢里,爷爷走了,跟着亲戚过活。那天傍晚我见她蹲在巷口,指尖戳着流浪狗湿漉漉的鼻子,狗尾巴尖还沾着泥,她却突然把狗往怀里一揣,闷头往屋里走——明明前一晚才哭着跟老舅说“那不是我家”。 饭桌上更绝。表妹扒拉着碗里的菜,她突然放下筷子,声音发颤却眼神直勾勾:“我再磨牙,你们就打我。” 一桌子人手里的碗都顿了顿,空气里飘着没说完的话——谁舍得打?可谁又受得住这份“懂事”? 这孩子到底想干嘛? 有人说她就是被惯坏了,寄人篱下还挑三拣四;也有人觉得是青春期叛逆,故意折腾大人。我起初也这么想,甚至觉得她像株带毒的藤蔓,悄无声息就缠得人喘不过气。 直到看见她半夜抱着狗蹲在阳台,狗睡在她臂弯里,她自己靠着墙,眼睛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影晃一下,她睫毛就颤一下。 那哪是折腾?那是抓救命稻草啊。 寄人篱下三年,她书包上的拉链坏了半年没人换,生日那天亲戚给的红包,转手就被拿去给表妹买了文具。她从没正经撒过娇,因为撒娇需要“被看见”的底气,而她连“存在”都得自己挣——说“不是家”是试探,怕被赶走;捡狗是占地盘,用一条命拴住另一条命;饭桌上说“打我”,是把自己放在最低处,换别人不敢轻举妄动。 心理学里管这叫“防御性攻击”,可对郭小雪来说,哪懂什么理论?她只知道,直来直去的想要会被拒绝,那就换个方式——用委屈当盾牌,用“懂事”做武器,哪怕扎伤别人,也得给自己撑出个角落。 这不是心机,是碎掉的孩子在粘自己啊。 像摔在地上的瓷碗,裂纹太深,拼不回原样,只能用尖刺朝外,假装自己还是个完整的碗。 现在再看她,后背不凉了。 是疼。那种看见有人在水底挣扎,却发现自己递过去的手,也被她当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的疼。她哪是坏啊,她只是从没被人好好接过——连哭,都得先看看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