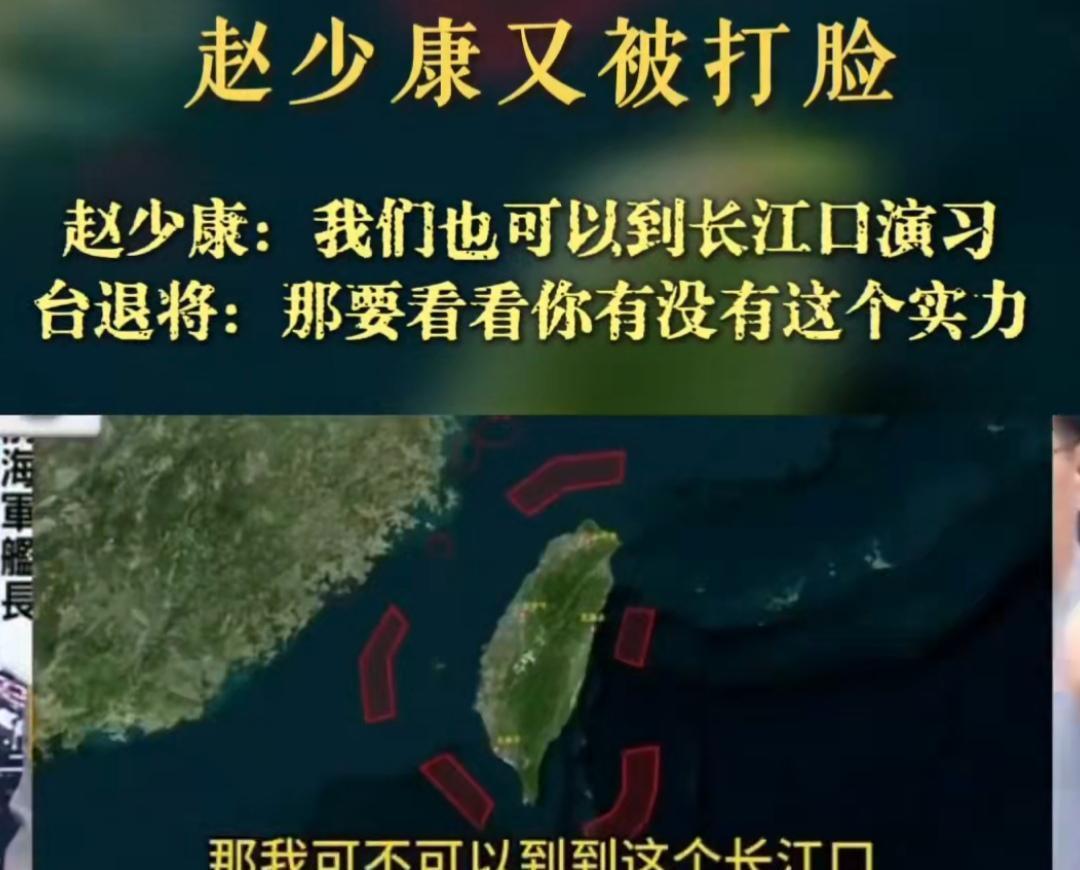1968年,台湾美女服务员意外被中非暴君相中,很快就远嫁非洲,过上了奢靡的生活,谁知当她给黑人总统生了两个孩子后,这位美女服务员突然仓皇返台,这究竟怎么回事? 那年,博卡萨率团访台,入住圆山大饭店。林碧春被安排为中非团组服务。据部分历史资料描述,博卡萨对台湾的接待非常满意,尤其对林碧春“照顾有加”的细致印象深刻。 当时的外交气氛极其敏感。中非是与台“建交”的少数非洲国家之一,而“联姻”常常被视为国家关系“加分项”。林碧春的出现,无疑恰好成为了这种“外交示好”的象征。 博卡萨很快提出,希望她能陪同前往非洲。他用尽手段,用豪车、钻石、奢侈品,包裹着这个请求。她的家人并不反对。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服务员能“嫁入王宫”,本就是天降机遇。 她犹豫过,但终究上了那架飞往班吉的飞机。 林碧春刚踏上中非土地时,热带阳光刺眼,热浪扑面。总统府比她想象中更大,仆从成群,围墙高耸。宫里早已为她准备好住所,一座红顶白墙的小楼,四周是岗哨和围栏,像一座漂亮的孤岛。 她的房间里装着空调,铺着进口地毯,家具是镀金的欧式风格。每天清晨,仆人端来银盘早餐,车队待命。她可以穿戴欧洲来的高定礼服,也可以点播她喜欢的台湾歌曲。看起来应有尽有,像进了童话城堡。 她陪同博卡萨出席活动,坐在王座旁,被介绍为“总统夫人”。她微笑、挥手,嘴角僵硬。她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官员和军人敬礼时的热情让她害怕。 她的“宠爱”只是博卡萨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牌。在外国媒体面前,他炫耀自己的多元家庭,用她当作“开明包容”的象征。但回到宫里,他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下一个女子身上。 她逐渐失去主动权,宫里的女仆也不再听她指令。她想学法语,被拒绝;她想写信,被要求“事先审核”;她问孩子的未来,对方说:“听总统安排。” 她为博卡萨生下了两个孩子。生育时,全城鸣放礼炮,宫里办了宴会。可孩子刚满月,就被带走“集中照养”,连见面都要申请。她曾去找,看见孩子穿着整齐制服,被侍女抱在怀里,不再熟悉。 她试图向母国寻求联系,但身边已无可信的人。她意识到,这不是“远嫁”,是被安置,是被囚禁在金色牢笼的异乡人。 那些夜晚,她站在阳台,望着宫墙外黑漆漆的夜色,脑中闪过圆山饭店厨房的灯光,那才是真实。她悄悄地开始打听:怎么能回台湾?带着孩子,安静地,逃离这一切。 林碧春终于意识到,所谓的“尊贵”只是一场困兽之宴。 日子过得越久,宫里的戒备越严。她的行动被限制,外出需要批准,身边的人都在监视。她试图联系外界,却总被挡回。她甚至连孩子的日常都无法过问。她不是妻子,不是母亲,更不是公民,只是一个被摆上舞台的“象征”。 她最初的服饰、自由、待遇,逐渐被剥夺。新来的女人取代了她在宴席上的位置。她在宴会的尽头站着,像个侍女,听着别的女人笑语盈盈地挽着博卡萨的手臂入席。 宫中的仆人不再用尊称称呼她,孩子也被送往“国家子女教育中心”,连探视都要签字申请。她的名字,身份,甚至语言,都被慢慢清空。 某天夜里,她偷偷潜入总统府图书馆,找到一部地图和一部陈旧的电话。那天之后,她反复练习怎么拨打电话回台湾驻中非“联络办”,小声地练,悄悄地记。 终于,某个黄昏,她成功接通了那边的号码。她不敢说太多,只说:“我想回来……带着我的孩子。”那头沉默了一会,答应她,会想办法。她听完,泪流不止。 接下来的几周,气氛压抑。她开始偷偷整理物品,藏起孩子的衣物与证件。有人告诉她,博卡萨在准备大规模清洗旧部,外界正在质疑他的政权合法性。她知道,再不走,自己和孩子都可能被牺牲。 有一天清晨,一辆非官方牌照的车辆停在她住所后门。她穿着最朴素的衣服,带着仅有的几个箱子,两名孩子裹着毯子在后座睡着。车启动的瞬间,她再没回头看那座金碧辉煌的王宫。 她不是王妃。她只是个想活着回家的母亲。那天,她逃了。穿越了一个独裁者的阴影,穿越了文化的铁幕,带着两个孩子,驶向未知的未来。 返台后,林碧春拒绝接受采访。没有媒体专访,没有官方通告。她仿佛从未存在过。她曾一度居住在台北郊区,靠亲友资助生活。 她没有公开提及那段经历。没人知道她是否后悔,也没人能真正理解她那几年在非洲王宫中的孤独与恐惧。 她的两个孩子如今何处,也无从查证。她这一生,仿佛就是那个年代夹缝中,一个被推上权力风口的普通人,被高举,也被遗忘。 那个曾在王宫穿金戴银的女子,最终只能低调回到故土,重新过上平凡生活。外人眼里是神秘、是传奇,但她自己,恐怕只记得那些年夜夜梦回时的困兽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