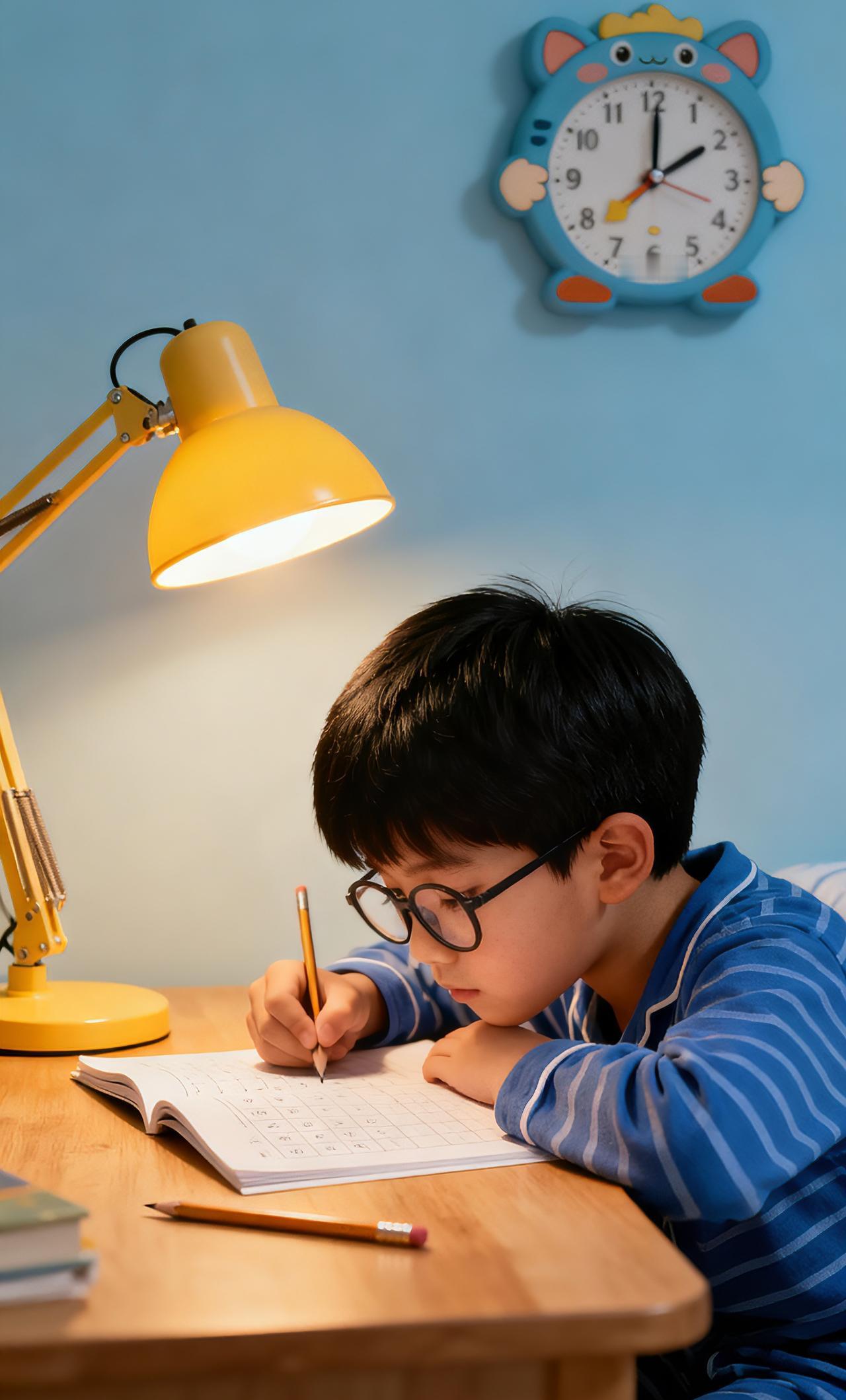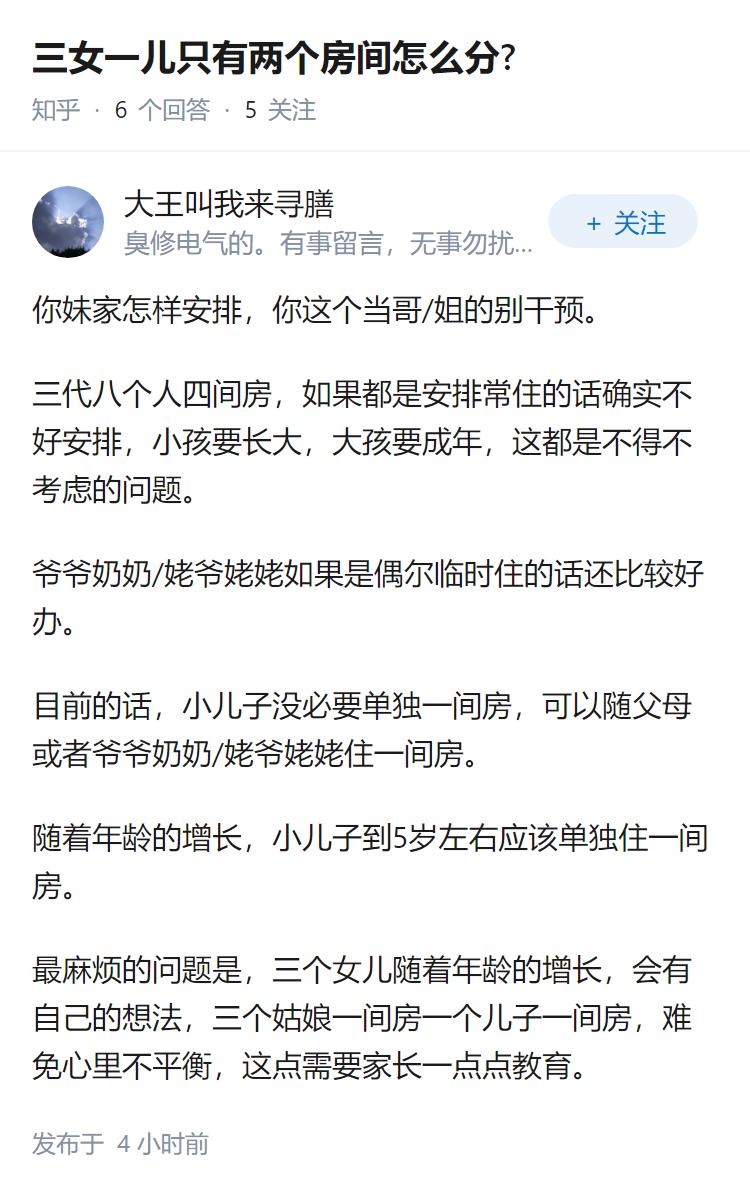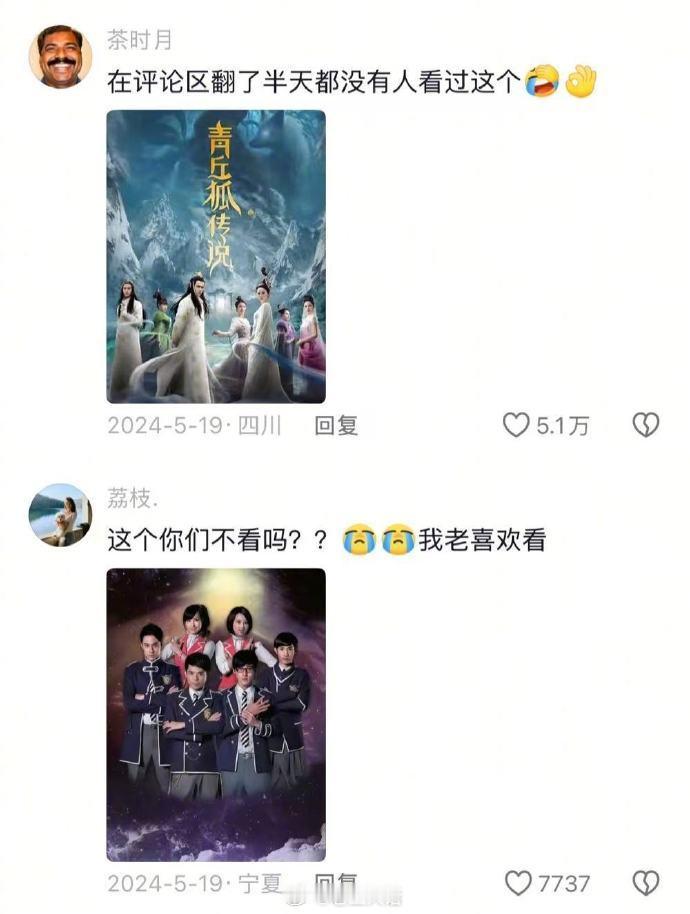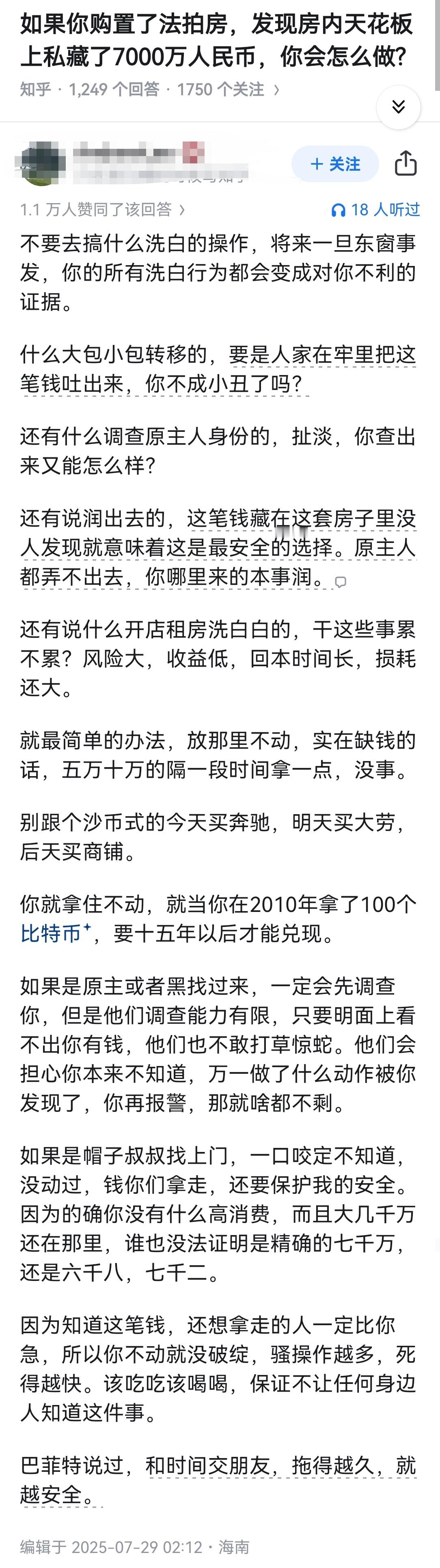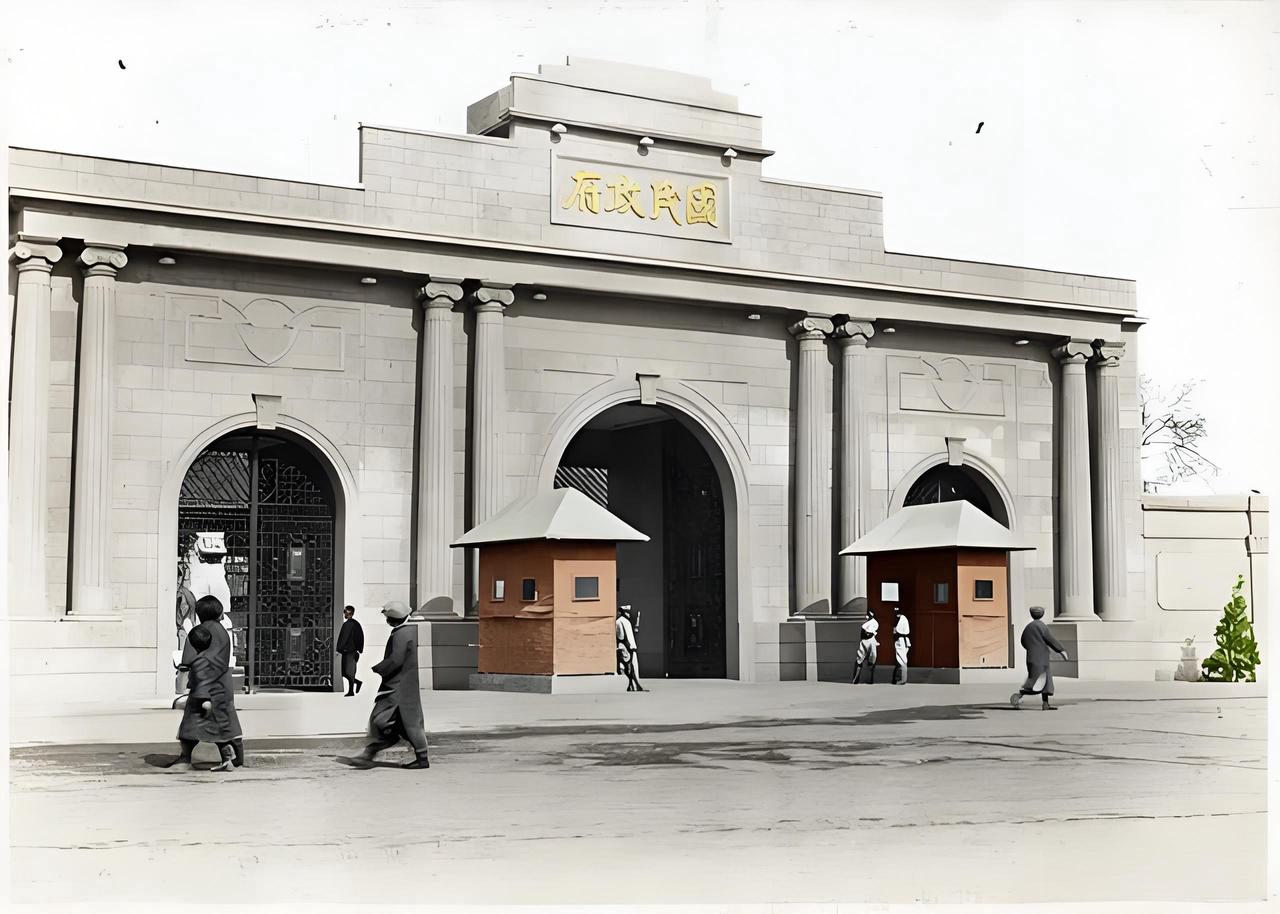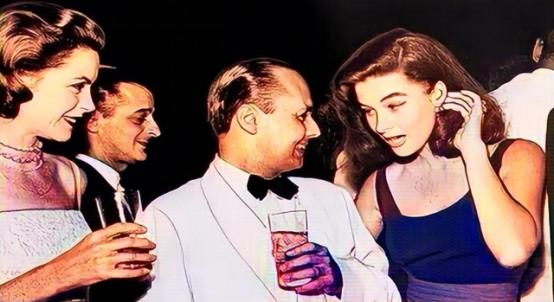1976年,儿子入伍3年后,农民蒲运海却等到了儿子死在战场的消息。谁料,打开烈士证书后,蒲运海一脸震惊:上面的名字和儿子的居然同名不同姓。此后,蒲运海便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儿子。 蒲运海是四川岳池县大佛乡普通农民,早年老婆去世,他就守着独子蒲仕平过日子。那时候农村苦,蒲运海每天天蒙蒙亮就下地干活,种包谷红苕,养头猪贴补家用。蒲仕平从小帮爸干活,挑水砍柴不喊累,身体壮实,村里人都说这娃有出息。 1957年蒲仕平出生,蒲运海一个人拉扯大,教儿子识字干农活。孩子长到十几岁,就爱听老人们讲边境部队的事,总说要保家卫国。1976年征兵,蒲仕平报名通过,村里敲锣打鼓送他走。那天蒲运海没多话,就把自家炒了三天三夜的黄豆塞进儿子背包。蒲仕平进了昆明军区14军40师118团,当了侦察兵,训练刻苦,很快就站稳脚跟。 入伍三年,蒲运海常收到儿子来信,说军营生活好,立志多立功。蒲运海不识字多,找村里人念,回信时仔细写,寄点家乡干货。日子就这么过着,他盘算着儿子退伍能分配好工作,日子红火起来。农村信息闭塞,他不知道南边边境已经紧张。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蒲仕平部队紧急开往前线,投到云南河口南溪河一带。战场乱,蒲仕平在2月17日一次任务中左胸中弹牺牲,才22岁。战友收殓遗体时,身份牌被血水雨水泡模糊了,“蒲”字看成“卞”,登记时就成了卞仕平。这个错,在战时匆忙中没人注意,直接进了档案。 几个月后,通知到村里。蒲运海正在地里干活,村支书跑来叫他去公社接电话。公社离家几小时路,他赶过去,部队干部递过烈士证书。蒲运海接过来,勉强认字,看到“卞仕平”三个字,顿时不信,反复问部队番号和籍贯对不对。干部说没错,是战场牺牲。他死死攥着证书,坚持说儿子姓蒲,肯定搞错了。从那天起,他就不认这个结果。 蒲运海认定儿子还活着,只是名字错导致找不着。他开始自个儿寻,卖掉家里值钱东西,带干粮竹杖去云南。农村没钱坐车多,他步行加搭车,走到昆明部队驻地,问了没人知道准确埋处。又去麻栗坡、屏边这些烈士陵园,一块块碑看,手擦碑面找名字。 陵园多,碑成千上万,他从早看晚,腿走肿了绑布条继续。找到类似名字就仔细比,不是又接着找。回家后省吃俭用,攒钱寄给陵园管事人,托他们留意,还寄干花放可能的地方。每年清明前后,他又想办法去边境转。 三十多年过去,蒲运海从壮年走到白发苍苍,眼睛花了腿脚不好,但只要有线索,就背包上路。乡亲劝他算了,他摇头,说儿子答应过争光,不能就这么扔下。村里人看他倔,也帮着打听,可信息太旧,总没结果。 那时候农村找人难,部队档案战时乱,很多事说不清。蒲运海就这么一年年等,一年年找,头发白完,腰弯了,还在坚持。很多人家儿子牺牲就安葬本地,他却连碑都摸不着,这痛谁懂。 转机在2015年,一个网友查老档案,发现屏边陵园东3区17排有座碑刻“卞仕平”,出生年月籍贯全对得上。联系民政局,比对确认,就是蒲仕平,错在战时身份牌模糊。 消息传到蒲运海,他92岁了,耳朵背腿不利索,但听说后马上要亲自去。家人扶他坐车到云南屏边,谷雨天,他看到新碑刻上“蒲仕平”,碑下添了父亲立碑的字。他蹲那儿半天,手摸碑面。 民政局给正名,重立碑,蒲仕平终于恢复真名,安葬在屏边。蒲运海把36年前的黄豆放碑前,心愿了了。回家后,他常坐门口看远山,那根竹杖靠墙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