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30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1988年广东老宅的藤椅旁,95岁的母亲颤抖着抚摸黄旭华掌心的老茧——那是30年算盘计算、钢板打磨留下的印记,比任何解释都更有力量。 就在几小时前,这位刚从南海300米深海归来的核潜艇总设计师,还穿着沾着海水的工作服,站在门口不敢认母亲,而老人盯着他看了半晌,只哽咽着重复“三儿瘦了”,却不知儿子刚从一场生死试验中闯回来。 黄旭华的“不孝”里藏着两次艰难抉择。 第一次是1958年接到调令时,父亲刚去世不久,母亲的头发还没全白,他站在灵堂角落,攥着那张写着“紧急任务,即刻赴京”的纸条,终究没敢告诉家人要去做什么。 妻子李世英后来回忆,他走的那天只带了一个小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本《船舶设计手册》,连一句“什么时候回来”都没敢说。 第二次抉择在1970年。当时核潜艇研制到了关键阶段,妹妹突然来信说母亲摔断了腿,想让他回家看看。黄旭华拿着信在试验基地的海边坐了一夜,海浪声里全是母亲的叮嘱。 他知道,只要自己开口,领导或许会批假,但潜艇的重心计算正卡在关键节点,三组人用算盘算出来的结果总差0.1克。 第二天一早,他把信锁进抽屉,在工作笔记上写下“潜艇不下水,母亲难安心”——他以为只要早点研制成功,就能有更多时间陪母亲,却没想到这一等,又是18年。 在荒凉的海岛基地,黄旭华的“土办法”曾让同事们哭笑不得。 为了确保潜艇重心精确,他要求所有设备上艇前必须过秤,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例外;施工产生的边角料要分类称重,扣除相应重量后才能记录数据。 有次年轻技术员嫌麻烦,偷偷把一小块废钢板扔了,他发现后立刻召集所有人开会,拿着算盘算了半小时:“这块钢板重38克,会让潜艇重心偏移0.02度,下潜时就可能撞上暗礁!”从那以后,没人再敢轻视这些“小事”。 1987年,黄旭华终于找到向母亲“报平安”的方式。 他在《文汇月刊》上看到一篇写核潜艇研制的文章,里面提到“总设计师的妻子叫李世英”,立刻把杂志寄给母亲。 94岁的老人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读了三遍,突然对子女们说:“你们三哥不是忘了家,他是在给国家造船呢!”妹妹后来在信里说,母亲把杂志放在枕头边,每天都要翻一翻,逢人就说“我三儿在干大事”。 1988年深潜试验前,黄旭华做了件“出格”的事。他把母亲的旧围巾叠好放进随身包里,对同事说:“要是真出了事,就把这个交给我家人。” 当时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深潜时艇毁人亡的阴影还在,参试人员里有人偷偷写遗书,他却笑着说:“我是总设计师,最了解这艘艇,我不下谁下?” 潜艇下潜到300米时,钢板发出的“咔哒”声让人头皮发麻,他却摸着口袋里的围巾,在日记本上写下“惊涛骇浪,乐在其中”——那一刻,他想的不仅是试验成功,还有回家后能给母亲讲讲“龙宫”里的故事。 如今的黄旭华,办公室里还摆着两样特殊的东西:母亲用过的老花镜,和当年算数据的算盘。 95岁高龄的他,每天仍会准时到研究所,帮年轻设计师修改方案,遇到复杂的计算,还会拿出算盘演示:“计算机算得快,但手动算过,才知道数据里的门道。” 他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全捐给了科研项目,说“这些钱要花在刀刃上,让更多年轻人能安心搞研究”。 去年冬天,黄旭华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回了趟广东老宅。 院子里的藤椅还在,他坐上去,仿佛还能看到母亲当年打盹的模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1988年那次回家时和母亲的合影,照片里母亲握着他的手,笑得很开心。 “母亲没等到我给她讲核潜艇的故事,但她知道我没辜负她的期望。”他轻声说,阳光落在照片上,像母亲温暖的手,轻轻抚摸着他掌心的老茧。 现在,黄旭华依然坚持每天学习新知识,他说“核潜艇技术一直在发展,我不能落后”。 偶尔有人问他,隐姓埋名三十年值不值,他总会指着窗外的核潜艇模型:“你看,这就是我的答案——国家强大了,老百姓能安心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这份家国情怀,就像他掌心的老茧,历经岁月打磨,却愈发清晰厚重。 信息来源: 光明网《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深潜”功名三十载,志探“龙宫”一痴翁》 中国军网《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不言悔》 中国网《黄旭华:我为祖国深潜》 北京日报《他三十年未与父母团聚,为国“深潜”造出大国重器!》




![[呲牙笑]新来的“虎式”,看上去真不小——1943年,东线,别尔哥罗德西北15公](http://image.uczzd.cn/1497369983104333852.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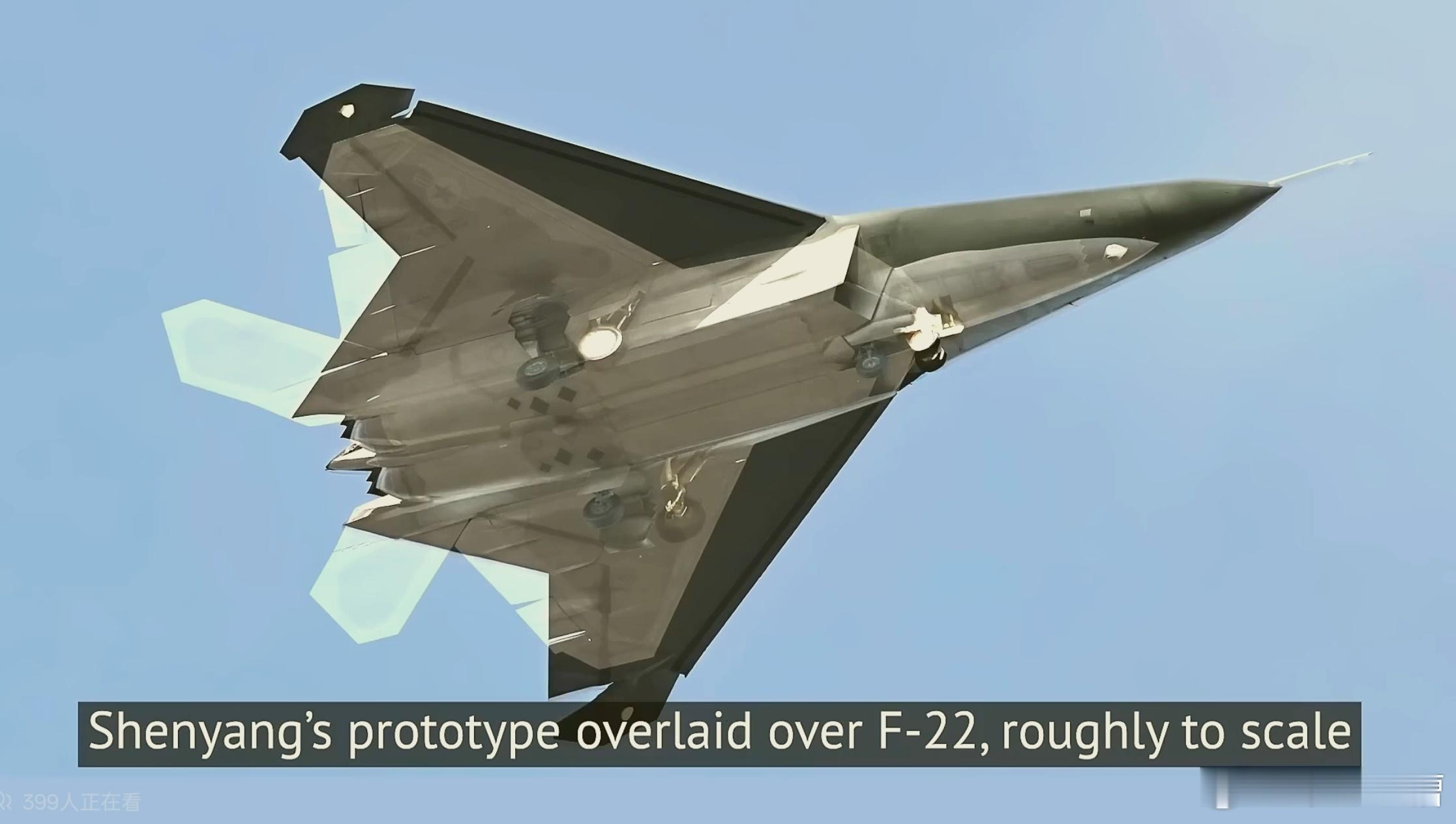



![美国准备向巴基斯坦出口AIM-120C8或D3空空导弹[666]这是看巴基斯坦](http://image.uczzd.cn/14046335688551071743.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