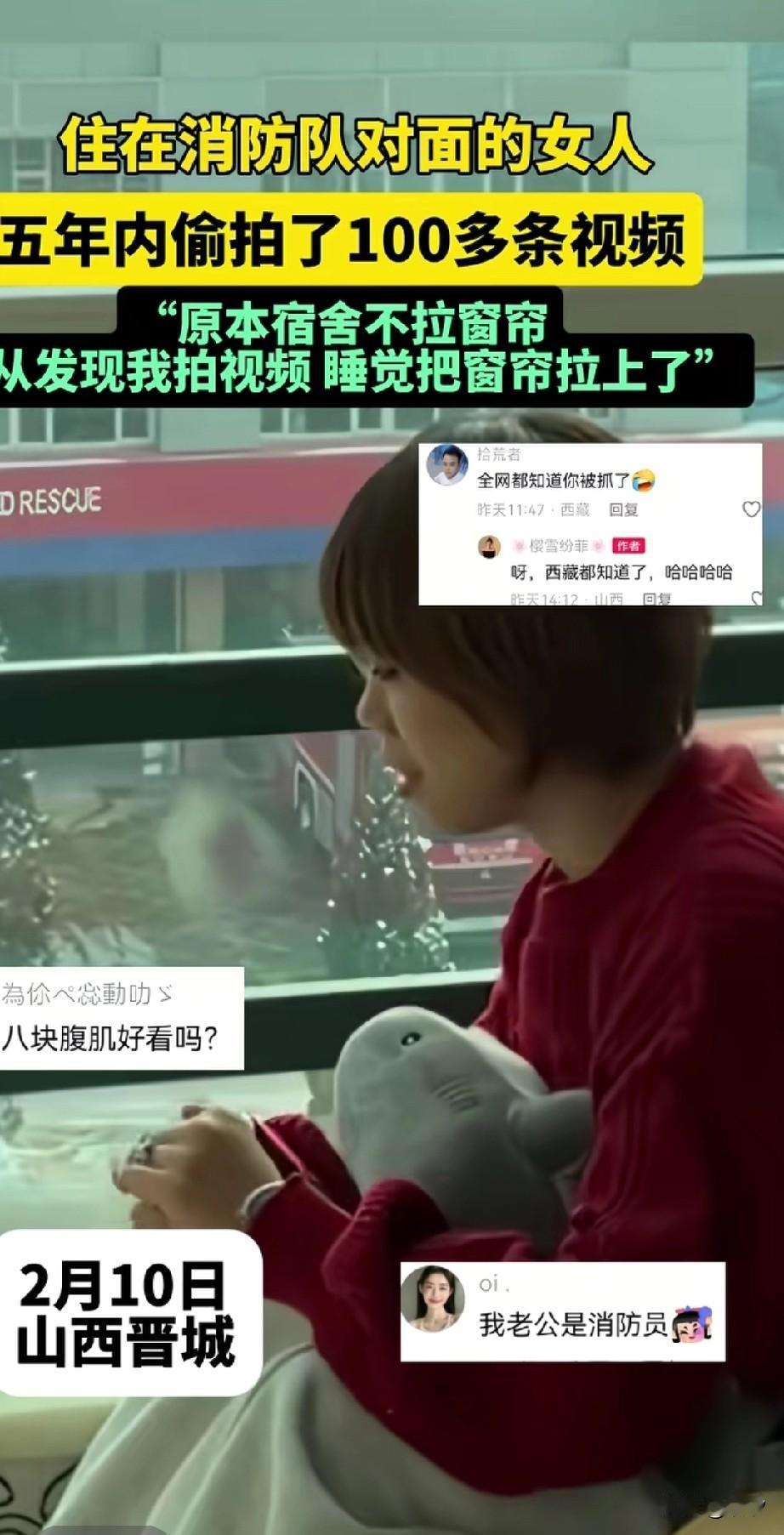1975年,她用4.5万公款包养了7个情夫,然而,整整十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没想到,最后竟死在一个男人手里,为什么? 1975年,江苏如东马塘镇的蝉鸣撕心裂肺,镇上人盯着汤家新到的“的确良”衬衫直咂舌。 那雪白料子摞起来足有半人高,够全镇姑娘媳妇穿三年。 街坊们背地里啐道:“汤家二丫头真成了‘汤二侯’!” “侯”是戏称,可汤兰英当得起。 当邻居为一口白米饭精打细算时,她家米缸里的大米喂猪都嫌糙,得雇人舂过才入口。 当主妇们攥着布票排队扯花布,她上海定制的衬衫已论打买,一天换三套跟走马灯似的。 最扎眼的是八块上海牌手表,在蓝灰制服海洋里闪得人眼疼。 “这哪是过日子?简直是活神仙!” 杂货铺王婶酸溜溜嘀咕,没看见汤兰英正用公家支票签下“海蜇皮一百斤”。 那墨迹未干的纸页飘落在信用社积灰的地板上。 可没人想到,这座“神仙窟”地基早已被蛀空。 十六岁在建筑站做会计时,汤兰英第一次伸手捞钱就被逮住。 “小孩子不懂事嘛。” 领导眼皮都没抬,丢给她一句轻飘飘的话。 处分?不过是丢了饭碗。 她舔着嘴唇笑了。 调到蔬菜大队再贪几百块,补上窟窿照样太平无事。 两次侥幸像野草在她心里疯长:“只要钱捂得紧,天塌下来有人顶!” 1965年进马塘信用社才是她真正的狂欢。 银行财政合并,监管形同虚设。 她左手捏公章右手拨算盘,支票簿成了自家提款机。 “存根?撕了喂鸡呗!” 她对同事嬉笑,钞票流水般淌进衣柜夹层。 十年间四万五千块没了踪影。 那年头工人月薪三十块,这笔钱够买一千四百年的口粮! 钱堆成山,寂寞更难熬。 丈夫远在苏州当兵,高额津贴反倒成了绝佳掩护。 汤兰英把家改造成温柔陷阱。 “李科长尝尝这鲥鱼,刚从长江捞的!”县委书记吃得满嘴流油。 “王局长试试这块表?”供销社主任腕上换了瑞士机芯。 七个男人轮番登场。 有手握审批权的干部,有垂涎美色的职员。 她解开衬衫第三颗纽扣,换来一次次查账放行。 某次突击审计,信用社主任甚至亲自打电话:“汤会计啊,赶紧装病去上海躲躲!” 1975年秋雨绵绵,第七任情夫老范盯着桌上新买的貂皮大衣脸色铁青。 “这月都第五件了,”他摔碎酒杯,“你当自己是慈禧太后?” 汤兰英慵懒地翘着脚涂指甲油:“急什么?明天还有批太湖大闸蟹……” “钱呢?”老范猛然揪住她头发,“信用社账上早空了!你当我瞎?” 窗外惊雷炸响,汤兰英这才看清他眼底翻涌的贪婪。 十年富贵喂大的毒蛇,此刻亮出了獠牙。 三个月后,县银行行长办公室烟雾弥漫。 “叔,您可得救我!” 汤兰英额头抵着冰冷地砖,“那些钱我都用在革命事业上了!” 老行长抖开举报信冷笑:“老范把你送我的茅台全吐出来了!1965年到现在,你抹掉四万五,信用社只剩九千库存,怎么?打算让全县储户喝西北风?” 算盘珠子噼啪爆响。 十年假账在阳光下现出原形,空白支票、伪造印章、拆东墙补西墙的窟窿…… 当公安冲进汤家时,八块手表早换成金条熔进马桶水箱。 1977年7月24日,如东中学操场挤得水泄不通。 汤兰英五花大绑跪在烈日下,胸前木牌写着“贪污犯汤兰英”。 人群突然骚动,老范戴着镣铐站在警戒线外,眼神像淬毒的刀。 “砰!” 顿时,一声枪声惊飞满树麻雀。 汤兰英向前扑倒时,听见围观者议论:“听说她死前喊冤,说当年挪两百块就该坐牢……” 马塘镇从此再无人见过那个把衬衫熨得笔挺的女人,唯有信用社斑驳墙壁上,一道陈年刀痕刻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当第一笔公款滑进私囊时,子弹就已上膛。 主要信源:(铜川市人民检察院——七十年代最大的女贪官,东窗事发,原因是她的一个情夫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