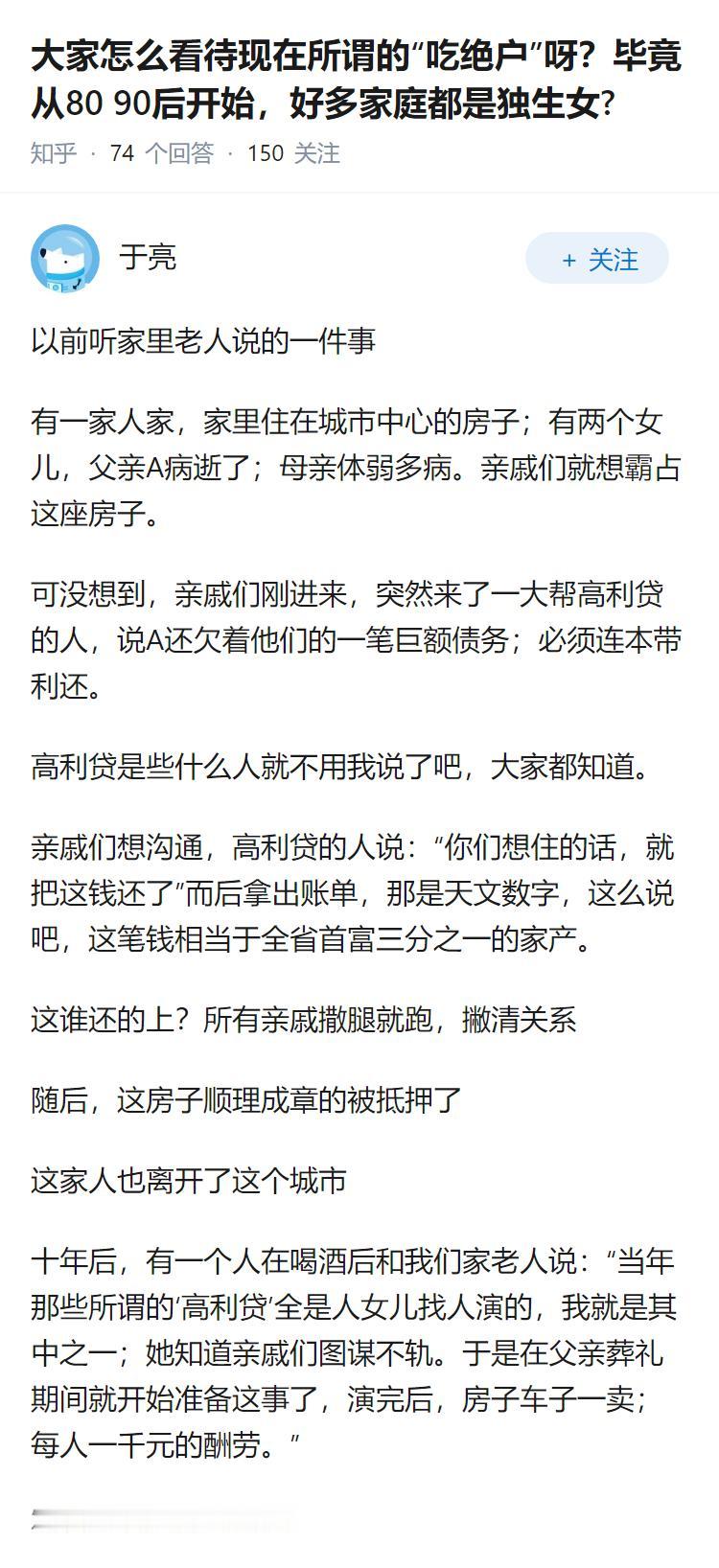1960年,乐会县的1位老农何世富“油尽灯枯”,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喊来妻子曾国彩,讲:“我的许多战友在京当官,我由于犯了错误,才脱离了红军。”曾国彩听后,气愤极了,喊:“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何世富的秘密,得从1930年说起。 那年他二十岁,家住乐会县中原镇,父母早亡,靠给地主放牛糊口。 琼崖革命风起云涌,共产党在村里办夜校,讲“打土豪分田地”,他听得热血沸腾,连夜跑到区委报名参军。 他编入琼崖工农红军第三团,因识字、机灵,很快当上班长,跟着冯白驹的队伍在万泉河两岸打游击。 那时的何世富,是团里的“神枪手”,能单手打落飞鸟。 也是“突击手”,每次攻碉堡都冲在最前。 而战友们记得,他总把干粮让给伤员,自己啃芭蕉根充饥。 可这“不怕死”的劲头,在1932年戛然而止。 1932年,国民党对琼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何世富所在的三团被围在母瑞山,断粮七天七夜,战士们靠吃野果、观音土撑着。 那天,何世富奉命带一个班突围,去乐会县找地下党送信。 可刚出山口,就撞上国民党巡逻队。 子弹扫来,他左腿中弹,班长职责让他不能倒下,咬着牙把信塞进鞋底往回撤。 可他没料到,等他拖着伤腿回到母瑞山营地,队伍已经转移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他像没头苍蝇般在山林里转,腿伤化脓,差点病死。 等他拄着木棍找到乐会县委,得到的却是“何世富同志擅自脱离队伍,按逃兵论处”的通报。 他找过政委申辩,可当时情况混乱,没人能证明他的任务。 更让他心寒的是,有战友私下说:“腿伤了就开小差,算什么红军?” 被“除名”后,何世富没脸回原部队,也不敢回村见父老。 他一路乞讨到万宁县,给地主当长工,住牛棚,吃残羹剩饭,腿伤好了,心却结了疤。 1940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逃荒到乐会县的曾国彩。 姑娘家父母双亡,在村里给人做针线,人长得清秀,性子也倔。 何世富没敢提自己的“红军”身份,只说“老家遭了灾,来讨口饭吃”。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曾国彩看他人老实,肯下力,就嫁了。 婚后,何世富在村里租了三亩薄田,起早贪黑种地,曾国彩纺线织布,小日子虽穷,却也安稳。 那时乐会县还有“还乡团”,专抓“通共”的,他怕万一被查出来,不仅自己活不成,还要害得妻儿被戳脊梁骨。 曾国彩也真信了他是“普通佃农”。 她只记得,丈夫话少,干活不惜力,每年交完租,剩下的粮食刚够吃,从没见他跟外人来往,更没提过“当官”“战友”这些词。 1960年,何世富突然病倒,咳嗽带血,县医院说是“痨病晚期”,没法治了。 他躺在炕上,看着妻子忙前忙后,想起当年在母瑞山,战友们也是这么照顾伤员的。 他叫来曾国彩,断断续续讲完自己的经历。 曾国彩听完,气得浑身发抖。 她想起这三十年的苦,生大儿子时难产,差点死在炕上,何世富只说“没钱请接生婆”。 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揭不开锅,他宁肯自己啃树皮,也不肯去“找战友帮忙”。 村里人笑话她“嫁个穷光蛋”,他从不辩解,只说“我命不好”。 “你骗我!你明明有那么多当官的战友,为什么不找他们帮忙?你让我跟孩子跟着你受了一辈子罪!” 曾国彩的眼泪决了堤,把积攒半生的委屈全倒了出来。 何世富望着妻子,没辩解,只说:“我犯了错,没脸找他们。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我这‘回头’,来得太晚了。” 何世富走后,曾国彩越想越气,跑到公社反映情况。 公社书记听说“老农是红军”,不敢怠慢,连夜翻查乐会县革命史档案,又派人去北京找何世富的“战友”。 “这何世富,确实是琼崖纵队的班长,1932年送信时与队伍失散,被误记为‘脱队’。” 北京来的调查员带来消息,还带来一位老将军的信。 正是何世富当年三团的政委,如今已是某军区副司令员。 信里写着:“世富同志是条好汉,当年送信负伤,我亲眼所见。他不是逃兵,是英雄。” 曾国彩捧着信,她想起丈夫临终前那句“我犯了错误”,原来不是“开小差”,是“被误会”。 她又哭又笑,把信贴在胸口,觉得这三十年的“气”,全化成了“悔”。 何世富的坟,后来迁到了乐会县革命烈士陵园。 陵园的老管理员说:“他不是逃兵,是没被记住的英雄。” 曾国彩活到八十岁,临终前对儿子说:“你爹不是骗子,是怕连累我们,才把‘红军’两个字藏了一辈子。” 她让儿子把那封信,和何世富的破军帽,一起放进棺材。 这世上,有些秘密,藏的是愧疚,也是担当;有些“错误”,是时代的误会,也是个人的坚守。 主要信源:(微信公众平台——【红色记忆】何畏在仪陇古楼寨‖胡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