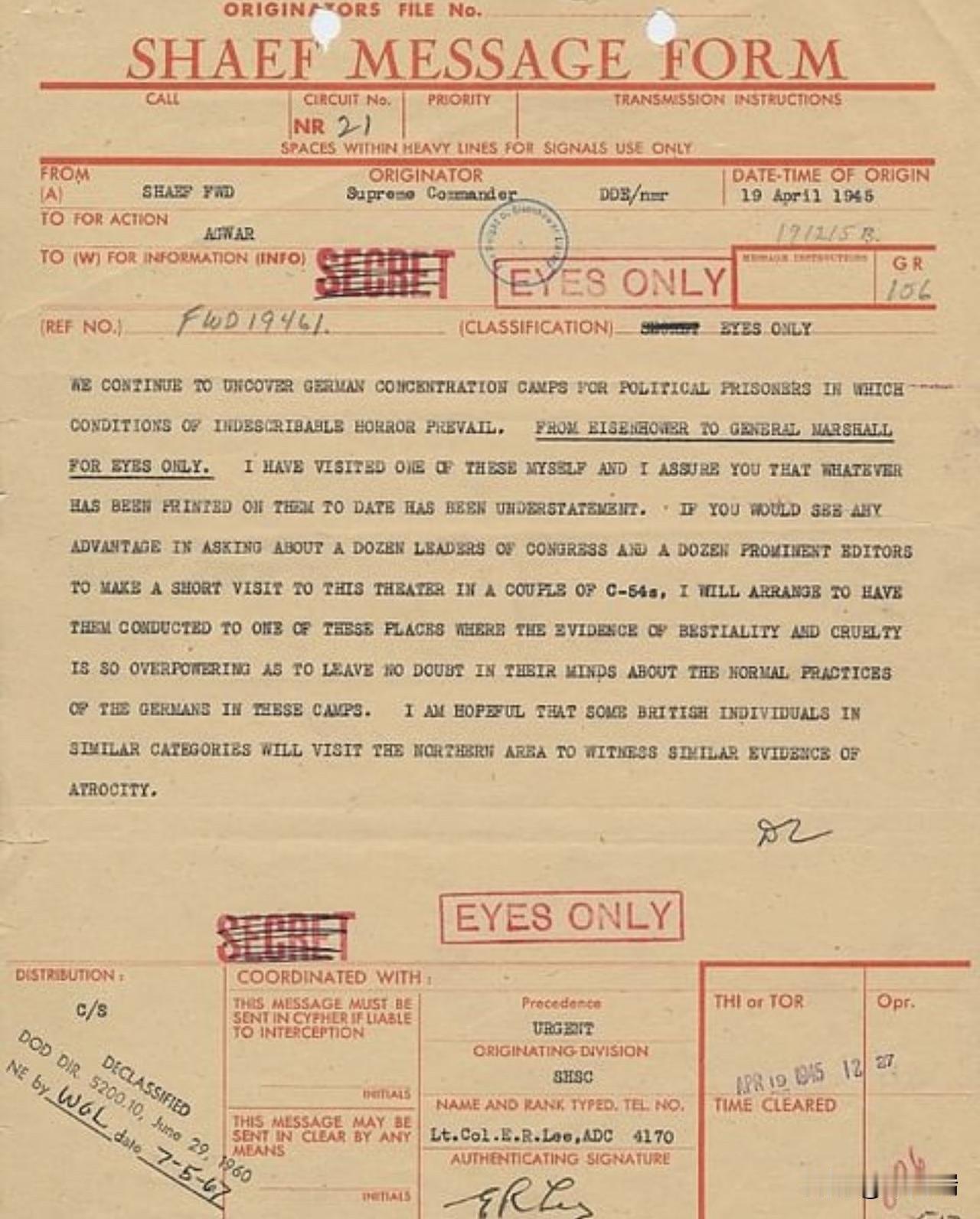1967年9月,60岁的孟小冬告别香港十年独居岁月,应义姐姚玉兰之邀迁居台湾,自此在台北东门町开启了人生最后十年的隐居生活。 当时,孟小冬做出迁居台湾的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966年香港受左派运动波及,社会动荡让她倍感不安,此前大陆方面虽多次递来橄榄枝——1963年马连良、裘盛戎访港时,曾转达周总理的问候与邀请,愿以百万港币稿费请她回内地传承余派艺术,但她顾虑时局,始终未应。 最终在姚玉兰与陆京士的反复劝说下,她放下心中芥蒂,选择台湾作为晚年归宿,而台湾当局的不闻不问,也让她得以真正远离政治纷扰,安心静养。 孟小冬的台北居所,是东门町一处普通的租屋,她执意不肯入住陆京士以她名义购置的房产,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回忆,孟小冬早年算命得知不宜用本名置业,便始终恪守这份执念,宁可租房度日,也不愿破戒。 租屋内设着一方佛堂,是她每日晨起诵经的地方,自香港带来的三条宠物犬,成了她独处时最贴心的陪伴,除了偶尔下楼遛狗,她几乎足不出户。 日常的消遣简单而规律,晨起诵经礼佛,午后与前来探望的亲友打牌闲谈,夜晚便守着一台电视消磨时光,尤其偏爱古装剧,曾因欣赏演员蓝琪的古典气韵,托戏曲评论家丁秉鐩牵线相识,两人相谈甚欢,尽显她藏于严肃外表下的柔软。 她对新鲜事物亦有好奇,偶尔会模仿流行歌曲,引得众人发笑,这份鲜活,与舞台上那个唱腔端严厚重的须生形象判若两人。 生活里的孟小冬,带着几分不谙世事的笨拙,却也被浓浓的温情包裹。 杜维善记得,她始终学不会用煤气炉加热食物,夜里饿了便会打电话向亲友求助;她偏爱北方吃食,台北的同庆楼叉子火烧、东来顺涮肉,都是她的心头好,每年过年,杜家都会依着她的习惯包饺子,而非南方的米饭炒菜。 姚玉兰与养女杜美霞,是她晚年最坚实的依靠,姚玉兰几乎每日都会登门相伴,孟小冬常说“她往我这里一坐,我就定心,她一天不来,我这日子就不知怎么过”,而杜美霞更是日日照料她的起居饮食,处理内外琐事,成了她最信任的人。 杜府上下皆称她为“妈咪”,梨园后辈则尊她为“老师”,每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的生日,亲友与弟子都会齐聚为她祝寿,1976年她六十九岁大寿时,港台弟子同台清唱,她难得展露笑颜,只是兴奋过后,身体便难承其累,这份欢喜,也成了她晚年为数不多的亮色。 即便远离舞台,孟小冬对余派艺术的执念从未消散,这份坚守,也让她成为台湾梨园后辈心中的灯塔。 丁秉鐩作为她的至交与资深剧评人,曾无数次慨叹她的艺术造诣,称她演唱《洪羊洞》时,“尺寸虽快,而腔如天马行空,变化有致,气氛上痛诉衷肠;跌宕婉转处,凄凉低迷,完全是人之将死的诀别之态,令人不忍卒听,堪称感人的绝唱。” 他回忆,孟小冬虽不再登台,却会偶尔调嗓,哼唱余派名段,嗓音依旧清亮醇厚,只是始终不肯接受任何演出与教戏的邀请。 但对诚心求教的后辈,她却从未吝惜指点,余派后辈姜竹华曾忆起,自己登门请益时,孟小冬会逐字逐句纠正她的唱腔与咬字,从气口把控到身段细节,皆倾囊相授,那份严谨与细致,让她受益终身。 钱培荣、赵培鑫等弟子,也常赴台受教,她留下的说戏录音,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珍贵资料,杜维善坦言,“她虽未正式开科收徒,却让余派的火种,在台湾生生不息”。 晚年的孟小冬,始终被顽疾缠身,长期抽烟让她的呼吸系统饱受折磨,肺气肿与哮喘相伴多年,苦不堪言。 丁秉鐩曾劝她调理身体,她却无奈地说:“我按你的法子治也没效,我是另一种病因的哮喘病,肺气肿,是根本不能治的。” 杜美霞回忆,她的哮喘时常发作,后期连日常呼吸都变得艰难,医生多次劝她住院,她却始终不愿,只说“等我考虑考虑”,骨子里的倔强,从未因年岁与病痛消减。 1977年春节过后,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治标药物全然失效,5月25日晚,一阵剧烈的哮喘让她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台北中心诊所,医生剖开喉管吸痰,仍未能挽回她的生命,次日午夜,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蔡康永对孟小冬的一段记述,那种亲历的落寞感,让人很是感慨—— 那是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地下一楼的鸿霖西餐厅,蔡康永的父亲当时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那里吃饭,年幼的他常被父亲带去,要陪着一桌一桌地跟父亲的朋友们打招呼。 那天父亲刚坐下,转头看到最里面长桌末端坐着一位穿灰色宽松旗袍的圆润老太太,过去打完招呼后回来告诉他,那是杜月笙的夫人,孟小冬。 蔡康永回忆说,自己虽是小孩,但因为是上海家庭,已听人提过杜月笙大名,只是当时颇感头晕,一心以为杜月笙是极遥远的书中传奇人物,怎么会这么平常就能在餐厅随便遇见他的太太,甚至还在心里嘀咕“杜月笙家人啊,起码也该有十个八个保镖随侍在旁吧”。 蔡康永坦言,自己模模糊糊记得再转头看看老太太,想看出点“冬皇”派头,但只记得望去一片影影绰绰,灰扑扑的,实在看不出“冬皇”的架势。 他最后感慨,“我是小孩,那时还不懂得:无论你是哪界的帝,哪界的皇,一被岁月搓洗,都只能渐渐化为灰扑扑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