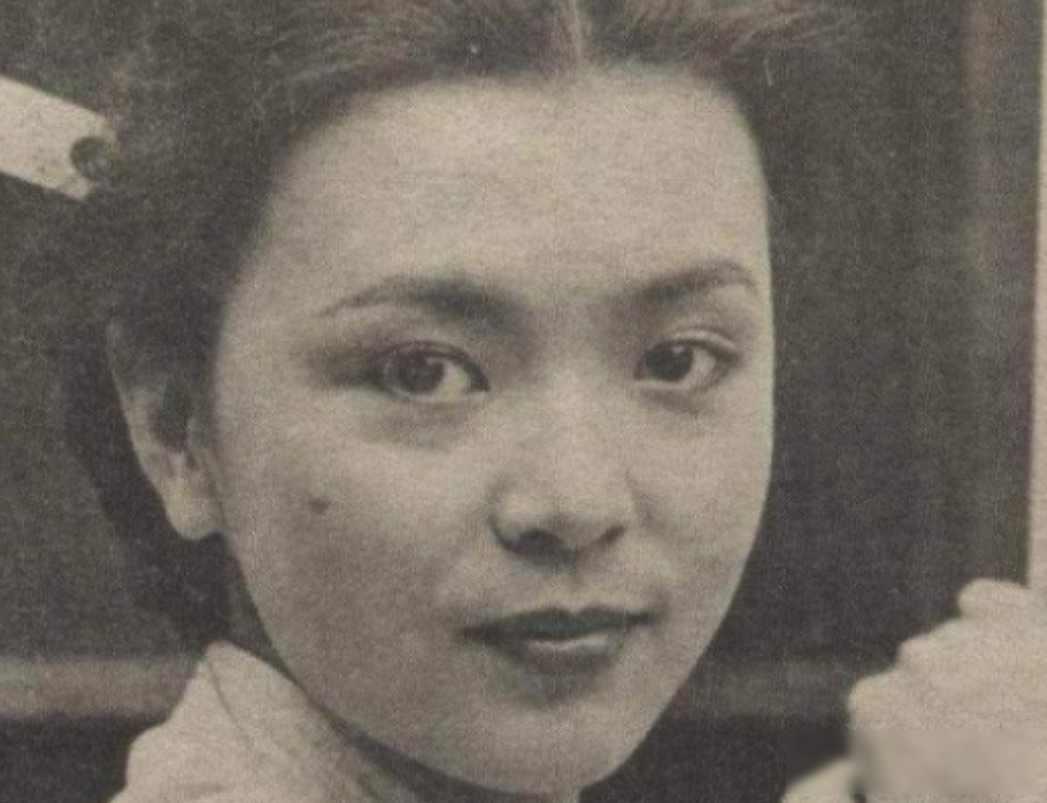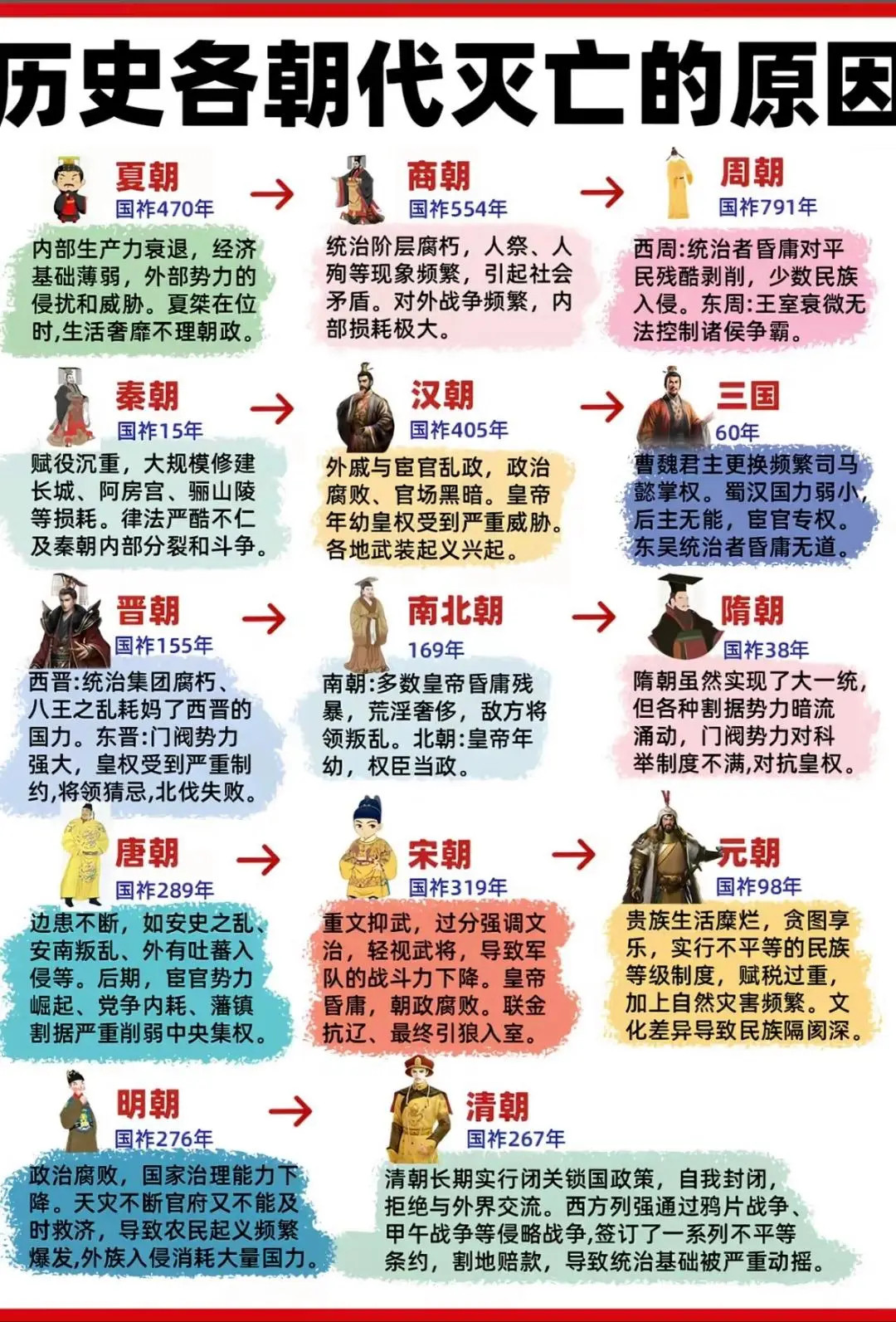1935年,一风尘女子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鸨却冷笑道:“想带她走?没门!” 1935年的上海,霓虹灯亮着,一间雕花阁楼里,琵琶声断断续续,弹琴的姑娘叫潘素,才二十岁,指甲上的月牙痕让弦勒得发白,她原是苏州望族出身,父亲一走,继母就把祖宅卖了,把她送进了十里洋场。 琴师们说她弹《塞上曲》时指尖磨出了血,可总有人愿意为她花钱,有个穿绸衣的老太太总坐在角落数银元,人叫她老鸨,潘素每天得陪八桌客人,可琴房那盏油灯从没灭过,夜里她对着母亲留下的《芥子园画谱》发愣,墨迹在纸上慢慢散开,像她心里压着的那点东西,怎么也化不开。 这天夜里,琴弦断了三根,弹到《阳关三叠》里“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句,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忽然说,姑娘知道这是王维的离别曲吗,潘素一愣,他接着报了名字,张伯驹。 第二天他再来,怀里抱着厚厚一摞《红楼梦》程乙本,潘素瞧见他手指沾着墨,也像她那样在书页边上写写画画,两人聊到很晚,张伯驹忽然说,明天我带钱来。 老鸨数着钞票,冷笑了一声,臧处长每月包三天,你以为这是戏院里买票吗,潘素被锁进一间挂着暗红窗帘的屋子,窗外下着细雨,凌晨三点,钥匙转了,张伯驹拎着左轮手枪,肩膀上搭着她的织锦旗袍。 北平的冬天冷得人直打哆嗦,张伯驹妻子家里闹着分家产,他把田产全换了钱,给潘素请了画师,一九四一年那回绑架,绑匪要的是《游春图》和《平复帖》,潘素连夜把陪嫁的翡翠镯子卖了,存折一页一页撕下来,拿钱走,画不能动。 晚年夫妇住在什刹海的小院,潘素画的山水挂在西厢房墙上,有年轻人问她,当年怕不怕,她笑着指了指画里的远山,怕,可总得有人守着这些山。 文物捐赠那天,张伯驹在故宫门口买了两碗杏仁茶,他们谁也没开口,就那么看着太和殿的金瓦,像当年听琵琶时,静静对望的两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