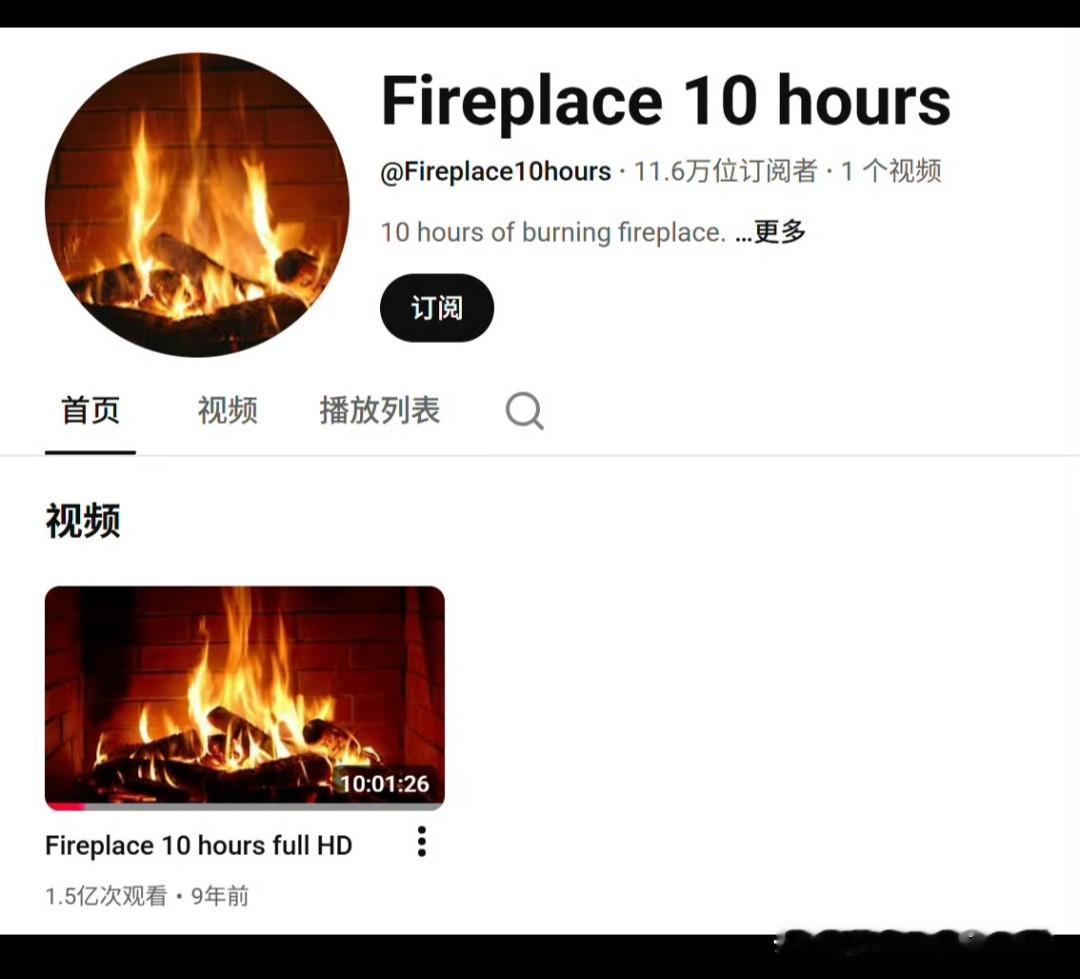1973年,知青刘朝旭被推 荐上大学,临走时去找队长告别。没想到,在他家窗前,听到里面队长说:“朝旭要走了,去给他借点路费吧!”队长媳妇说:“你上次卖了羊皮袄才凑够给知青买锅的钱,现在让我上哪儿借!” 1973年的山西临汾,黄土塬上的风卷着沙,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刘朝旭攥着那张印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站在队长郭满仓家的窑洞前,脚边的黄土被他碾出个小坑——明天就要离开这片待了四年的土地,他总得跟这位把他当亲儿子疼的郭叔告个别。 窑洞的窗户糊着麻纸,借着里面昏黄的煤油灯光,能看见郭叔蹲在炕沿上抽旱烟,烟锅“吧嗒吧嗒”响。刘朝旭刚要抬手敲门,就听见郭叔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带着点沙哑:“朝旭明儿就走了,去给他凑点路费,北京远,路上得花钱。” 炕那头传来郭婶的叹息,声音压得低,却字字清晰:“你忘了?上月知青点的铁锅裂了,你把过冬的羊皮袄拆了卖了,才凑够钱买新锅。现在村里谁家不紧巴?让我上哪儿借去?” 刘朝旭的手僵在半空,鼻子突然酸得厉害。他想起四年前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刮着风的春日,绿皮火车在土坡下停住,他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下车,放眼望去全是望不到头的黄土,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同行的知青有的当场就哭了,他咬着牙没哭,可心里的慌,比没底的窑洞还空。 是郭叔赶着驴车来接他们的。那汉子脸膛黑得像被太阳烤过的炭,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全是褶子,露出两排结实的牙:“娃娃们别怕,到了这儿,咱就是一家人。”他说这话时,手里还攥着根赶驴的鞭子,鞭梢上沾着点黄土,却让人莫名踏实。 知青点的窑洞漏风,郭叔带着社员们用黄泥糊了三遍;冬天冷得伸不出手,他把自家炕上铺的羊毛毡拆了半块,悄悄塞到知青点的灶膛边;刘朝旭水土不服拉痢疾,郭婶守在他炕边,用粗瓷碗熬小米粥,熬得黏糊糊的,上面漂着层米油,说“喝了养人”。 那年头粮食金贵,郭叔家的口粮也紧巴,可每次分了新粮,他总让儿子郭小军送来一瓢高粱面。刘朝旭后来才知道,那是郭叔把自家配额里的细粮换成了粗粮,省下的全给了他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有次他看见郭小军盯着知青点的玉米饼子直咽口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下,偷偷把饼子塞给孩子,转头就红了眼。 去年冬天,知青点的铁锅被冻裂了,大冷天的没法做饭。郭叔没吭声,第二天就把他那件穿了十年的羊皮袄脱下来,让去镇上赶集的人捎着卖了。那袄子是郭婶的陪嫁,里子的羊毛厚得能攥出水,平时郭叔宝贝得很,只有最冷的时候才舍得穿。刘朝旭看着郭叔冻得通红的脖子,想说啥,却被他一瞪:“娃娃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一件破袄算啥。” 此刻听着窑洞里的动静,刘朝旭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黄土里,洇出一小片湿痕。他听见郭叔磕了磕烟锅:“去问问东头你三婶,她家刚卖了鸡蛋,兴许能匀点。就说……就说我郭满仓借的,开春卖了新粮就还。” “那你开春穿啥?”郭婶的声音带着哭腔,“你那老寒腿,离了羊皮袄咋熬?” “熬熬就过去了。”郭叔的声音顿了顿,“朝旭是咱村飞出去的金凤凰,可不能让他在路上受委屈。” 刘朝旭再也站不住,转身往知青点走。黄土塬上的风还在刮,可他觉得心里头烧得慌。他摸了摸怀里的录取通知书,突然打定主意——明天走之前,把自己攒的那点钱全留下,再把那件从家里带来的蓝布褂子留给郭叔,褂子是新的,比羊皮袄薄,可总比没有强。 第二天一早,郭叔果然揣着个布包来送他。布包里是五块钱,还有几个煮鸡蛋,蛋壳上还沾着点草屑。“路上吃,垫垫肚子。”郭叔挠着头笑,眼角的皱纹里全是风霜,“到了北京好好念书,给咱村争光。” 刘朝旭接过布包,感觉有千斤重。他对着郭叔深深鞠了一躬,想说谢谢,喉咙却像被堵住了,啥也说不出来。火车开动时,他看见郭叔还站在土坡上,黑黢黢的身影在黄土背景里,像棵扎得很深的老槐树。 后来刘朝旭在信里得知,郭叔开春真的没穿羊皮袄,靠喝姜汤硬扛过了倒春寒。再后来他回村里探望,特意给郭叔买了件新的羊皮袄,里子的羊毛又厚又软。郭叔穿着新袄,拉着他的手在窑洞前晒太阳,说:“我就知道,咱朝旭是个有心的娃。” 黄土塬上的风依旧年复一年地刮,可有些东西,比风更长久——比如那句“到了这儿就是一家人”,比如那件被卖掉的羊皮袄,比如藏在贫瘠岁月里,沉甸甸的情意,像塬上的老槐树,根扎得深,叶长得旺,能挡得住所有的风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