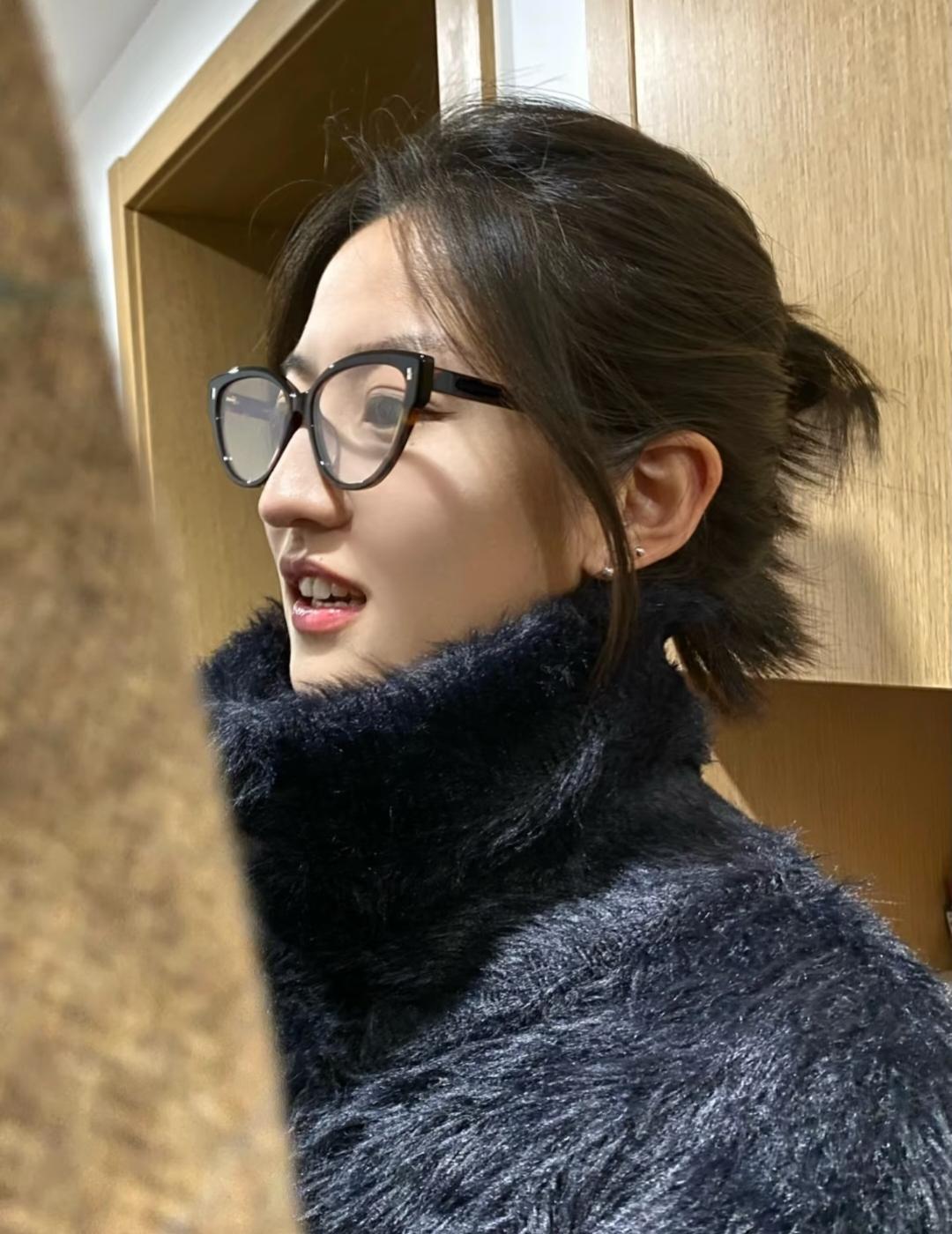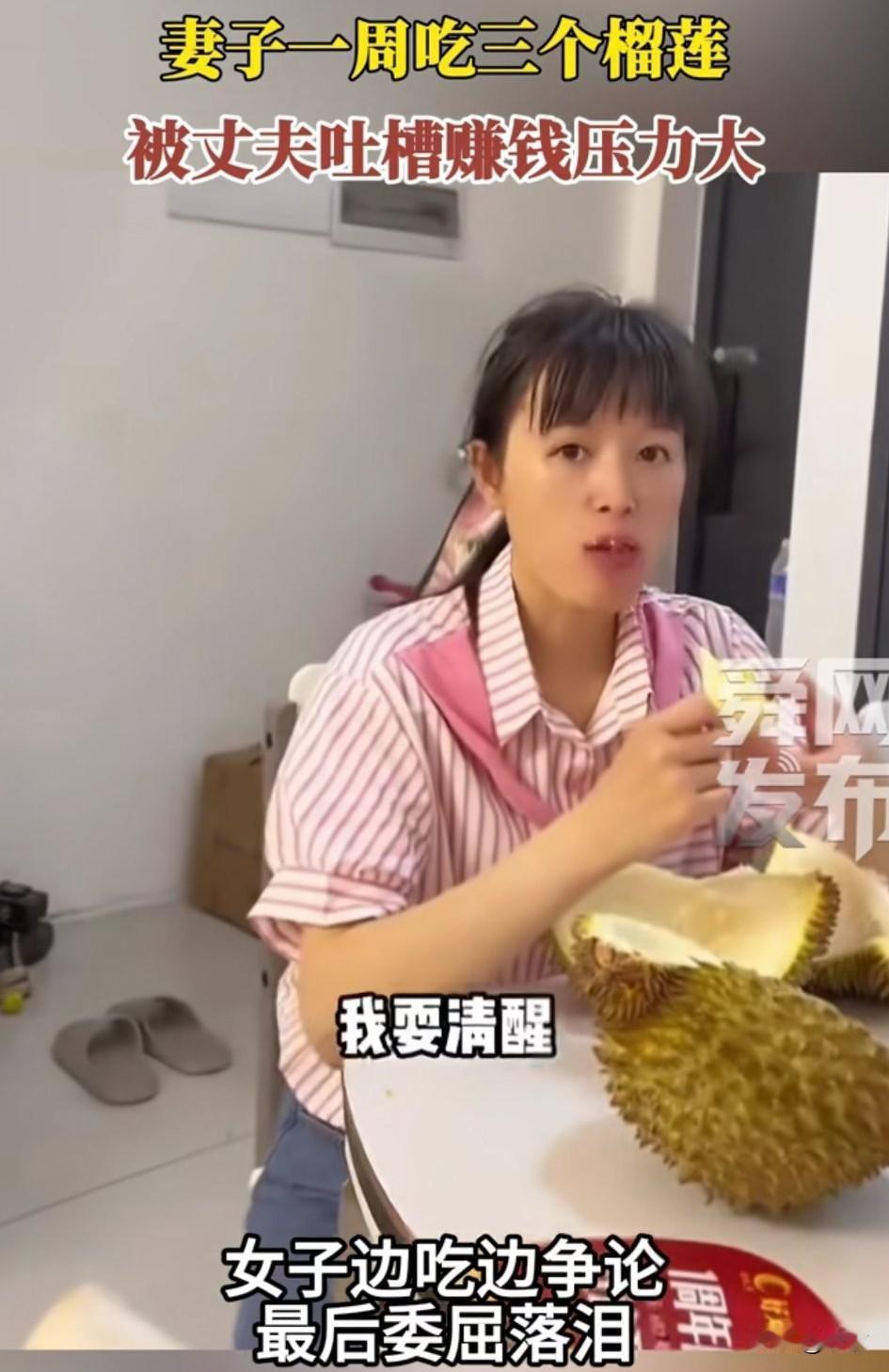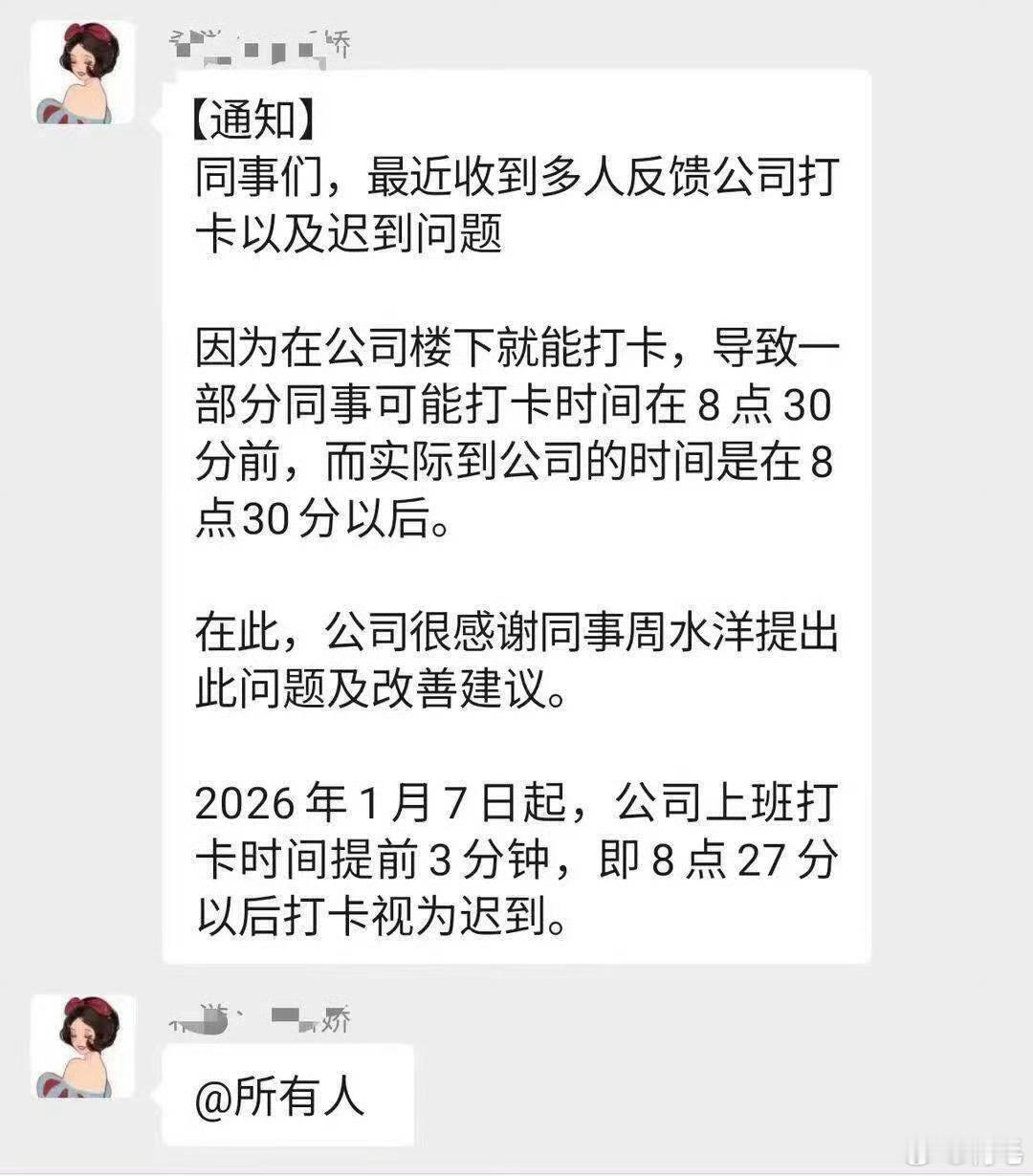昨天,儿子终于收到了心心念念的录取通知书。上午邮递员就送到家了,儿子在外面学车,叮嘱让他自己拆开。那个牛皮纸信封就放在茶几上,阳光透过纱窗照在上面,烫金的校徽若隐若现,像藏着个会发光的秘密。我每隔十分钟就要去瞄一眼,生怕它长腿跑了似的。 中午他回来,我正剥蒜呢。他进门,鞋带散了,也不急着系,就那么拖着,先去茶几那儿转了一圈,手指头在信封上轻轻划拉了一下,像碰什么易碎品。然后他居然转身进了厕所,水哗哗响。我在厨房,心里那叫一个急,这孩子,怎么这么能憋呢。 他从厕所出来,甩着手上的水珠,才不紧不慢地拿起信封。空调外机嗡嗡响,窗外有只知了扯着嗓子喊。他撕开封口,特别小心,一点声儿都没有。抽出那张纸,他低头看了好一会儿,背对着我,一动不动。我手里攥着半头蒜,也跟着定在那儿。 然后他肩膀忽然就塌下去了,不是松口气那种塌,是像跑了很久很久,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的样子。他转过身,脸上没啥狂喜的表情,就是有点愣,还有点……空荡荡的。他把通知书递给我,嗓子有点哑:“妈,你看。” 我接过来,手指头摸着那凹凸的印章,心里头滚过好多话,最后就“诶”了一声。他走到阳台,背对着客厅,看外面。老半天,才闷闷地说:“邮递员送来的时候,说什么没?” “就说‘恭喜啊’。”我答。 “哦。”他又不说话了。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光溜溜的地板上。我心里那点高兴,不知怎么,掺进了一丝说不清的酸。这孩子,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晚上他爸打电话来,嗓门大得不用开免提:“好小子!给老子争气了!想要啥奖励?爸给你买!”儿子对着手机,嗯嗯啊啊地应着,笑是笑着,可笑意没到眼底。挂了电话,他盯着黑屏的手机,发了会儿呆。 夜里我起来喝水,看见他房门底下还透着光。轻轻推开一点缝,他坐在书桌前,台灯照着他半边脸。那张通知书就摊在桌上,他没看,手里捏着个旧魔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转得磕磕绊绊的。书架上那排做完了的、画得花花绿绿的习题册,在阴影里静悄悄的。 我忽然想起他初三那年,也是这样一个晚上,他因为一道物理题死活解不出来,气得把草稿纸全撕了,撕得粉碎,然后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我没进去,就在门外站了一会儿。那时候觉得,这孩子心里的劲儿啊,太足了,怕他绷断了。 现在,劲儿好像一下子泄了。或者说,是那个绷得太紧的目标,突然达到了,眼前一下子空了,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了。 第二天早上,他睡到快十点。起来后,晃晃悠悠走到客厅,看见通知书还放在茶几上,他拿起来,折了两下,塞进了自己那个旧书包的夹层里,拉上拉链。那动作,随意得像塞一本不常用的课本。 “妈,”他趿拉着拖鞋往厨房走,“早上吃啥?我饿了。” 锅里熬着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窗外的阳光,跟昨天一样,正好又落在那张空了的茶几上。
河南平顶山,男子家门口突然来了一批民警,他们全副武装,表情严肃,男子妻子吓得不敢
【4评论】【7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