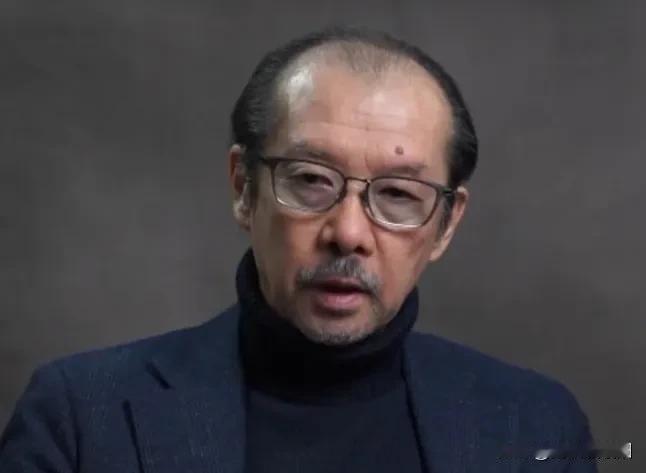1937年,日本“淫魔少将”定下人生目标,“侵犯1万名少女,还必须得是处女”,临死前他的下半身被打烂,结局让人“解气”。 在这份尘封已久的档案里,1937年的那个冬天格外刺骨,不仅仅是因为天气,更因为人性的温度降到了冰点以下。 关于东口义一这个人,市井传闻里他是立誓要糟蹋“一万名少女”的恶魔少将,甚至传言他最后落得下身溃烂、惨叫着死去的“现世报”结局。这种叙事固然让人解气,仿佛苍天有眼,恶人终有天收。但当我们拨开情绪的迷雾,走进中央档案馆那份代号“38联队2大队”的笔供原文时,会发现一个比传说更冰冷、更令人窒息的真实——那不是一个疯狂恶魔的独角戏,而是一群普通士兵合谋构筑的精密“地狱”。 在1937年12月14日的薄暮时分,那日后被冠以“淫魔”之名者,彼时不过是在下关车站附近悉心擦拭榴弹炮的一名上等兵。彼时,他们刚为一场名为“诠衡”的会议画上句点。时光的指针悄然滑过,这场会议的余韵,似在空气中微微荡漾,等待着后续故事的展开。这词听着文绉绉,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杀人放火后的“绩效评估”。或许正是为了犒劳这所谓的绩效,一场精心设计的诱捕开始了。 那是傍晚时分,村田曹长带着十个兵去敲中国百姓的门。他们没像野兽一样踹门,而是极尽虚伪地找借口:“皇军衣服脏了,需要妇女帮忙去洗。”这就好比披着人皮的狼在说谎,大冬天的晚上,哪有人去冰冷的江边洗衣服?但这蹩脚的谎言背后,顶着的是上了膛的步枪。 在那份1954年写下的供述中,并没有提及民间流传的“一万名处女”这种狂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一组让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数据:10名被押走的女性,年龄都不大,最小的怀里可能还抱着婴儿。她们被塞进了日军睡觉的宿舍地下室,不是正规的监狱,只有几条军用毛毯和满地稻草。而门口架着的,是冰冷的机关枪。 那一夜,乃至随后的是三天三夜,地下室变成了真正的修罗场。六十个人,是一整个作战分队的建制。整整六十个壮年士兵,轮流对十名手无寸铁的女性施暴。按照那个冰冷的统计,平均每位女性遭受了十八次非人的摧残。 这时候的东口义一在哪?他在供词里试图把自己摘干净:“我没有参与强奸。”确实,他没有在那张稻草铺上施暴,但他站在门口警戒。他是这台暴力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颗螺丝钉,他的枪口封死了受害者逃生的路,他的沉默是对暴行最大的纵容。即便多年后在战犯管理所,他和隔壁供述“机枪扫射2400人”的中野忠之寿相比,罪行的数量级似乎不同,但在把活人变成玩物、把杀戮当做工作的本质上,他们并没有区别。 比地下室更让人绝望的,是那天夜里的运输工具。在下关码头,每天进出几十趟运煤的卡车被征用了。为什么要用煤车?因为对于那时候的这支部队来说,把被蹂躏致死或者仅仅是看不顺眼的平民尸体运到江边倾倒,这玩意儿比挖坑埋人效率高得多。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留下的影像资料里,就有这么一辆煤车,锈迹斑斑的车斗里,一只戴着银镯子的苍白手臂无力地垂在外面,成了那个冬天最凄厉的无声控诉。 这就是历史最讽刺的地方。我们期待东口义一像传闻中那样“下半身被打烂”而死,期待一场血肉模糊的复仇。但现实是,他在太原特别军事法庭被判了18年。他活了下来,甚至看着下关车站重新通车,看着那座被他们蹂躏过的城市慢慢结痂、愈合。1978年,他死在东京,死因是肝癌,而不是众望所归的“天谴”。 至于那辆装满罪恶的煤车?1945年投降那会儿,它被码头工人推下长江泄愤。直到1998年清淤时才重见天日,车斗早就烂透了,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留下。不知道内情的工人们把它当成废铁,几斤几两称了,换回了几箱啤酒。 那辆车消失了,那个甚至可以说是“善终”的战犯也成了灰烬。甚至那些具体的哭声也早已消散在江风里。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翻看那份早已泛黄的笔供? 不是为了去验证那些诸如“一万名”的夸张数字,也不是为了意淫一场并不存在的惨烈报应来自我安慰。而是要警惕那每一个具体的细节:警惕那种能让六十个男人集体对罪恶麻木的制度,警惕那些把女性当成洗衣服工具继而当成发泄工具的谎言,警惕那些把运尸体看作运输煤炭一样平常的“效率逻辑”。 在档案馆那份笔供的封皮上,工作人员曾用毛笔写下“永志不忘”四个字。那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记住——当雪崩发生时,像东口义一这样站在门口只是“警戒”的一片片雪花,没有一片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