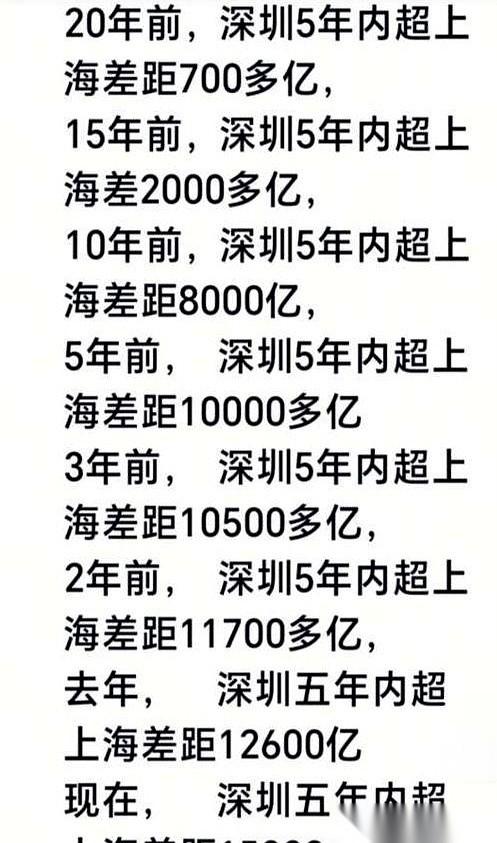1983年的严打,放在中国法治史和社会变迁史里看,是一段特殊又沉重的存在。 当时社会治安问题凸显,刑事案件数量激增,城市监狱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于是“注销城市户口、押送大西北劳动改造”的政策应运而生,这个政策既解了监狱爆满的燃眉之急,又给西部开发送去了免费劳力,在当时算是“一举两得”的设计。 但是对于那些被打上“重刑犯”标签的城市青年来说,城市户口被注销,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被连根拔起了,从被扔进戈壁荒漠的那一天起,往后的日子是什么样,结局如何,一切比他们预想的更加残酷。 注销户口这事儿,在当时不是说说而已,是写进中央文件的硬政策。 1983年8月中央出台的严打决定里,明确要求“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只要被判重刑,不管你是北京、上海的,还是江浙、京津的,户籍页上都会被盖上鲜红的注销印章,理由清一色是“因XX罪判处XX刑,遣送边疆劳动改造” 。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城市居民,成了没有籍贯的“异乡人”,而这一注销,往往就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 辽宁的大学生李晓光1983年因失手杀人被判死缓,户口一注销,再接到押往新疆的通知时,他说那种感觉“就像被家乡扫地出门,纯粹的放逐感” 。 更残酷的是,1984年还出台了“刑满释放人员留场就业”政策,明确限制大城市户籍人员返乡,就算服完刑,户口没了,原籍回不去,农场也不给落户,很多人直接成了“黑户”。 上海的陈建国原是工厂技术骨干,过失伤人被判无期,在戈壁种了15年树,1998年刑满时连身份证都办不了,想回上海买张火车票都没资格,最后只能留在农场当护林员,守着自己种的胡杨林过一辈子。 在当时,这些人的目的地,青海诺木洪、柴达木盆地、新疆若羌、甘肃三十里井子农场,鸟不拉屎,全是西北最苦的地方。 这些劳改点有个共同特点:海拔高、温差大、全是盐碱地。 夏天地表温度能飙到五六十度,脚踩在沙子上烫得直跳;冬天能冷到零下三十度,哈气成冰,风沙一刮,大白天都得点油灯。 第一批2400名江浙籍犯人坐了54小时闷罐车,下车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茫茫戈壁上几排土坯房,远处是光秃秃的雪山,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他们住的不是宿舍,是自己挖的“地窝子”——在地下挖个半掩体,铺点干草就是床,没供暖没通风,冬天冻得缩成一团,还容易煤烟中毒。 新疆若羌的劳改农场更偏,周围几百公里都是无人区,后来刑满留下的人聚居成了“上海街”,镇外沙包上的墓碑全朝着东南方,那是上海的方向。 那个年代,劳动改造根本不是什么“悔过自新的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高强度的苦役。 农场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五点吹哨起床,五分钟洗漱,五分钟整理内务,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牙具摆成一条线,五点半准时出工,一直干到晚上九点收工,一天劳动时长超过13小时 。任务定额高得吓人,每人每天要开垦半亩荒地,栽一百多棵沙棘,割几百斤苜蓿,完不成就要扣饭,连续三次没完成就得戴24小时“紧铐”,手腕磨得血肉模糊。 最苦的是挖排碱沟,戈壁上的土硬得像石头,一镐下去就留个白印,天津的李建国20岁因抢18块钱被判无期,在诺木洪挖了三年排碱沟,手掌震裂的伤口反复结痂,最后结成了厚厚的黑痂,几十年后还能摸到痕迹。 伙食标准也是低得可怜,农业单位犯人每月伙食费才13块钱,重体力劳动的每月也才15块,平时就是稀粥配咸菜,每周能吃一顿土豆烧牛肉就算“开荤”,半碗肉汤都能换半包烟 。 医疗条件更是形同虚设,得了阑尾炎只能打青霉素硬扛,要是得了高原肺水肿,得用拖拉机往一百多公里外的格尔木送,不少人没送到就断了气。 江浙籍的申某不堪忍受,半夜翻墙逃跑,结果在盐碱滩上迷了路,又冷又饿,三天后被发现时已经冻僵了,怀里还揣着没舍得吃的半块馍。 这些被放逐的人里,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他们的悲苦不全是因为劳动的艰辛,更多是身份的枷锁和未来的迷茫。 刑满释放后,不管是回不去的还是回去的,大多数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上海有个区摸底,一百多个回流的人里,只有十几个找到了正式工作,其他人要么蹬三轮,要么摆地摊,年纪不大就只能“内退”。 几十年过后,那些还活着的人,大多已经六十多岁,每年秋天都会自发回农场“探亲”,在废弃的黄土墙前合影,唱的不是《坐牢歌》,而是《外面的世界》。 他们的悲苦人生,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他们中有些人所犯的重罪在现在看来可能只是一个并不严重的错误,但注销户口政策切断了他们的退路,极端的劳改环境磨掉了他们的青春,而那些荒凉的劳改地点,最终成了很大一部分人永远的归宿。 现在走在青藏公路上,路边成片的沙棘和枸杞林,很少有人知道背后是这些人的青春和汗水。他们是严打的承受者,也是西部开发的参与者,他们的悲苦人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他们有罪, 更有血泪。 他们中的有些人, 在受到惩罚的同时, 也遭受了侮辱与伤害。 但时代的残酷性就是这样, 一粒灰尘落到你的肩头, 你的人生可能就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