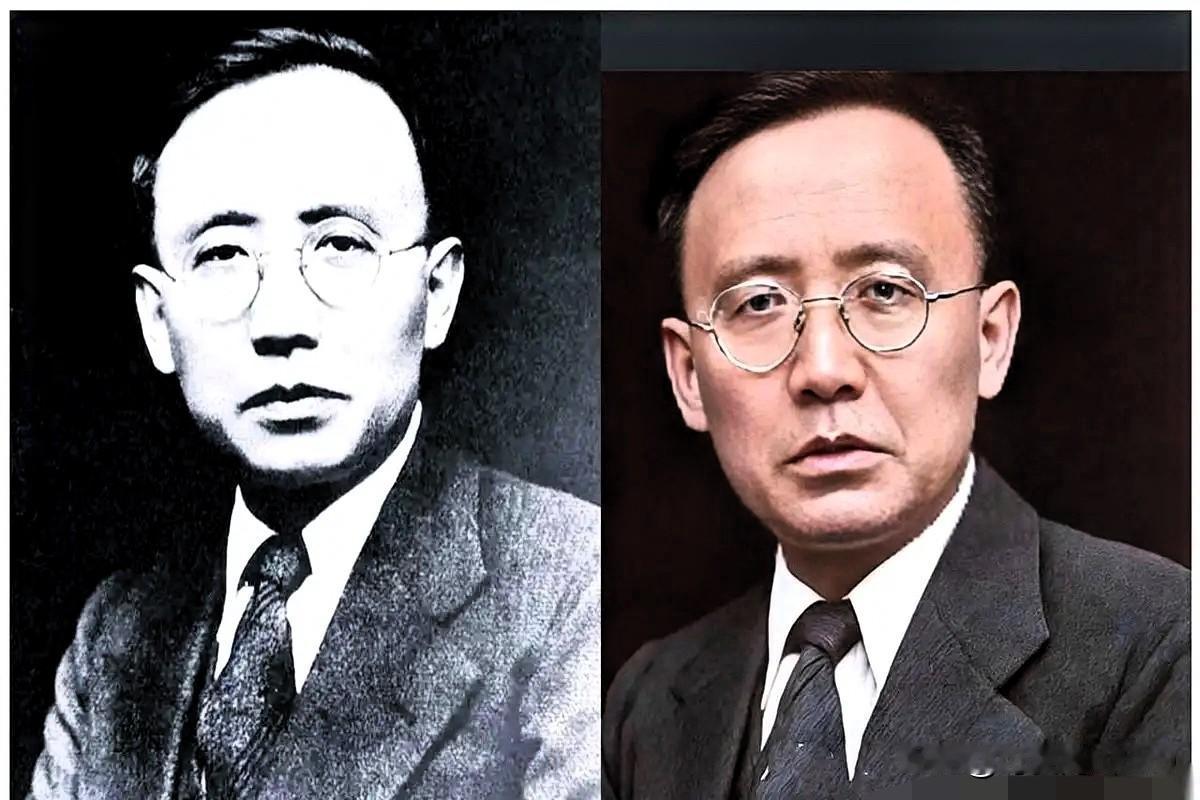1980年3月,邱岳峰吃了大量安眠药,被送往医院也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虽然他是著名的配音艺术家,但没有政府机构或单位(上译厂)出面的追悼会。 上海南昌路的小弄堂里,邱岳峰家的房门被急促地敲响。 邻居和同事撞开门时,他已经倒在沙发上,身边散落着安眠药瓶。 众人不敢耽搁,立刻将他抬上三轮车,往淮海医院赶。 医院的灯光亮了一夜,医生护士轮番施救,始终没能唤醒他。 3月30日晚上,医生走出抢救室,摇了摇头。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同事们都愣住了。 大家每天在录音棚里听他的声音,仿造《简·爱》里罗切斯特的深沉,《追捕》里唐塔的阴鸷,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邱岳峰的父亲曾是中国武官,母亲是白俄人士。 这样的家庭背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让他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没有经过复杂的流程,他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这个罪名像一道无形的枷锁,从此跟着他。 1966年之后的十年,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白天挑粪种地,晚上偷偷背台词。 有一次干校组织文艺演出,他忍不住上台朗诵,刚开口就被打断。 负责人指着他的鼻子,说历史反革命没资格登台。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上译厂不少同事都拿到了平反通知,恢复了名誉和待遇。 邱岳峰也递交了申请,厂里核查后说他的问题早已查清,没问题。 可他等了一年多,始终没拿到那份正式的平反文件。 他还是厂里的内控人员,出差要报备,参加重要活动要审批。 1950年他进入上译厂时,凭着过人的天赋,工资直接定到103元。 这个工资数额,二十多年里没涨过一分。 一家六口挤在17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四个孩子长大后,只能在阁楼上搭铺。 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就坐在小板凳上,借着台灯的光研究剧本。 遇到难把握的角色,他会反复听原版录音,逐字琢磨语气。 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特别赏识他,说他配的角色有灵魂。 1979年,上译厂译制《简·爱》,男主角罗切斯特的配音人选有争议。 有人觉得邱岳峰的声音太特别,不符合传统绅士形象。 陈叙一力排众议,坚持让他来配。 影片公映后,罗切斯特的声音传遍全国,电影院里场场爆满。 观众走出影院,都在讨论这个有磁性又有层次感的声音。 也就是这一年,厂里来了几位年轻女演员,其中一位经常向邱岳峰请教配音技巧。 两人在录音棚里讨论剧本,偶尔一起吃饭交流。 没过多久,厂里就传开了流言,说邱岳峰和这位女演员关系不正常。 流言越传越玄,最后传到了他妻子耳朵里。 妻子性格刚烈,当场和他大吵起来。 争吵中,妻子情绪激动,抬手打了他一巴掌。 这一巴掌,让原本就压抑的邱岳峰彻底垮了。 他没辩解,也没争执,默默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3月29日那天,他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叮嘱他们好好读书。 孩子们以为只是普通的叮嘱,没想到这是最后的告别。 他去世后,上译厂很快做出决定,不举办官方追悼会。 理由是他的死属于自杀,定性为背叛革命。 这个决定让同事们寒了心。 演员组的李梓站出来,说就算厂里不办,我们自己办。 韩非主动写了悼词,同事们凑钱买了花圈和黑纱。 追悼会定在龙华殡仪馆,消息悄悄传了出去。 那天早上,殡仪馆门口挤满了人,大多是素不相识的影迷。 有人拿着《简·爱》的电影海报,有人举着写有“罗切斯特永在”的牌子。 上译厂规定,只有部分同事能参加追悼会。 孙渝烽是邱岳峰的好友,两人约定退休后一起办个小书房,取名不易斋。 他赶到殡仪馆时,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想起每次配完音,邱岳峰都会把剧本整理好,在上面标注心得,然后送给年轻同事。 张涵予当年就是因为听了他配的《基督山伯爵》,才下定决心走上表演道路。 配音演员李杨也说,自己的配音技巧,大多是从邱岳峰的作品里学来的。 那些年,上译厂译制的《凡尔杜先生》《警察与小偷》等影片,邱岳峰都参与了配音。 他用声音塑造了几十个经典角色,每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可这些成就,没能让他摆脱历史的包袱。 他到死都没等到那份平反文件,没能拥有自己的小书房。 上译厂的同事们自发组织的追悼会,成了对他最好的致敬。 上千名影迷冒着寒风前来送行,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喜爱。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