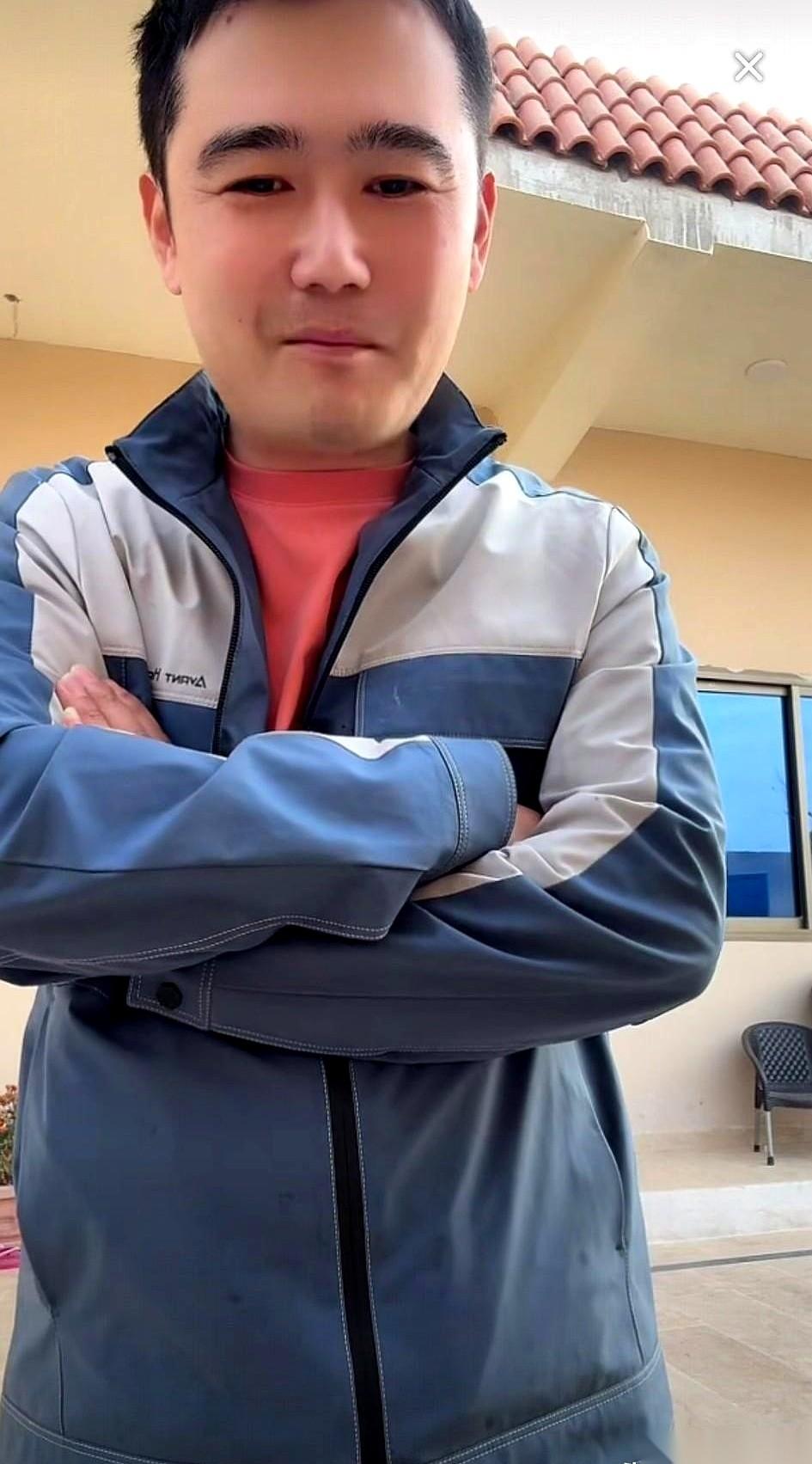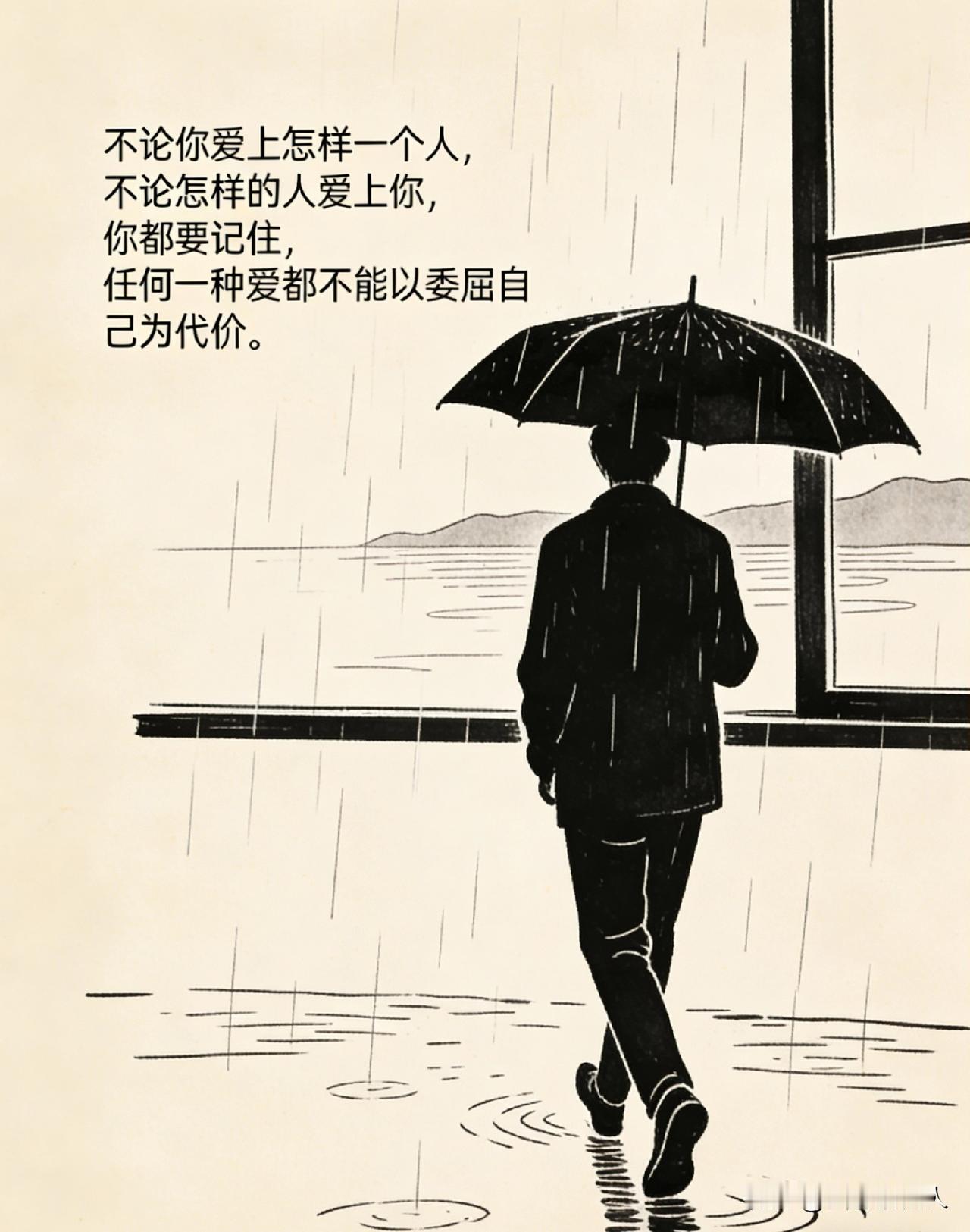他们把女人,钉在门板上。你没看错,就是用钉子,活生生的人,像一幅画那样,钉在自己家的门板上,事后,整个永昌县,成了一座“寡妇城”。 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的深秋,那年的永昌,地里的庄稼刚收了一半,就被过境的马家军盯上了。领头的军官叫马步青,手下的兵痞们扛着枪,挨家挨户踹门,抢粮食抢牲口,连百姓缝在棉衣里的铜板都要抠出来。 永昌县的男人性子烈,城西的铁匠们牵头,凑了几十把锄头和砍柴刀,趁着夜色摸进了马家军的临时营地,砍死了三个抢粮的哨兵。他们以为这能吓退豺狼,没想到,这是把整个县城的女人推进了地狱。 被钉在门板上的第一个女人,叫王桂英,是城西铁匠铺的老板娘。她男人就是带头反抗的铁匠,叫李铁锤。马家军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把李铁锤和其他参与反抗的十七个男人,全部吊在县城的戏台上,一刀一刀凌迟处死。 杀完男人还不算,他们把王桂英拖到自家的门板前,两个兵痞按住她的手脚,另一个举着拇指粗的铁钉,对着她的手腕狠狠砸下去。“钉!给我钉结实了!”军官的吼声震得人耳朵疼,铁钉穿透皮肉,钉进门板的那一刻,王桂英的惨叫撕破天幕,却没人敢上前一步。 围观的百姓被枪托逼着站在路边,老人的眼睛被血水刺得发红,小孩的嘴被母亲死死捂住,哭声闷在喉咙里,化成颤抖的呜咽。 王桂英不是唯一一个。那天,马家军把所有反抗者的妻子都拖到了自家门板上,手腕脚踝各钉一根铁钉,让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男人被虐杀,看着家里的粮食被装车拉走,看着牲口被活活打死在院子里。钉子没有钉在要害,就是为了让她们活着,活着感受疼,活着感受绝望。 有个刚嫁过来的新媳妇,才十六岁,叫春桃,她男人是个秀才,没参与反抗,只是站在路边骂了一句“畜生”,就被一刀劈成了两半。春桃被钉在门板上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她疼得浑身抽搐,手抠着门板上的木纹,抠出了血,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娃,我的娃”,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眼睛里的光一点点灭了。 兵痞们走了之后,县城里静得可怕。没死的女人被邻居们救下来,拔钉子的时候,没有麻药,只能咬着布巾硬扛,有的女人手腕的骨头被钉裂了,骨头被钉裂了,一辈子都抬不起胳膊。戏台子上的男人尸体挂了三天,乌鸦啄食着血肉,血腥味飘遍了整个县城。 没人敢埋,马家军留下话,谁敢埋,就把谁也钉在门板上。直到第七天,一场大雨把尸体冲得不成样子,才有人趁着夜色,把尸体拖到城外的乱葬岗,草草埋了。 从那天起,永昌县的男人几乎绝迹。剩下的女人,有的失去了丈夫,有的失去了父亲,有的失去了儿子。她们聚在一起,拆掉了被钉过的门板,烧了一锅热水,洗掉上面的血迹,却洗不掉渗进木纹里的冤屈。 曾经热闹的铁匠铺,再也听不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曾经书声琅琅的秀才家,再也没有翻过书页的声响。寡妇们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坐在煤油灯下,给孩子缝补衣裳,缝着缝着,眼泪就掉在针脚里。她们不敢提男人的名字,一提,心就像被钉子扎着疼。 有人说,马家军是因为打了败仗,拿百姓撒气。有人说,那些反抗的男人太傻,硬碰硬,害了自己也害了女人。可没人问问,那些男人为什么反抗。那年的永昌,地里的粮食本来就少,官府的赋税已经收走了大半,马家军再来抢,百姓们不反抗,就得饿死。 他们不是不怕死,他们是怕自己的女人孩子饿死。王桂英被救下来之后,再也没说过话,她守着铁匠铺的废墟,每天摸着被钉过的门板发呆,三年后,在一个大雪天,冻死在了门板旁边。 永昌县的寡妇们,硬是靠着一双手,把县城撑了起来。她们种庄稼,纺棉花,教孩子们认字,告诉他们,要记住那些被钉在门板上的日子,要记住那些为了活命反抗的男人。几十年后,有人在永昌县的老房子里,还能找到那些带着钉孔的门板,钉孔里的血渍,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像一道道刻在历史上的伤疤。 苦难从来不是用来被遗忘的,那些被钉在门板上的女人,那些被虐杀的男人,都是战乱年代里最渺小的尘埃,却用自己的命,诉说着百姓对生存的渴望。永昌县的“寡妇城”之名,不是耻辱,是见证,见证着底层百姓在绝境里的挣扎,见证着人性的恶,也见证着人性的韧。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