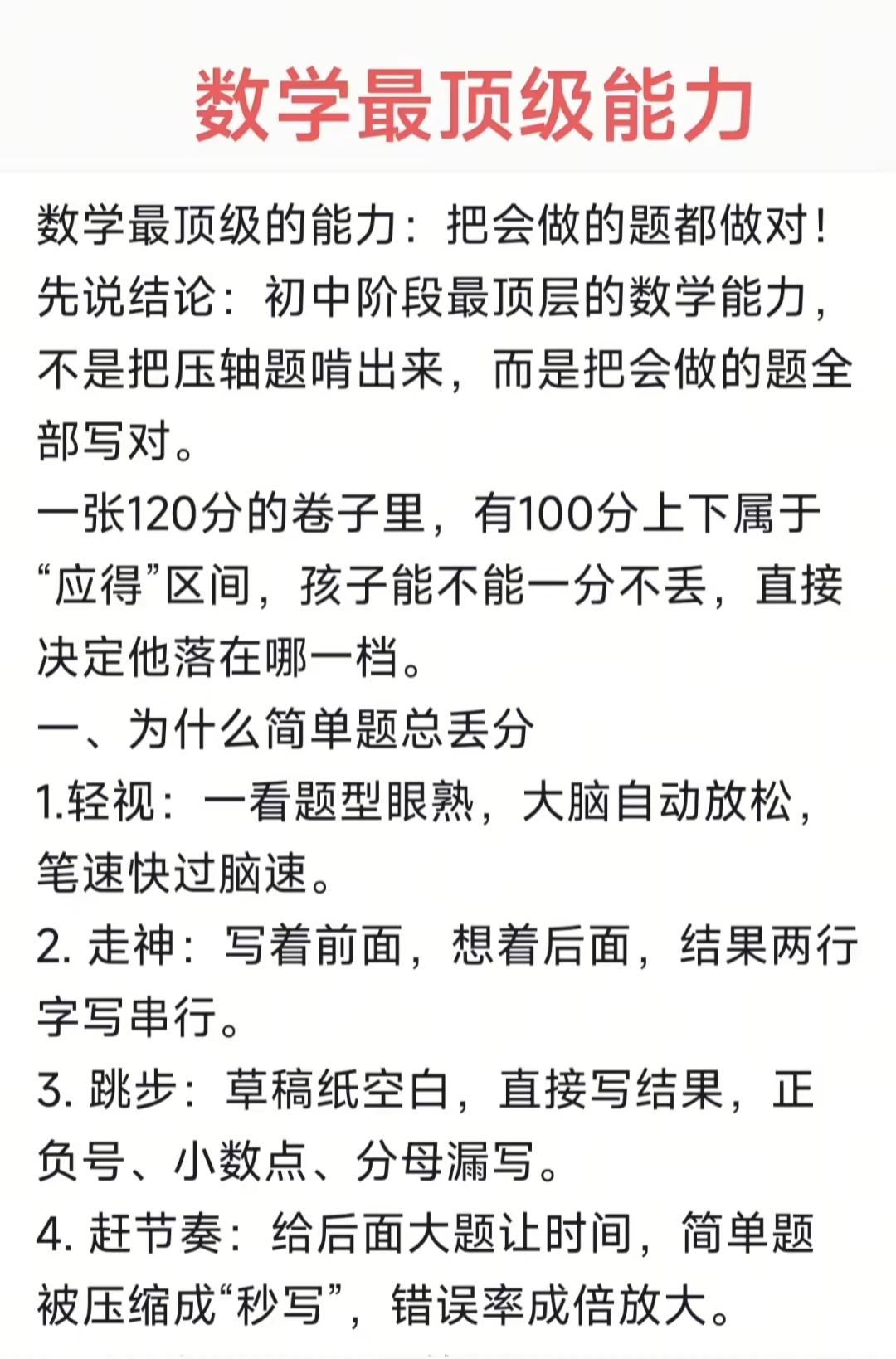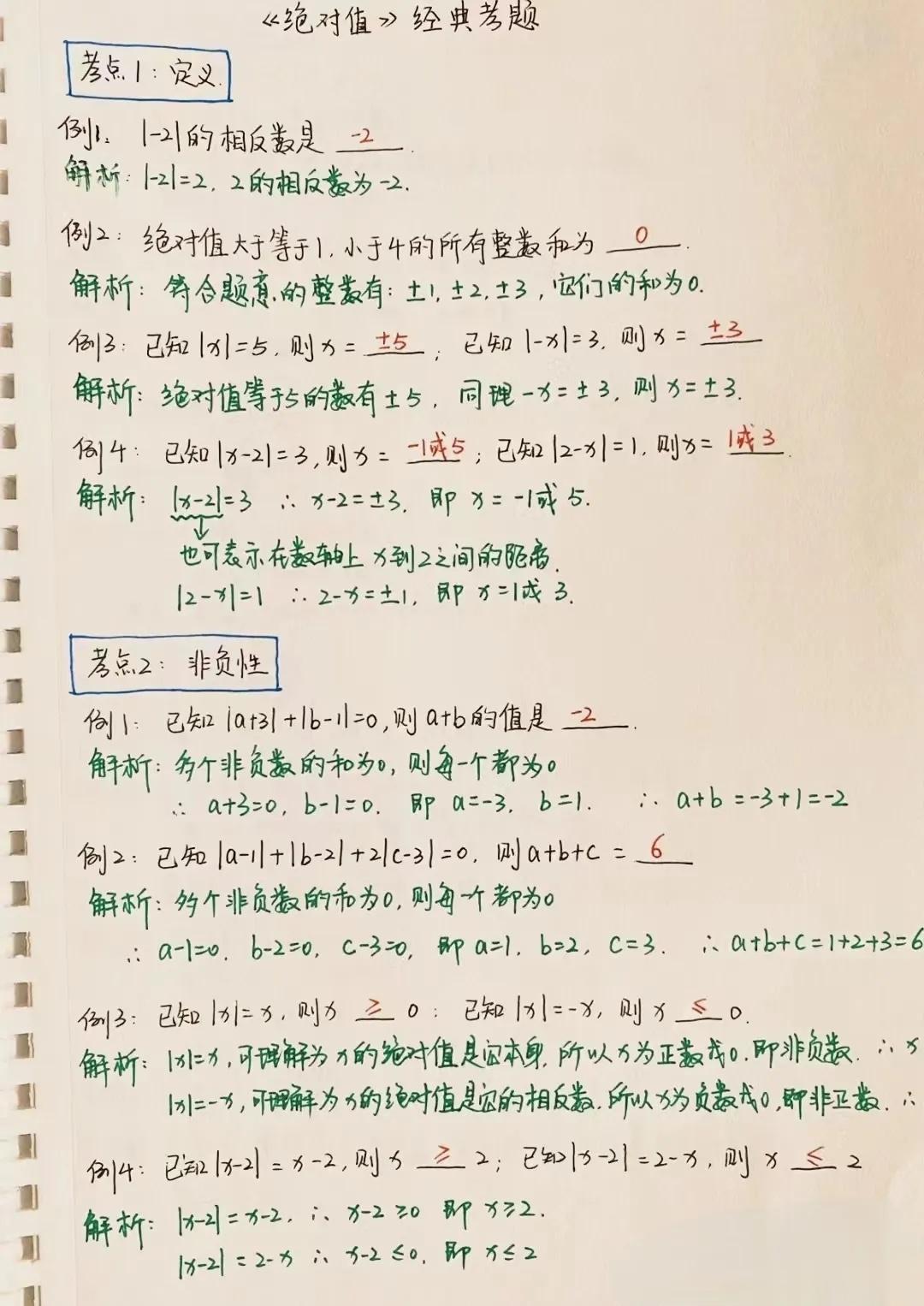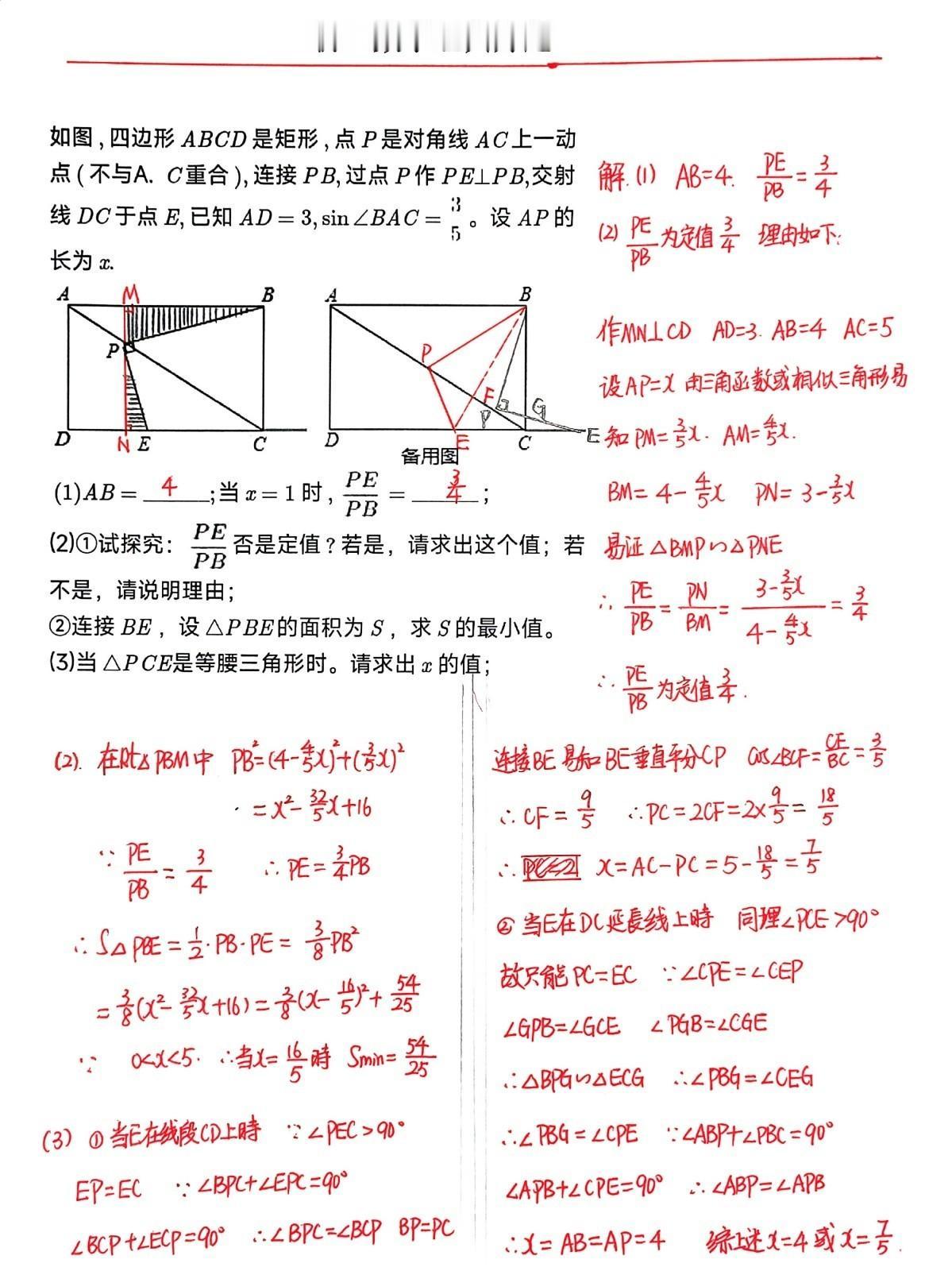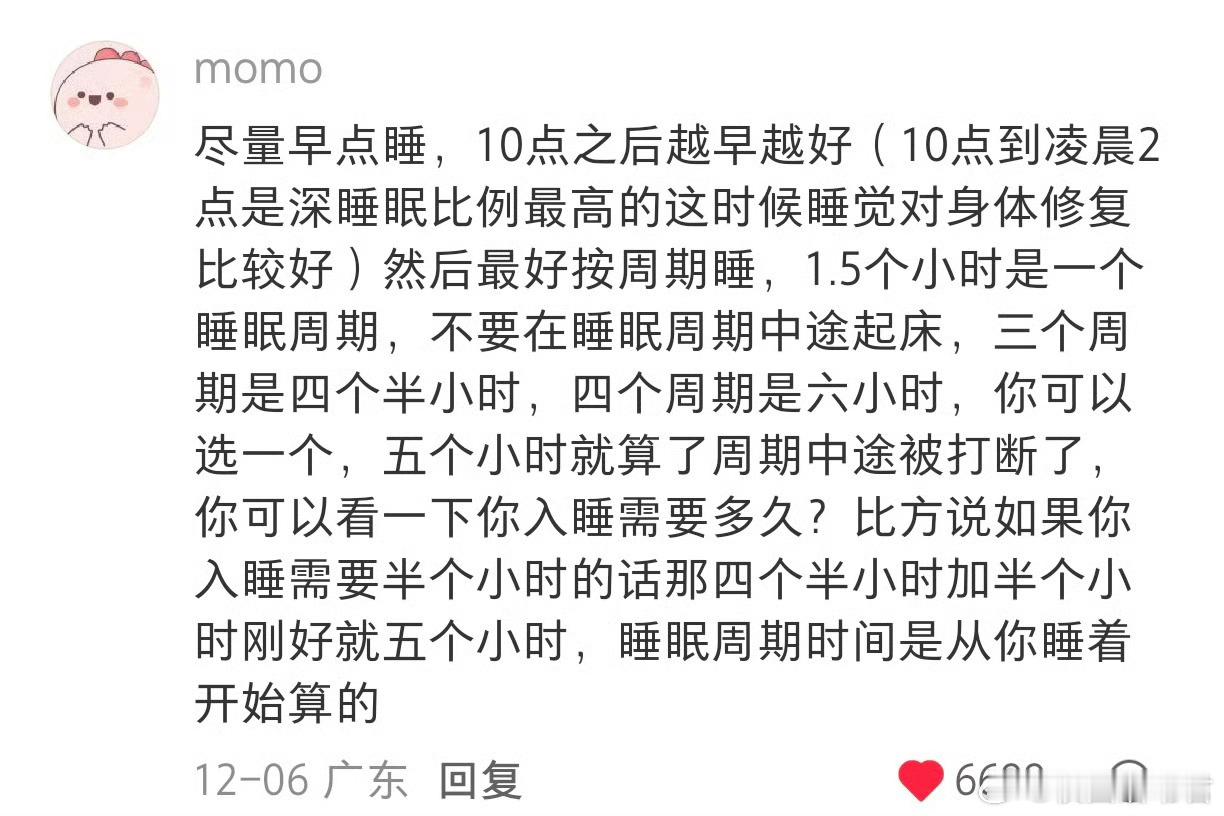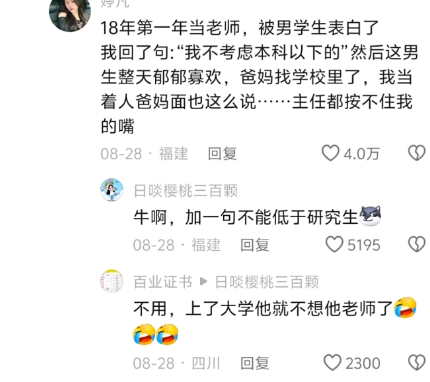1983年,有关部门邀请外国数学家门德尔逊来华讲学。不料他却大为吃惊,反问道:“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吗?为何请我来班门弄斧?”在场领导瞬间一脸懵逼,陆家羲?有这号人物吗? 这一问,让在场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因为即使搜肠刮肚,这群业内人士也没能在脑海里检索出“陆家羲”这个名字。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连夜核查,他们才终于在内蒙古的一所中学里,定位到了那个被称为“老师”,却早已震动西方学界的人物。 谁能想到,此时大洋彼岸推崇备至的“神人”,正蜗居在包头九中不足十平米的教工宿舍里,在这个没通暖气的小屋里对抗着全世界最复杂的组合数学难题。 陆家羲身上最扎眼的标签,不是数学家,而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民科”符号,他当过上海五金行的学徒,在这个讲究师承和出身的学术圈,他像个闯入者。 后来为了生存,他北上哈尔滨电机厂做技术员,哪怕在那个工友下班只顾着拼酒打牌的嘈杂环境里,他唯一的消遣也是啃那本借来的《数学方法趣引》。没有系统教育,他就靠翻烂字典硬生生自学完高中课程,哪怕最后考入师范院校物理系,也没能改变他作为“物理老师”的职业轨迹。 但在无数个深夜,他是另一个世界的王。 包头的冬夜能把墨水冻住,陆家羲的手上缠着布条,防止冻裂的指关节握不住笔。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一切天文数字般的推导全靠人力,他在废旧报表和廉价纸张的背面构建他的数学帝国,可这座“帝国”第一次崩塌,是因为一次迟到十年的信息差。 早在1961年,他就彻底攻克了悬置百年的“寇克曼女生问题”。那个在方格纸上被一遍遍验算的答案,被他视若珍宝地寄往北京的学术期刊,等待他的没有掌声,只有轻描淡写的“不宜发表”四个字——这几乎宣判了一个无名小卒在学术界的死刑。 他没有放弃,把那些甚至没被认真审阅的手稿锁进抽屉,像个西西弗斯一样继续推石上山,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更残忍的玩笑。 1979年,在一场大雪中,陆家羲偶然翻到一本从国外引进的期刊,上面的内容让他如遭雷击:早在1971年,就有两名外国学者宣布攻克了“寇克曼问题”。 那是他十几年前就锁进抽屉的答案。 只因为籍籍无名,只因为信息闭塞,属于他的“世界首创”变成了废纸,那天他站在图书馆里,甚至听得到雪落下的声音,那是十年心血化为乌有的声音。 这个打击换作常人足以致命,但陆家羲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既然已经晚了,那就去挑战那个连西方人也不敢轻易触碰的更高级——“斯坦纳三元系大集”。 这一次,他不再盲目投给不识货的所谓“权威”,而是将那几篇耗尽心血的论文,直接寄给了美国《组合论杂志》。 1981年,大洋彼岸的回信让这间寒冷的宿舍第一次有了温度:这一成果被认定为该领域的重大突破。整整六篇论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分期连载,西方数学界惊呼,在远东的某个角落,居然藏着一位能解开死结的大师。 这就是门德尔逊发出那句质问的背景。那个在国内无人知晓的“隐形人”,其实早已在国际坐标系中标注了属于中国的高度。 也是直到这一年,国内学术圈才真正看见了他。1983年10月,陆家羲终于不再是那间陋室里的孤独演算者,他接到了武汉学术会议的邀请函。为了凑足路费,他卖掉了家里那辆赖以为生的旧自行车,穿着那是无论如何也体面不起来的旧衣裳,第一次站在了同行的聚光灯下。 当他在讲台上展示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推导过程时,台下的掌声一度震得玻璃发颤。那是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喝彩,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高光时刻。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虚弱。长期超负荷的脑力劳动和营养不良,早在他身体里埋下了炸弹。会议结束后,他坐着硬座火车回到包头,甚至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为了完善后续的研究计划再次伏案。 10月30日的深夜,由于长期劳累诱发心脏病,他趴在自己那张并不宽敞的书桌上,永远停止了思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陪伴他的依然是那些堆得像山一样的草稿纸。 哪怕是他在身后的整理遗物环节,展现出的画面也足以让闻者落泪。妻子在他常穿的那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口袋里,摸出了半个还没吃完的干硬馒头,以及那封早已泛黄、甚至被揉皱过的退稿信。信纸的背面,是他后来工工整整写下的一句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在他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象征着中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证书寄到了学校。红色的封皮在阳光下有些刺眼,可惜那个为此燃尽生命的人,再也无法亲手拆开它。 陆家羲这三个字,后来被印在了教科书里,成为一段励志的传奇。但人们或许更应该记住门德尔逊当年的那个错愕眼神——它在不停地追问我们,还有多少惊世骇俗的天才,因为没有光鲜的头衔和学历,正无声地湮没在尘埃与偏见里。 真正的热爱往往是沉默且残酷的,它不需要外界的理解,却能在最贫瘠的土壤里,开出最锋利的花。 信源:人民日报——拼搏 20 多年,耗尽毕生心血,中学教师陆家羲攻克世界难题斯坦纳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