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年,东汉百官跪在路边迎接董卓入京,在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中,董卓一眼就看到了老朋友皇甫嵩,赶紧下车拉起他的手,笑着问道:“义真,你怕了没?”皇甫嵩盯着他,回道:“你若辅政为民,有何可怕;若用武镇国,谁不害怕?”董卓面色僵硬,讪讪而过。 中平元年的深秋,皇甫嵩站在晋县的土坡上,身后是十万黄巾军降卒的尸骸堆成的“京观”。他刚写完请朝廷免税赈灾的奏折,指尖还沾着墨渍,就听见驿站快马带来的消息:有人弹劾他“滥杀降卒,骄纵跋扈”。三个月后,他解甲归田,看着曾经挂着左车骑将军印绶的梁柱,第一次明白——战功,从来不是朝堂信任的通行证。 陈仓之战的分歧,比晋县的秋风更刺骨。董卓拍着营门的立柱吼“当速攻”,他却指着远处敌军阵中摇晃的饿殍旗帜:“再等十日,粮尽自溃。”最终敌军果然因缺粮溃散,可董卓摔门而去时,甲胄碰撞的脆响,像一根针,扎进了两人关系的缝隙里。后来他主动交还兵权,董卓却在同一年被削职为并州牧,信使送来董卓“此恨绵绵”的私信时,他正对着铜镜摘下最后一片护心甲。 “将军手握天下兵权,若趁此时自立,可安汉室!”阎忠的声音撞在帐壁上,震得油灯摇晃。皇甫嵩翻过案上的《孙子兵法》,遮住那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淡淡道:“我若称王,与董卓何异?”侄子皇甫郦带着亲兵在帐外跪了三天三夜,求他讨伐董卓,他只是让亲兵送去一件棉袍——他不愿用一场内战,换一个沾满鲜血的王位。 董卓入京那天,皇甫嵩站在百官队列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腰间空荡荡的绶带。曾经挂着印绶的地方,如今只剩一道浅褐色的勒痕。他知道董卓不会忘陈仓的旧怨,更不会忘他手中曾有的兵权,可他没想到,这位新权臣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任命他为“挂名中郎将”,连议政的偏殿都不让他进。 乱世之中,坚守真的比权位更值得吗?有人说他愚忠,说他若当年听阎忠之言,或许能挽救汉室。但他比谁都清楚,中平元年被罢官时,朝堂早已是一盘散沙;陈仓之战后,军心已在“京观”的阴影下摇摇欲坠——他所谓的“威望”,不过是世人对“忠臣”的最后一点幻想。 直到吕布的画戟刺穿董卓咽喉的消息传来,皇甫嵩正在宫中整理先帝遗诏。王允举着诏书闯进来,声音发颤:“郿坞尚有董卓残部三万,非将军不能平!”他接过诏书时,指尖第一次有了久违的力量。领兵出征那天,他没穿铠甲,只束了一条素色腰带,就像当年征讨黄巾时一样。 火光烧了整整一夜,郿坞的琉璃瓦在烈焰中噼啪作响,映得他鬓角的白发像落了一层霜。士兵们从废墟里翻出董卓囤积的粮食,足够洛阳百姓吃三年;而不远处,就是他当年请朝廷免税赈灾却被驳回的灾区旧址。 他站在瓦砾堆上,想起董卓入京时那句问话:“义真,你怕了没?” 此刻,他终于可以回答:我怕过——怕负了十万黄巾降卒的性命,怕负了先帝托孤的眼神,怕负了这乱世里仅存的一点人心。 只是,怕,不等于退。 他最终没能扶起倾颓的汉室,就像他当年没能保住那十万黄巾降卒的性命。但当他在郿坞废墟上下令“释放所有董卓家眷,只诛首恶”时,至少守住了自己对“忠”的定义——不是对某个王朝,而是对自己心中那杆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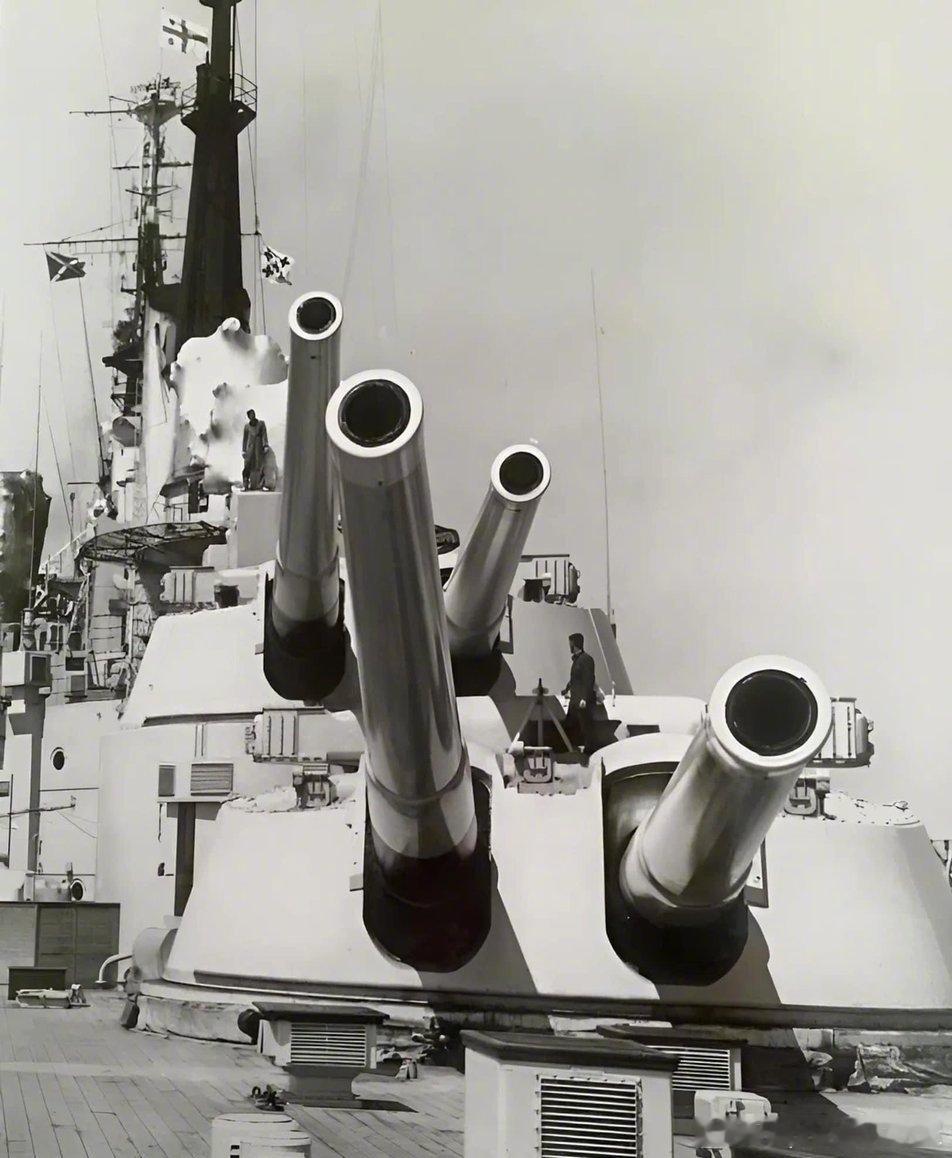







用户13xxx27
忠于封建王朝,就必然要杀死这些无路可走逼反的十万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