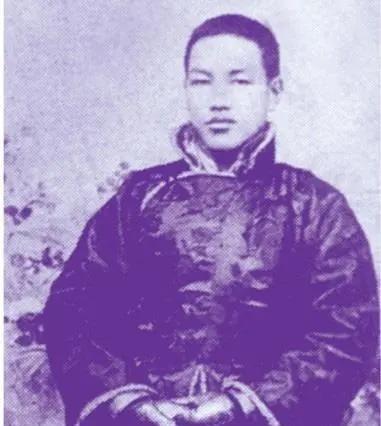1901年冬,19岁的毛福梅和14岁的蒋介石拜堂成亲,主婚人刚喊完“送入洞房”,没想到蒋介石就跑去和小伙伴捡爆竹了。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当场脸色大变,气得直跺脚。 奉化溪口的青石板路上,毛福梅缠足的小脚挪得慢,手里攥着绣了一半的荷包——那是她嫁过来前,在南货店柜台后偷偷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像她对未来的猜想。蒋家与毛家是世交,蒋家欠着毛家三千银元的旧账,王采玉觉得“亲上加亲”能了这笔债,更能给顽劣的儿子拴个“贤内助”,便托了媒人。 毛福梅没见过蒋介石,只听过他是“私塾里爱逃学的瑞元少爷”。她裹脚时疼得咬着帕子哭,娘说“女人家脚小才稳当”;蒋介石读四书五经时偷撕书页叠纸鸢,王采玉拿戒尺打手心,骂“没个正形”。两个被长辈捏合的人,新婚夜一个和衣睡在床上,一个靠在妆奁边坐到天明,红烛燃尽时,蜡油滴在毛福梅的绣鞋上,凝成小块的黄。 1903年春天,蒋介石突然要带毛福梅去宁波。他说“你也该识几个字”,把她送进女校,还请了梳头婆子。毛福梅在课堂上用炭笔描“蒋”字,笔画总写不直;蒋介石站在窗外看,有同学问“那是你家先生?”她红着脸点头,心里像揣了团暖烘烘的棉絮。 可这团暖意很快被海风打散。1905年蒋介石去日本,走前塞给毛福梅一包银元,没说归期。她回溪口陪王采玉念佛,木鱼声敲得比心跳匀。偶尔收到信,字里行间是“东京见闻”“革命理想”,提她的只有“母亲安好?”四个字。1910年蒋经国出生那天,她疼得抓坏了床单,蒋介石在上海,回来后抱了抱孩子,说“眉眼像我”,转身就去了堂屋和朋友谈事。 姚冶诚是1911年进的蒋家。蒋介石说“她懂我”,毛福梅没闹,还帮着收拾房间。两人一起去集市买布,姚冶诚挑艳色的,她选青蓝的,摊主笑着说“蒋家太太们倒和睦”。可夜里听见蒋介石骂姚冶诚“赌钱输光体面”,她缩在被子里想:他骂她时,会不会更难听?果然,后来为蒋经国读书的事,蒋介石推了她一把,她撞在门框上,额角青了一块,没敢让王采玉看见。 1921年王采玉病重,拉着毛福梅的手说“福梅啊,忍忍就过去了”。蒋介石跪在床边发誓“必善待发妻”,转头就在佛堂念休书。亲戚们劝“一日夫妻百日恩”,他把休书拍在香案上,香灰撒了半张纸。毛福梅哭着回娘家,娘叹“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又走回蒋家,脚底板磨出了血泡。 1927年的协议签得快。“解除名分,仍居丰镐房,蒋经国归你养”,蒋介石的笔在纸上划过,像当年捡爆竹时划开的口子。宋美龄来溪口那天,毛福梅搬去萧王庙,带走的只有那只绣歪了的荷包。她照样给蒋介石做鸡汁芋艿,让厨子送去老宅,自己坐在门槛上剥毛豆,看日头从东墙移到西墙。 1939年12月12日,日军飞机的轰鸣声炸碎了溪口的宁静。毛福梅跑出丰镐房,又想起忘带蒋经国儿时穿的虎头鞋——那是她熬了三夜绣的,鞋头绣着“长命百岁”。她折回去,刚摸到鞋盒,炸弹就在院外炸开,瓦砾堆里,那只青蓝布的荷包和虎头鞋缠在了一起。 蒋经国从苏联回来奔丧,抱着母亲的灵柩哭到吐血。蒋介石在重庆听副官报信,愣了半晌,让侍卫去请和尚念经,自己坐在窗边,手里转着串佛珠,那串珠子还是王采玉当年给他的。1947年立碑时,蒋经国坚持刻“显妣毛太君之墓”,有人说“该写‘蒋母’”,他红着眼吼“她是我娘”。 有人说蒋介石对毛福梅并非全无旧情——1903年在宁波女校外,他其实站了整节课;可也有人说,那不过是少年人一时的新鲜感。 旧式婚姻像把钝剪刀,裁着女人的一辈子。毛福梅守着蒋家,从缠足少女到白发老妪,没骂过一句,没怨过一声,最后连墓碑上都没刻“蒋”姓。 只是不知道,1947年蒋经国重立“以血洗血”石碑时,有没有想起1901年冬天,那个捡爆竹的少年和挪着小脚的新娘——他们的路,从一开始就被那串散落的竹蒂头,铺得歪歪扭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