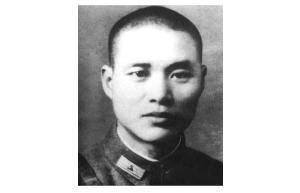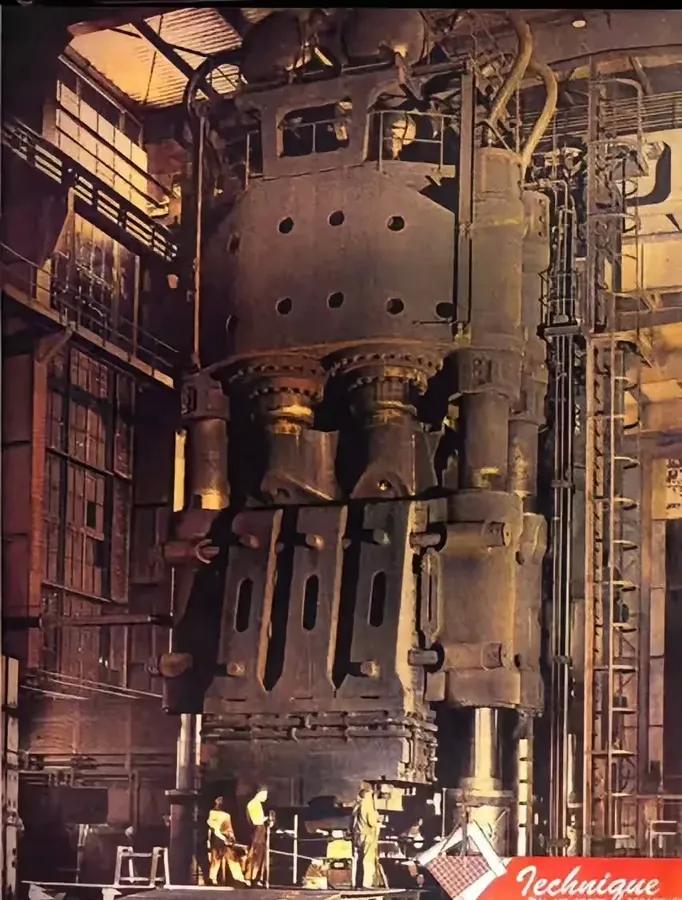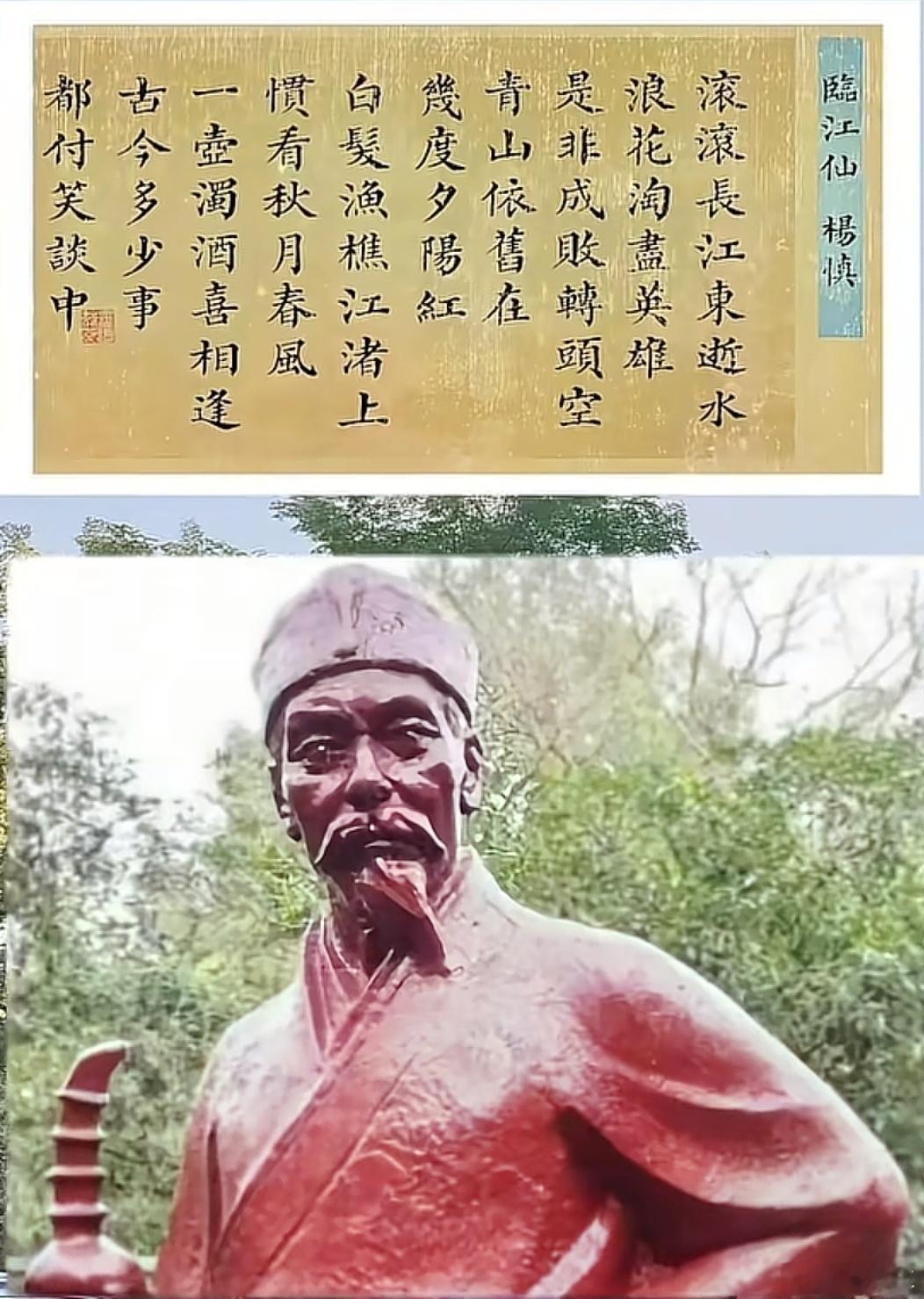1980年,沈醉到香港,准备与第二任妻子栗燕萍见面,但栗燕萍已经改嫁了,她就嘱咐现任丈夫:“他若要打我,你别拦着!” 1949年,那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沈醉此时面临着人生最大的抉择。他把栗燕萍和几个孩子送上了去香港的船,手里攥着五张船票的钱,那是他给家人最后的保命符。他答应妻子,处理完手头的事就去香港汇合,然后一起去台湾。 卢汉云南起义,沈醉被扣押,随后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消息传到香港,变了味。国民党为了宣传需要,对外宣称沈醉已经“杀身成仁”,壮烈殉国了。身在香港贫民窟的栗燕萍,听到这个消息时,天都塌了。 这时候,唐如山出现了。他是沈醉的老部下,也是流落香港的“天涯沦落人”。他看着老长官的遗孀孩子快饿死了,心一横,站出来搭把手。一来二去,为了生存,为了给孩子上户口读书,两人搭伙过起了日子。 而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的沈醉,对此一无所知。他在狱中积极改造,心里唯一的念想就是老婆孩子。直到有一天,新来的狱友无意中透露了栗燕萍改嫁的消息。 那一刻,沈醉崩溃了。据当时狱友回忆,沈醉把自己关在角落里,把牙刷柄磨尖了想自杀,如果不是被人及时发现,这世上早就没了沈醉这个人。他想不通,自己还没死,老婆怎么就成了别人的? 那种被世界抛弃的绝望,比坐牢更诛心。 但沈醉毕竟是沈醉。经过三十年的改造,经过新社会的洗礼,他的心境早就变了。1980年,当他终于拿到去香港探亲的通行证时,他心里装的不再是恨,而是深深的愧疚。 回到开头那一幕。 门开了。沈醉站在门口,两鬓斑白,腰杆却依然笔直。栗燕萍低着头,浑身发抖,等待着预想中的耳光或者痛骂。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沈醉看着眼前这个苍老的女人,看着那个局促不安的老部下,眼眶瞬间红了。他快步走上前,没有举起拳头,而是紧紧握住了唐如山的手,声音颤抖却坚定地说:“老唐,谢谢你!谢谢你替我照顾了她们母子三十年!要是没有你,她们可能早就不在了。” 这一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开了三十年的坚冰。栗燕萍猛地抬头,泪水决堤而出,所有的委屈、愧疚、恐惧,在这一刻化作嚎啕大哭。 沈醉转过头,看着前妻,轻轻说了一句:“这些年,苦了你了。” 这一幕,在场的沈醉女儿沈美娟后来回忆说,那是她这辈子见过最震撼的场景。父亲没有用“原谅”这个词,因为他知道,在生存面前,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谈原谅。他把所有的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是他没能履行诺言,是他让妻儿流离失所。 接下来的日子,沈醉展现出了极高的情商和胸怀。他提议,从今往后,他和栗燕萍以兄妹相称,和唐如山做回兄弟。 他在香港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还有更惊险的博弈。 当时的台湾当局得知沈醉到了香港,那是急得跳脚又满怀期待。要知道,沈醉如果能从香港去台湾,那可是绝佳的“反共宣传”素材。国民党特务带着重金和美女,甚至许诺高官厚禄,轮番来游说沈醉:“去台湾吧,那是你的老家,你的退休金我们都给你补齐。” 甚至连美国方面也伸出了橄榄枝,暗示他可以去美国养老。 面对这些诱惑,沈醉只做了一件事。 他在离开香港前,在一本留言簿上,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他对那些来当说客的旧相识说:“我沈醉这半辈子,前半生那是真的‘醉’了,做了不少对不起人民的事;后半生在共产党这里,我才真正‘醒’了。我的家在北京,我的根在大陆,谁也别想把我拉走。” 既断了台湾的念想,又表明了自己的气节。他用行动告诉世人,那个曾经的军统特务死了,活着的是新中国的爱国人士沈醉。 临别时,栗燕萍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报纸。那是1959年沈醉第一批被特赦时的《人民日报》,还有后来关于沈醉的所有新闻剪报。 栗燕萍指着报纸上沈醉的照片,每一张的脸部都被红笔画了个圈。她哭着说:“我怕时间太久,我老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你的样子,所以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遍。” 沈醉看着那些泛黄的报纸,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哭得像个孩子。他把这个铁盒子视若珍宝地带回了北京,直到去世,这个盒子都一直放在他的床头。 后来,沈醉在北京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那个装满剪报的铁盒子,被垫在了他的骨灰盒下面。 而在香港的栗燕萍,得知沈醉去世的消息后,做了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她托人买来五张去往大陆的空白船票——那是当年沈醉欠她的——在维多利亚港的码头边,一张张烧给了沈醉。 烟灰随着海风飘散,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未完的承诺。 沈醉的晚年,一直致力于两岸统一的工作,写回忆录,揭露军统黑幕,呼吁台湾故旧回归。他常说:“我们这代人的悲剧,不能再在下一代身上重演了。” 1980年的那次重逢,它不仅仅是两个老人的叙旧,更是一个民族伤痕愈合的缩影。它告诉我们,仇恨可以被时间冲淡,但爱和理解,能穿越时间,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