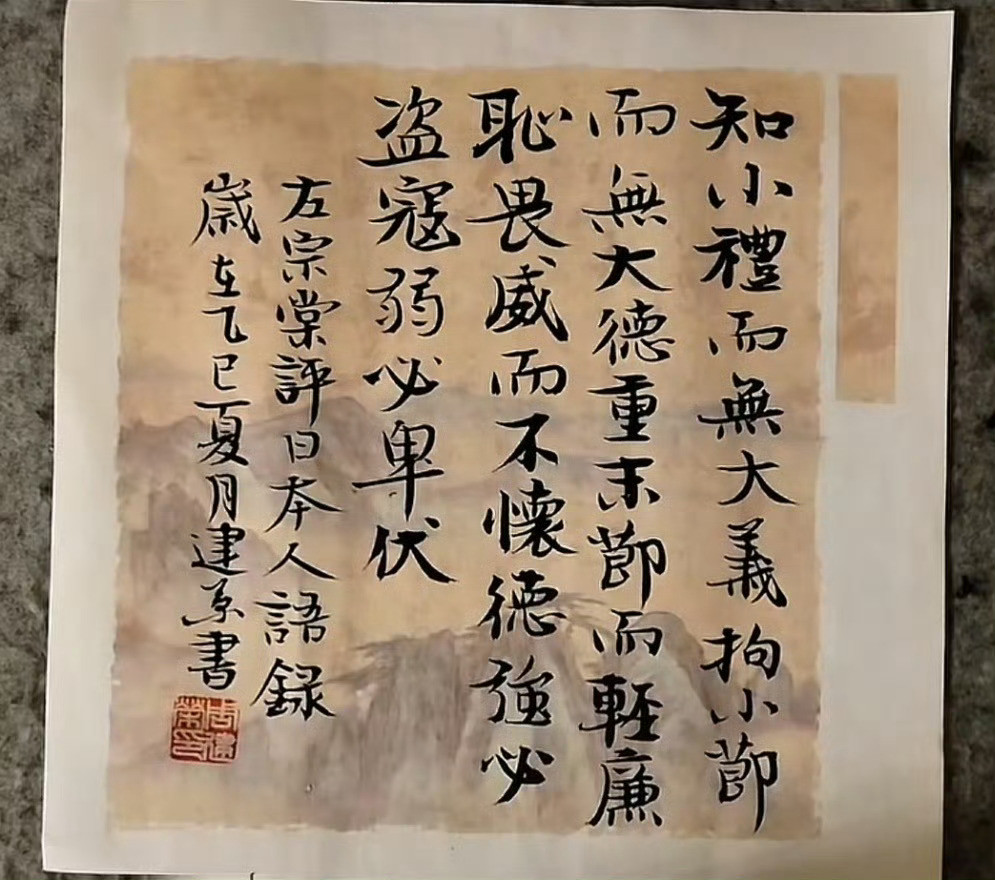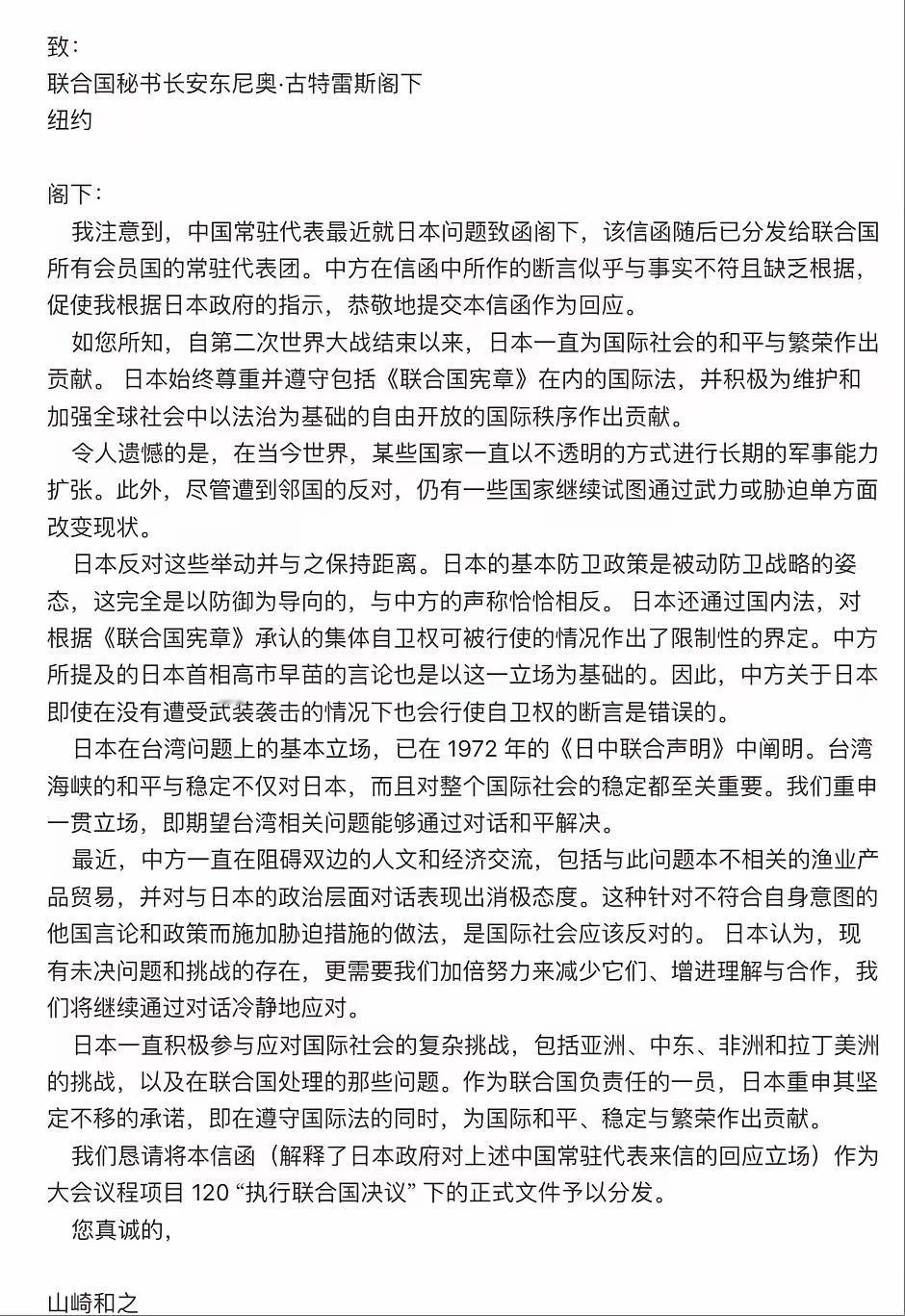果不其然。 越南媒体突然报道了:受中日关系紧张等因素影响,在日本的越南务工群体因为中国游客减少,正在经历解雇和减薪潮。 当中国游客因中日关系紧张按下赴日暂停键,首当其冲的不是日本本土从业者,而是早已被绑定在低端服务业的越南劳工。这不是偶然的蝴蝶效应,而是日本长达十几年“用人策略”埋下的定时炸弹。 日本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依赖已到病态程度: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游客贡献了日本旅游消费的四分之一,人均消费超24万日元,支撑着东京银座的奢侈品店、北海道的滑雪场、大阪的药妆店。这些场所的后厨、保洁、导游岗位,70%以上由越南“特定技能劳工”填充。 他们持有的签证被严格限制在特定行业,一旦旅游业遇冷,雇主无需支付遣散费即可解约,这在日本《劳动基准法》里有个灰色条款:“因业务调整导致的解雇,外劳无权主张同等补偿”。 这种系统性歧视早有伏笔。日本政府为解决少子化危机,表面推出“特定技能”制度,实则延续2012年的“研修生陷阱”。越南劳工赴日前需向中介支付平均68万日元的费用,相当于他们在越南两年的收入。 抵达日本后,时薪被压至日本法定最低标准的80%,住宿扣款、工具费、甚至“日语培训费”层层盘剥,许多人月薪到手不足10万日元。 更致命的是,他们的签证与雇主绑定,一旦被解雇就面临非法滞留风险,2024年越南籍“失踪研修生”占总数56%,大多因欠薪逃亡。 中国游客减少引发的退订潮,让这种脆弱性彻底暴露。札幌某酒店60%的订单来自中国旅行社,11月单月取消28个旅行团,直接裁掉12名越南保洁工。 东京某居酒屋老板坦言:“解雇越南员工比协商日本兼职容易,他们不敢投诉,怕影响签证。” 这种隐性默契在日本服务业蔓延:京都的温泉旅馆、奈良的纪念品店,优先裁减的永远是不会说日语的东南亚面孔——即便他们已在日本工作三年,即便他们的时薪只有正式员工的一半。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日本社会的“工具人”思维。越南劳工被包装成“技能实习生”,实则从事日本年轻人不愿做的3K工作。当经济景气时,他们是“支撑日本GDP的贡献者”;当危机来临,立刻沦为“可以牺牲的成本”。 2024年越南劳工占日本外劳总数30%,却在旅游相关行业占比高达58%,这种产业布局本身就是定时炸弹。 加上日元贬值让越南劳工的汇款缩水30%,国内中介吹嘘的“月存15万日元”神话破灭,导致新赴日人数下降三成——但存量劳工仍被锁死在随时被抛弃的岗位上。 最讽刺的是,日本政府一边高呼“改革外劳制度”,一边放任雇主转嫁危机。2025年7月通过的《育成就劳法》号称允许劳工换岗,却设置了“同行业、同地域”的严苛限制,对旅游业从业者毫无意义。 当越南驻日使馆试图介入劳资纠纷时,往往收到“经营困难”的标准化答复。就像爱知县某技术公司拖欠200名越南高技能劳工4800万日元工资时,当地劳动局仅以“协商解决”结案。 这场危机的本质,是日本用“临时工思维”构建的产业链,在遭遇外部冲击时的必然溃败。 中国游客减少是导火索,真正暴露的是日本对廉价外劳的依赖症:既想享受人口红利,又不愿承担社会保障;既需要东南亚劳工填补服务业缺口,又拒绝给予平等权益。 当越南务工者在东京街头排队领取救济面包时,日本内阁正在讨论“如何吸引印度游客替代中国市场”——他们始终没明白,被牺牲的不仅是越南劳工的生计,更是日本经济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