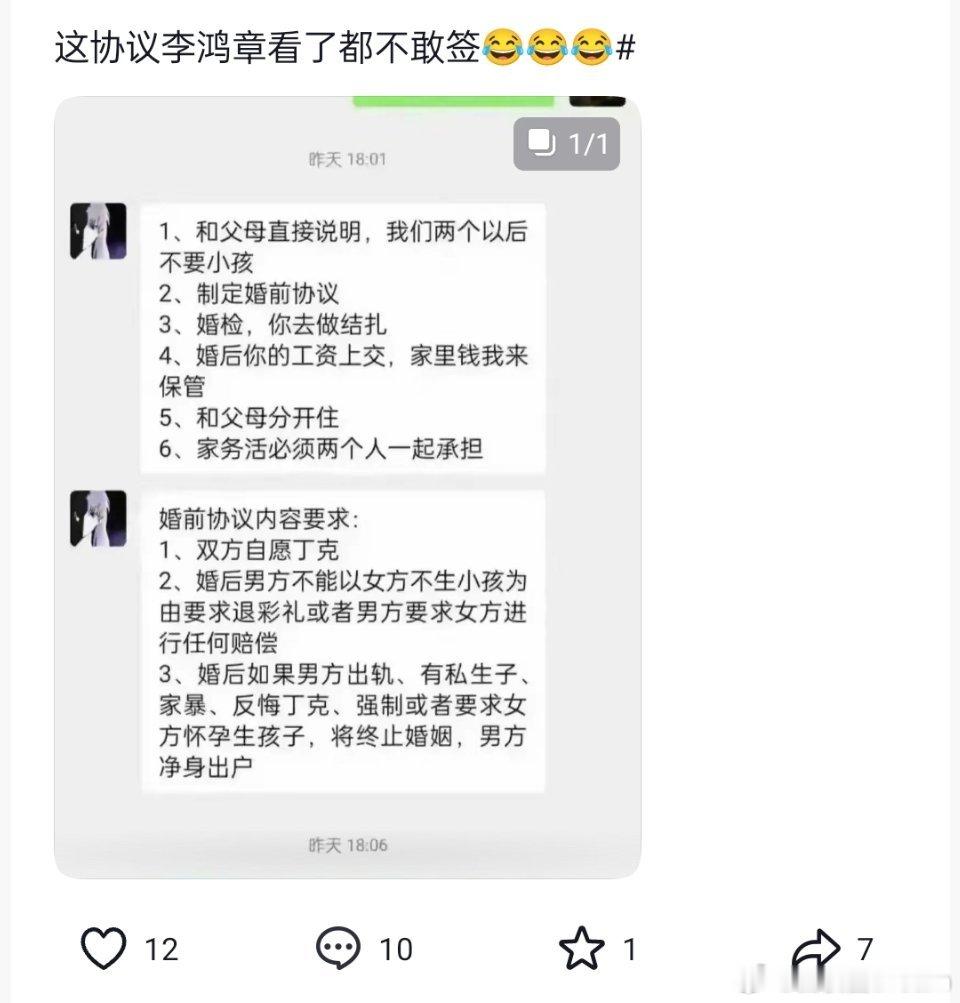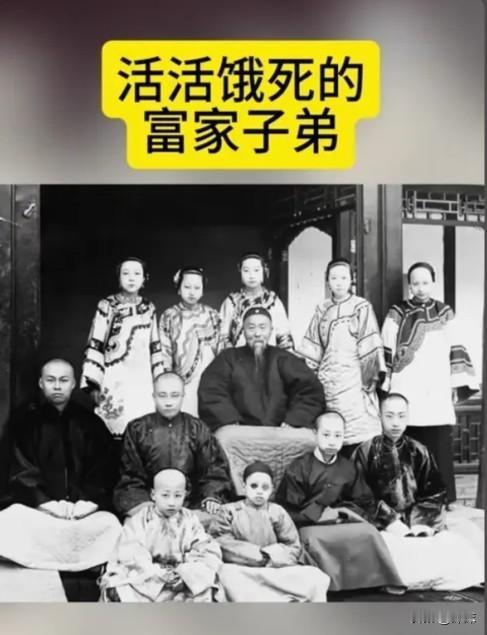1901年,李鸿章去世,他给子孙留下4000多万两白银和无数家产,可没想到,52年后,他的孙子,43岁的李子嘉,竟因为穷得买不起食物,活活饿死了,死后,他的身上只裹了一张破草席,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草草埋葬了事。 李鸿章这辈子攒下的家底真不算少,4000多万两白银只是明面上的数,算上安徽、江苏的万亩良田,上海、南京的几十处商号当铺,还有各地的宅院地产,折算成当时的银元得有十亿出头,比晚清一年的国库收入还多出两成。 1910年李子嘉在上海法租界出生时,家里光伺候他的佣人就有二十多个,奶妈得是身家清白的农家妇女,还得懂几句洋文,婴儿床是从巴黎运来的雕花铁床,连擦嘴的手帕都绣着金线,那排场真是把“富贵”俩字刻在了日子里。 他爹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虽说也算见过世面,可对儿子的管教全凭“给钱”。1922年李经方病逝,12岁的李子嘉直接继承了1.3万亩良田的地契,上海外滩两栋洋楼,还有芜湖半条街的商铺。 那时候他每月零花钱就有500银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可没人教他怎么管账,更没人说过“坐吃山空”这回事。管家每次递上账本,他扫两眼就签字,连田租收了多少都懒得问,反倒觉得花钱慢了丢面子。 十四五岁起,李子嘉就成了上海滩风月场的常客。长三堂子的姑娘们见了他都主动迎上来,他随手打赏就是一块银元,够寻常人家吃半个月。后来有人怂恿他吸鸦片,说这是“上流人的消遣”,他二话不说就在家里设了烟馆,天天招呼狐朋狗友吞云吐雾。 李经方生前留下的老管家劝过几次,说鸦片是败家根苗,他直接把人辞退,换了个会陪他抽烟的佣人。1928年的时候,他为了给一个叫翠玉的戏子买定制行头,一口气卖了苏州的十亩良田,那片地每年能收上千斤稻谷,他却眼皮都没眨一下。 李经方其实早看出儿子挥霍无度,生前特意断过他半年财路,想逼着他戒鸦片。可李子嘉有的是办法,偷偷把母亲留下的英国珠宝拿去当铺抵押,换了钱继续抽大烟、逛赌场。赌场老板见他出手阔绰,特意给他开了VIP包间,骰子一掷就是几百银元的输赢。 1935年他在赌场输了8000银元,转头就把芜湖的三家绸缎庄抵押了出去,那可是李鸿章当年亲手创办的商号,传了三代的家业就这么成了赌桌上的筹码。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李子嘉的日子更荒唐了。日本浪人盯上了他的家产,哄着他把南京西路的商铺抵押给自己,说是“代为保管”,实则转眼就改成了日本洋行。他非但没察觉,还拿着抵押来的钱天天和日本人喝酒,以为能靠着这层关系保住富贵。等到抗战胜利,他想去要回商铺,才发现地契早就被换成了废纸,连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 1945年之后,李子嘉的家底基本空了。良田卖光了,商铺没了,洋楼也抵给了银行,只剩下一套破旧的宅院。可他还是改不了挥霍的毛病,偶尔借到点钱,先去买鸦片,再去小酒馆喝酒,根本不管下一顿在哪。 1948年冬天,他冻得实在受不了,想去投靠堂兄李厚甫,结果刚走到门口就被拦了下来,堂兄隔着门骂他“败家子”,连面都没见。 1949年之后,李子嘉搬到了芜湖城隍庙的破庙里,和左宗棠的孙子左巨生成了邻居。俩曾经的富家子弟,如今只能靠捡破烂、讨饭过活。左巨生还好,偶尔能帮人写写字换口饭,李子嘉除了花钱啥也不会,只能眼巴巴等着好心人施舍。1953年开春,江南下了场冷雨,庙里又潮又冷,李子嘉连着几天没讨到东西,蜷缩在稻草堆里没了气息。 左巨生找到李子嘉的族人报信,没人愿意来管。最后还是城隍庙的和尚找了张破草席,裹着他的尸体抬到乱葬岗,挖了个浅坑埋了。谁能想到,当年踩着金银出生的贵公子,到头来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李鸿章当年费尽心机攒下的家业,没熬过三代就败得干干净净,不是钱不够多,是这钱没养出懂得珍惜的人,反倒养出了只会挥霍的性子。这富贵来得太容易,散得也就格外快,李子嘉的结局,说到底还是自己折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