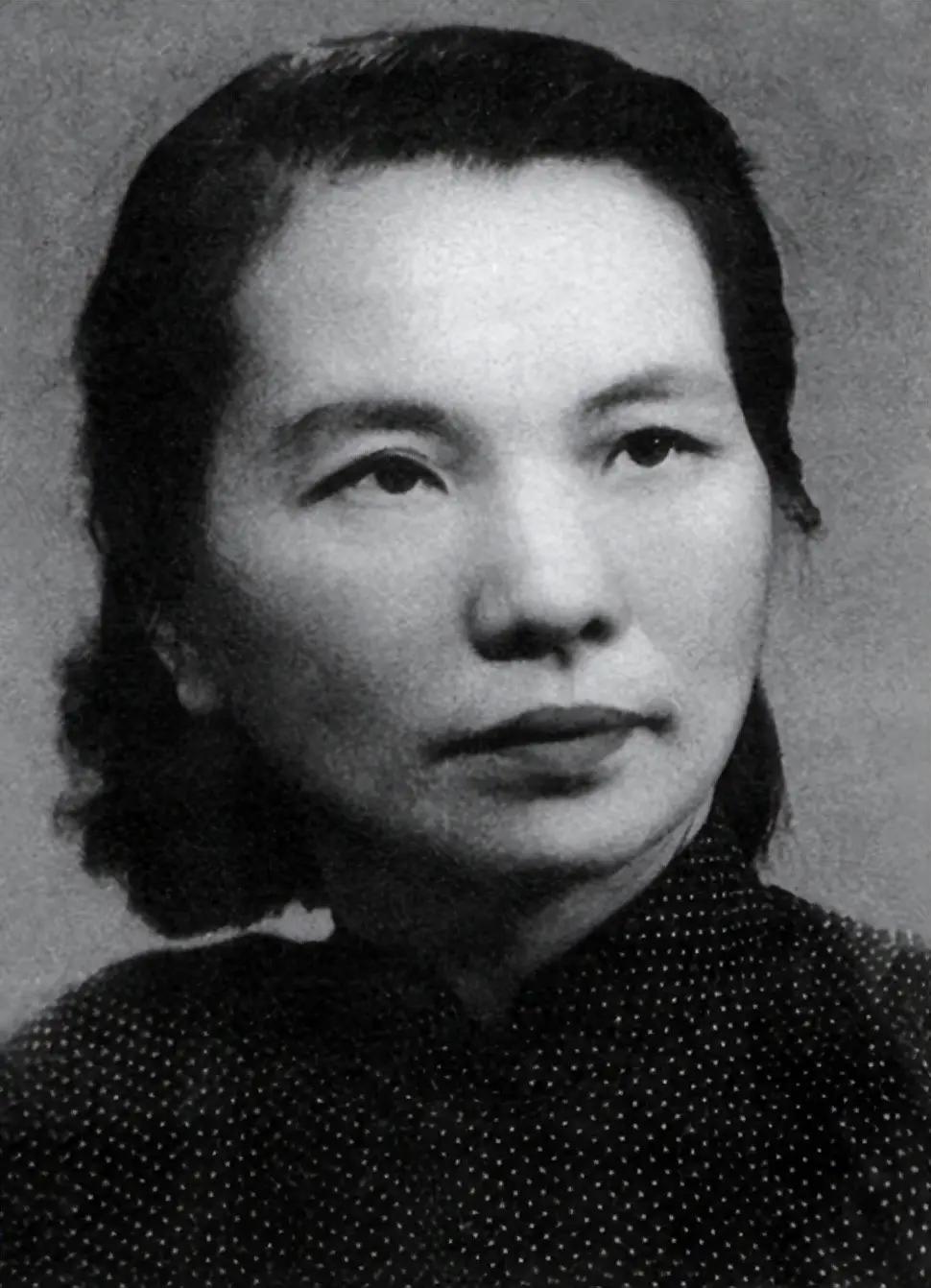1969年,21岁的女知青廖晓东,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光棍。新婚夜,廖晓东一脸娇羞,谁料,老光棍一脸不耐烦。然而,正当廖晓东一脸懵时,老光棍竟然给了她一巴掌! 1973年深秋,山洼村的煤油灯在夜色里亮了半宿。 廖晓东坐在土坯搭的讲台上,忍着腹痛给乡亲们批改作业。 10岁的小石头趴在桌边,看着她蜡黄的脸小声问:“廖老师,你是不是疼呀?” 她摸了摸孩子的头,把暖水袋往肚子上贴了贴:“没事,改完这些就休息。” 这个从青岛来的女知青,曾是家里的娇娇女。 1968年秋天,21岁的她刚到山洼村,踩着泥泞的土路走进村头土房,窗纸破了洞,冷风直往屋里灌。 父亲是青岛某中学的语文教师,出发前反复叮嘱她“知识能照亮人心”,这话被她写在了笔记本扉页。 第二天她就跟着社员下地,没干过农活的手很快磨出泡,村妇张婶把自己的粗布手套让给她,她在本子上画了只手套,旁边写着“张婶的善意”。 让她决心办学的,是收工时看到的一幕。 几个孩子在田埂上用树枝写字,歪歪扭扭的符号根本不成章法,一问才知村里从没出过识字的人。 10月25日的日记里,她写着“土房当教室,煤油灯当电灯,明天开课”。 第一个报名的是三十多岁的卢兆东,这个光棍汉蹲在门口搓着手,说想认几个字写信给远方的亲戚。 廖晓东发现他学得最认真,每天最早到教室擦黑板,还会把自家种的红薯悄悄放在她门口。 1969年冬天,卢兆东在扫雪时救了掉进冰窟的孩子,廖晓东在日记里画了颗红心,标注“心眼不坏”。 1970年社员大会上,村支书提起卢兆东因家贫娶不上亲的难处,他红着眼眶说“不怪别人,只怪自己没本事”。 廖晓东站起来的瞬间,会场鸦雀无声,她清晰地说“我愿意嫁给他”。 同来的女知青私下劝她“三思”,她翻开笔记本,指着那颗红心说“他值得”。 婚礼没有仪式,她抱着那捆笔记本搬进卢家茅草屋,当晚就和丈夫一起补屋顶。 婚后的生活有甜蜜也有苦涩,卢兆东性子急,甚至新婚夜就红过脸。那晚两人补完屋顶,廖晓东拿出笔记本规划识字班扩招的事,卢兆东闷声说“女人家好好过日子就行,教那么多字没用”,她反驳“识字能让孩子们有出路”,争执间卢兆东急了眼,挥手推了她一把,她踉跄着撞到桌角。 可没过半分钟,他就慌了神,蹲在地上给她揉腿,哽咽着说“我没读过书,怕你嫌我笨,更怕留不住你”。后来有次她教夜校晚归,他因担心发火摔了碗,事后蹲在地上捡碎片,说“我怕你出事”。 她没生气,反而把父亲的钢笔送给丈夫,说“以后想我的时候,就写写字”。 识字班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十几个孩子发展到三十多个老老少少,她用知青补贴买了纸笔,把学生按年龄分成高低班,笔记本上记满了每个孩子的学习进度。 仅一年时间,村里就有二十多个成年人能写家书、认工分票,孩子们更是能熟练背诵百家姓、读写常用字,她的扫盲成果被公社作为典型宣传。 10岁的小石头父母双亡,她常留孩子吃饭,不仅教他读书写字,还教他算数记账,后来小 石头凭借在识字班打下的基础,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公社中学的孩子。 她在日记里称他“最懂事的学生”,也把他当作自己教育成果的缩影。 1972年春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依然每天站在讲台上讲课,直到临产前还在批改作业。 儿子出生后,她把队里分的细粮都留给孩子和丈夫,自己啃窝窝头。张婶送来的鸡蛋,她也攒着给营养不良的学生补身体。 即便坐月子,她也没停过教学,让丈夫把学生的作业抱回家批改,还编写了适合乡村的简易识字课本,把农具名称、农作物名称都编进课文里,方便村民理解记忆。 1973年夏收后,她开始频繁腹痛,脸色蜡黄,却总说“忙完秋收再去看”。 直到一次讲课中途晕倒,被村民抬到卫生所,县里来的医生检查后,让村支书赶紧安排转院。 她攥着医生的手说“别浪费钱,我还有很多字没教完”,回到家就躺在病床上写识字卡片。 她编写的简易课本,后来被周边三个村子的扫盲班沿用了五年。 1974年2月12日,廖晓东在丈夫怀里闭上眼睛,最后一句话是“把笔记本给孩子们当课本”。 出殡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学生们捧着用彩纸做的花,跟在棺木后慢慢上山。 如今山洼村早已通了柏油路,当年的土房变成了三层教学楼。 她当年提出的“因地制宜编教材、分层教学促吸收”的扫盲方法,至今仍是当地乡村教育的参考案例。 当年的小石头退休前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他培养的学生里,有三人回到村里当老师。 卢小军作为廖晓东的孙子,如今接过了教学的接力棒,每次开学第一课,都会讲奶奶和那捆笔记本的故事。 每年清明,全校师生都会去廖晓东的墓前献花,孩子们会齐声朗读她当年编写的识字课本,声音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主要信源:(民国网——青春悲歌:一个过分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