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物理大师存在的意义,一句话给国家省了200亿美元。 在欧洲日内瓦的地下隧道里,大型强子对撞机已经运转了十余年。 它曾因发现希格斯玻色子名震世界,但随着时间推移,设备老化、科研突破放缓,这座耗费百亿欧元的“科学巨兽”逐渐显露疲态。 此时,国际高能物理学界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他们看到了继续推进对撞机研究的可能。 一个大胆的提议随之浮出水面:在中国建造一座周长超100公里、能量是欧洲对撞机7倍的超级对撞机,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装置。 但这个看似风光的科学计划,却在一位老人的反对声中按下了暂停键。 2012年,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让高能物理领域沸腾,也让中国科学家看到了追赶国际前沿的机会。 中科院高能所牵头提出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方案,计划分两步走:先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再升级为质子对撞机,整个项目预算高达1400亿人民币,折算下来接近200亿美元。 这个消息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多次表达合作意愿,不少国外科学家都期待能参与到这个“未来项目”中。 在支持者看来,这是中国跻身世界高能物理研究中心的绝佳机遇,建成后不仅能探索暗物质、反物质等前沿谜题,还能带动超导、微波、探测器等一系列高端技术的国产化。 就在项目推进的关键阶段,杨振宁的反对声音打破了一边倒的支持氛围。 2016年,94岁的他在公开平台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杨振宁特意提到了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的教训,这个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项目,预算从3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80亿美元,最终因资金失控被国会叫停,白白浪费了30亿美元的投入。 杨振宁担心,中国的超级对撞机也可能沦为“无底洞”,后续的维护、升级费用可能远远超出最初预算。 更让他忧心的是科研资源的分配问题。 当时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仅为5%,远低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 200亿美元的投入,相当于每年要从科研总预算中划出数十亿元,这必然会挤占生命科学、量子计算、芯片研发等更贴近国家需求的领域经费。 他在后续的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高能物理的“盛宴”早已过去,希格斯粒子发现后,大型对撞机的科研产出越来越有限,很多所谓的新发现都只是理论猜想,用巨额资金去验证猜想并不划算。 97岁高龄时,杨振宁仍在国科大的演讲中坚持自己的立场。 他清晰地指出,超级对撞机建成后,由于国内相关人才储备不足,大概率会由外国科学家主导核心研究,中国投入巨资却可能为他人做嫁衣。 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国际大型科研项目的主导权往往与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直接挂钩,而当时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顶尖人才数量确实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项目。 这场争议最终影响了项目的走向。 在“十三五”期间的发改委项目评审中,CEPC项目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200亿美元的投入计划就此搁置。 支持者并未完全放弃,后续仍在推进技术设计和预研工作,2025年还发布了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但项目的大规模建设始终没有启动。 200亿美元如果投入到民生改善、基础学科建设和“卡脖子”技术攻关中,能产生更直接、更广泛的效益。 科学探索需要热情,但更需要理性,尤其是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钱花在刀刃上才是对科学、对人民最负责任的选择。 杨振宁用自己的声望和学识,为国家避免了一场可能的资源浪费,这正是大师存在的真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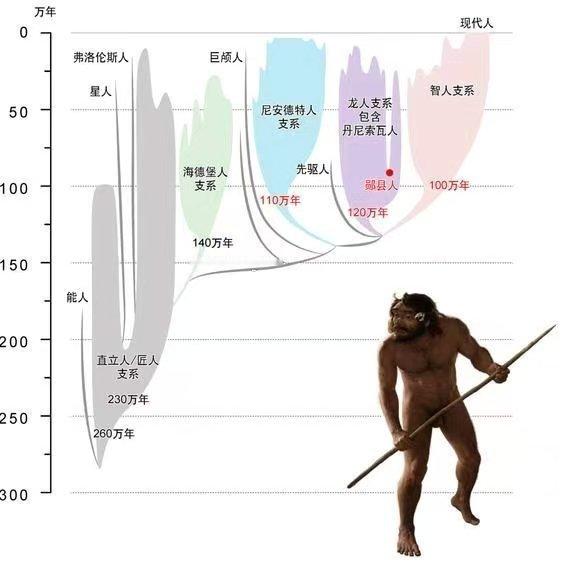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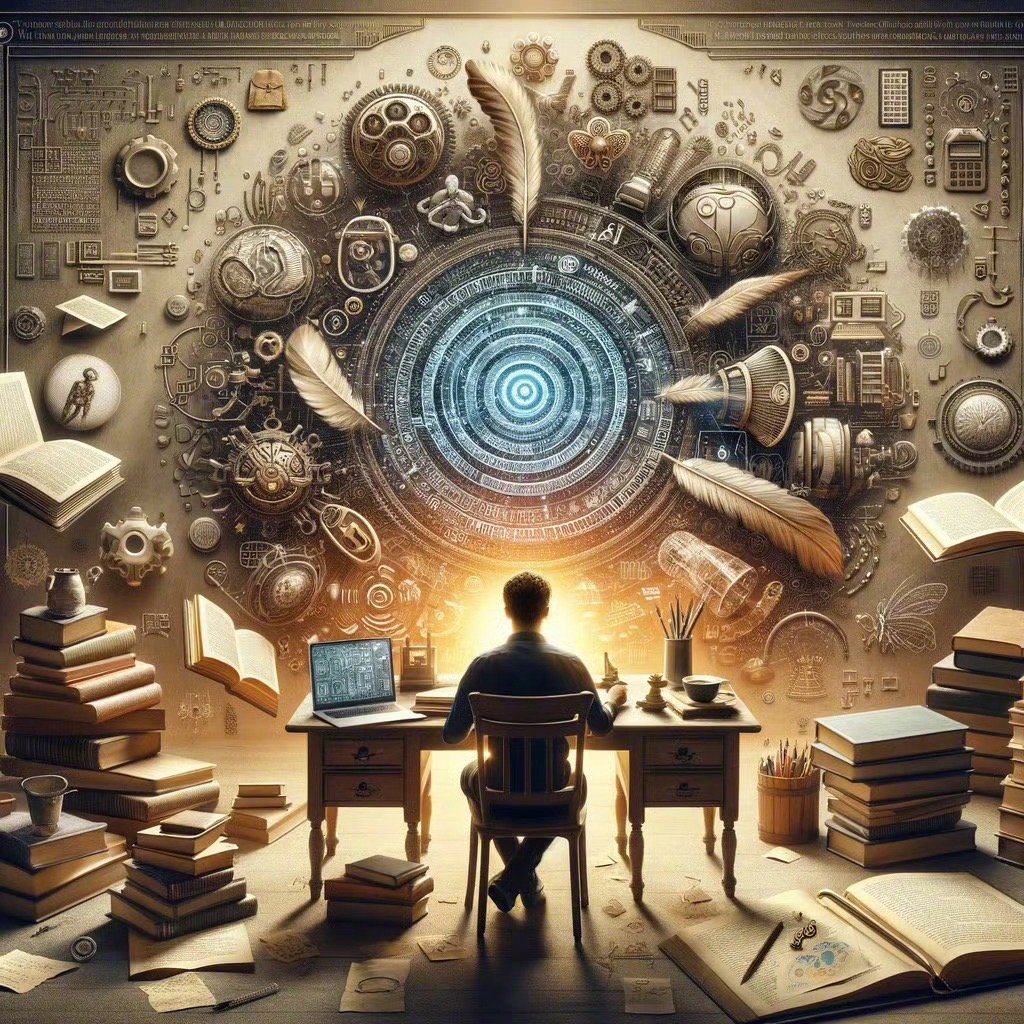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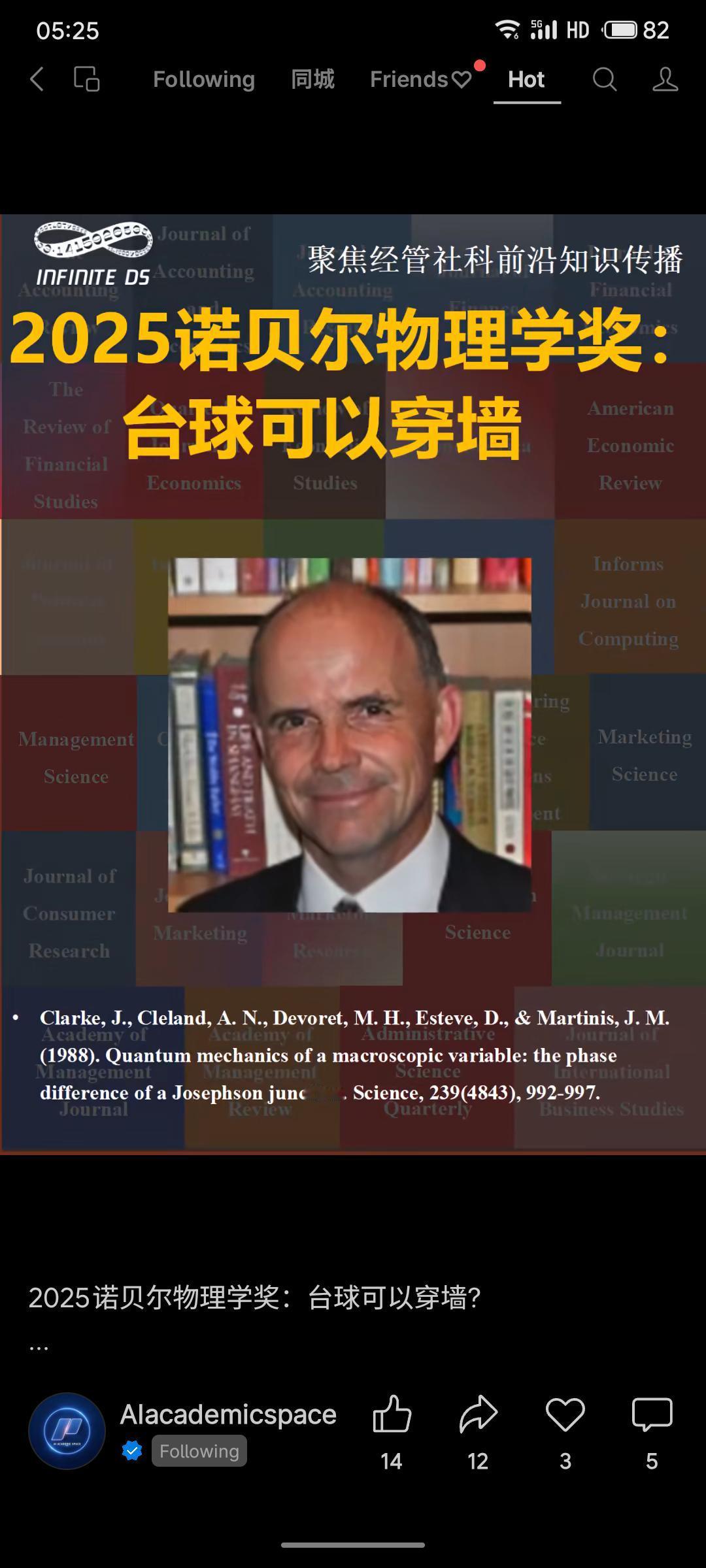

儒商
杨也说过等理论有突破(最好是由中国国内科学家提出),不要靠蛮力,各方面条件更成熟时再建更有利。
替天行道
粒子物理和现实世界是脱钩的。就像人工智能。网络的权重并不存在于单个粒子里。多有多的规律。宇宙射线能量比人工加速器能量高万亿倍,都没有新发现。这个时候建加速器就是赌博
丫丫
这个老人从他带领大一的新生中看到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根基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