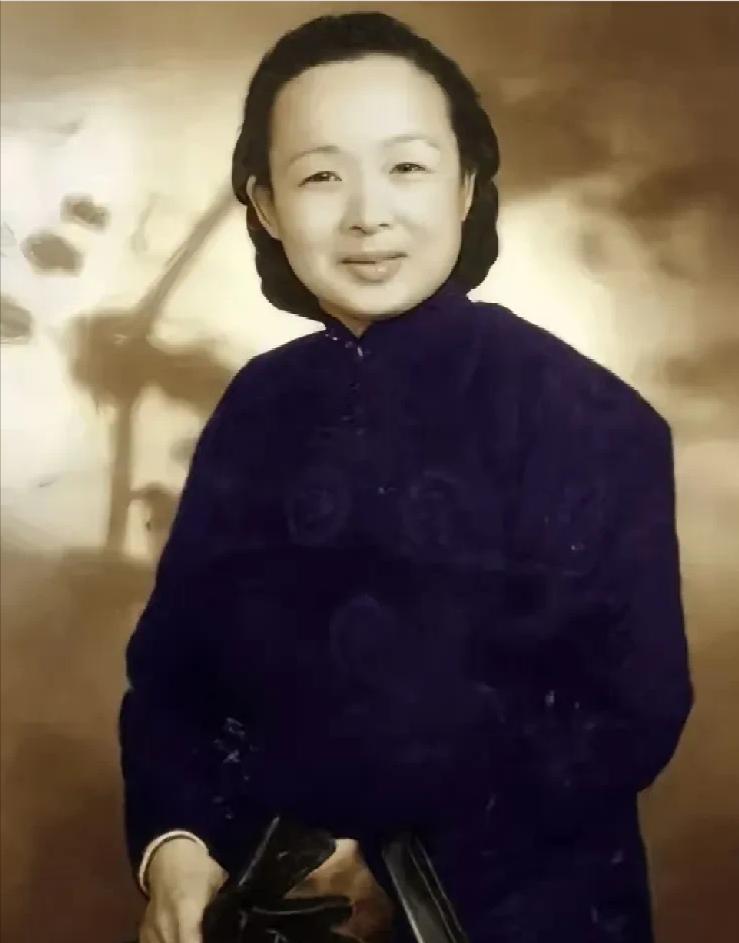[微风]1949年,谢晋元的遗孀向陈毅要了一个房子,陈毅就把吴淞路466号送给她,几天后,有人举报,她带了七八个年轻男子一起入住! 1949年的上海,一封举报凌维诚“作风问题”的信件,让刚被陈毅赠予凌维诚的吴淞路466号别墅变得备受关注。 因为邻居们都看到,这位守寡的夫人竟然和七八个年轻男子同住,一时间议论纷纷,接到举报后,派出所民警在深夜奉命进入别墅调查。 面对民警的询问,屋里的男子们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些泛黄甚至带着血渍的证件。 证件上“524团1营”的番号清晰可见,民警瞬间明白了他们的身份——这些都是谢晋元将军麾下“八百壮士”的幸存者,误会就此解开,在场的民警都向他们举手敬礼,眼里含着热泪。 凌维诚能得到这栋别墅,源于对“八百壮士”功绩的铭记,上海解放才七天,凌维诚就用一张粗纸给陈毅市长写了一封信。 她写信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幸存却无人照料、如同“活着的死人”的“八百壮士”老兵,恳求能给他们一处安身之地,陈毅被“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事迹,以及凌维诚为老兵奔走的义举深深打动。 陈毅当即决定,把这栋原本属于日侨的别墅拨给凌维诚和老兵们使用,秘书提醒他“这是敌产”,陈毅指着不远处的四行仓库旧址说:“墙上每一颗子弹,都比房产证值钱。” 这栋出于敬意赠予的别墅本是老兵们的庇护所,可刚开始就因为男女同住的情况,遭到了邻里的误解和议论。 误会澄清后,陈毅听说了这件事,特意派人送来面粉等物资接济他们,但凌维诚和这些老兵们却委婉地拒绝了。 他们不需要施舍,只想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活,保住尊严,很快,吴淞路466号就不再只是一个住所,变成了一个生产场所。 凌维诚牵头成立了“孤军工业服务社”,别墅后院的竹棚成了他们的生产车间,在这里,独臂的老兵摇着纺车织袜子,腿脚不方便的老兵就坐着粘贴火柴盒的磷纸。 为了让产品有辨识度,他们创立了“孤军牌”品牌,凌维诚甚至拆下自己嫁衣上的金线,在毛巾样品上绣出了品牌名字。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们生产的每一块肥皂上,都刻着从001到414的编号——这正是当年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的确切人数。 当“孤军牌”产品出现在虹口的菜市场时,市民们都自发排起长队购买,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向这些英雄表达敬意,也认可他们靠自己赢得的尊严。 吴淞路466号不仅是生产基地,更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支撑着凌维诚兑现她对老兵们的承诺。 这个承诺是在丈夫谢晋元遇刺后许下的,当时她对幸存的部下说:“团长不在了,我这个团长夫人会担起责任,不会让你们流落街头。” 为了兑现承诺,这位曾经的富商之女告别了优渥的生活,在战后的上海四处奔波,她亲眼见过双目失明的老兵在桥洞下乞讨,见过烈士遗孀带着孩子在垃圾桶里翻找腐烂的菜叶,她也曾向国民政府求助,却没有得到回应,彻底失望。 有了吴淞路466号这个稳定的“家”,凌维诚的承诺有了更坚实的支撑,1952年冬天,她从雪地里救回了冻僵的老兵唐棣,这位曾在战俘营里咬断日军耳朵的硬汉,在睡梦中还高喊着:“团长,我把机枪抢回来了。” 对于那些选择回乡的战友,这里也成了中转站,凌维诚总会凑齐路费和安家费给他们。 1991年凌维诚去世后,她的子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本笔记本,上面工整地记录着107个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标注着“病故”“回乡”等不同的人生结局,这107人都是她曾经资助和收留过的“八百壮士”幸存者或其遗孀,也是她用一生温暖过的人。 主要信源:(《上海解放初期市政工作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