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发生一起悲剧,一家三口来自东北,移民新加坡多年,住在组屋。父母都是高知,女儿在新加坡名校就读,曾是学霸,拥有剑桥博士学位,但后来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 一对来自中国东北的父女被发现双双离世,卧室中70多岁的父亲遗体已化为白骨,客厅门边47岁的女儿徐娜倒在地上。 法医初步判断,两人死亡时间相差约一个月,失去父亲照料的徐娜,疑似因无法自理最终饿死。 徐娜的人生前半段完全是“学霸范本”。 1997年,还是英华初级学院学生的她,就拿下全国中学生华文写作比赛甲组冠军; 2001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本科毕业,仅两年就拿到硕士学位; 打开新加坡本地的论坛,输入“徐娜”两个字,跳出来的帖子标题像一把钝刀——“剑桥博士饿死在组屋”“东北神童为何成了无主孤魂”。鼠标往下滑,有人贴出她1997年领奖的老照片:齐耳短发,白衬衫,笑得像刚擦亮的钢。谁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这抹亮会被时间啃成一把灰。 我住她楼下四年,电梯里碰见过几次。她总缩在角落,怀里抱着超市塑料袋,袋口勒得死紧,像怕谁抢。眼神对上,她先躲,再点头,幅度小得几乎看不出。有回我帮她捡滚到脚边的苹果,她声音轻得像漏气:“谢谢姐,别碰我东西,脏。”那苹果其实光溜溜,没一点泥。后来我才懂,脏的不是苹果,是她脑子里那团雾。 她爸我见过更多次,瘦高个,花白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买菜的推车擦得锃亮。邻居喊他“徐老师”,听说在国内是大学物理教授,移民后教过私立中学,再后来岁数大了,只能给补习社打打杂。他见谁都笑,笑完就低头,像怕欠人钱。有人背后嘀咕:“老徐把女儿当奖杯,捧太高,摔碎了。”我听完不舒服,却也没反驳,毕竟谁家锅底没灰? 真相像猫,白天躲窗帘后,夜里出来踩人脸。警方报告说,老人大概先走,心脏病,一躺下去就没再醒。屋里没开空调,热带潮气像发酵粉,一个月把人发成了白骨。女儿就在隔壁房,门没锁,可她没踏进去一步。是怕,还是已经认不出爸爸?没人知道。冰箱空了,米桶也空了,最后她靠喝自来水续命,胃缩成拳头大。发现她的邻居说,徐娜躺在门边,手指甲抠得满地是痕,像拼命想爬出去,又像拼命想把世界关在外头。 学霸到饿死,跨度太大,大家只能搬出“精神”这块万能布,把所有洞都塞上。有人说她读博那年被导师逼疯,有人说是遗传,她妈年轻时也抑郁,跳了楼。版本越传越邪乎,像给死人穿花衣裳,合身不合身没人管。我翻到她当年在国大的毕业论文,封面写着《华语语系离散叙事中的身份重构》, PDF 打开,第一页致谢只有一行字:献给爸爸,愿你不再漂泊。短短一句,比所有传言都重。 我爸也是老派人,坚信“读书改命”。小时候我考第二,他整张脸能拉到膝盖。徐娜的事传开后,他几天没说话,晚饭时突然冒出一句:“咱们得认,书念到头,可能还是斗不过命。”说完把鸡腿夹给我,像补偿。我那一刻鼻子酸得发辣,仿佛看见二十岁的自己:夜里两点,台灯把脸烤得蜡黄,耳机里循环的是“考不上你就完了”。原来我们都被同一根鞭子抽着,只是有人抽断了,有人抽疯了。 新加坡遍地是“别人家的孩子”,地铁广告牌、补习社橱窗、家长会PPT,笑脸排成墙。可没人贴后续:有人顶不住,从高楼一跃;有人把自己关进病房,一天三颗药,记忆像被橡皮擦啃;也有人像徐娜,慢慢褪成影子,直到影子也碎。这里不缺成功学,缺的是失败学——怎么面对掉队,怎么承认“我撑不住了”,怎么在组屋墙壁那么薄的地方,喊救命却不被当成疯子。 老徐走后,社区办了场小型追思会。来的人不多,志愿者摆了两张照片:一张他年轻时在国内讲台,一张徐娜拿写作冠军。照片摆在一起,像两条平行线终于交汇,却是在灵桌上。牧师念经,声音温柔得像给婴儿拍嗝。我盯着徐娜那张小脸,忽然想起电梯里她说的“脏”。如果哪天她敢把心里那团黑雾掏出来,会不会有人接得住?还是大家只会后退三步,给她贴“有病”的标签? 我搬离那座组屋前,把一本旧笔记本塞进她信箱,扉页抄了菲律宾诗人巴塔的一句话:“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我知道她看不见了,可我希望下一位住客翻到时,能愣一秒,然后拨通求助电话,而不是把门一关,让下一个故事继续烂在黑暗里。 有人怪老徐太倔,不送女儿去专科医院,死撑。可设身处地,他一个异乡人,语言半通,医保薄薄几页,能撑到白发苍苍已算硬核。指责容易,伸手难。我们爱听“逆袭”,不爱看“掉队”,可掉队才是大多数人的日常。徐娜用命扔出一个问题:当光环熄灭,谁来给普通人兜底?如果答案只是“自己扛”,那社会不过是一群各自结痂的孤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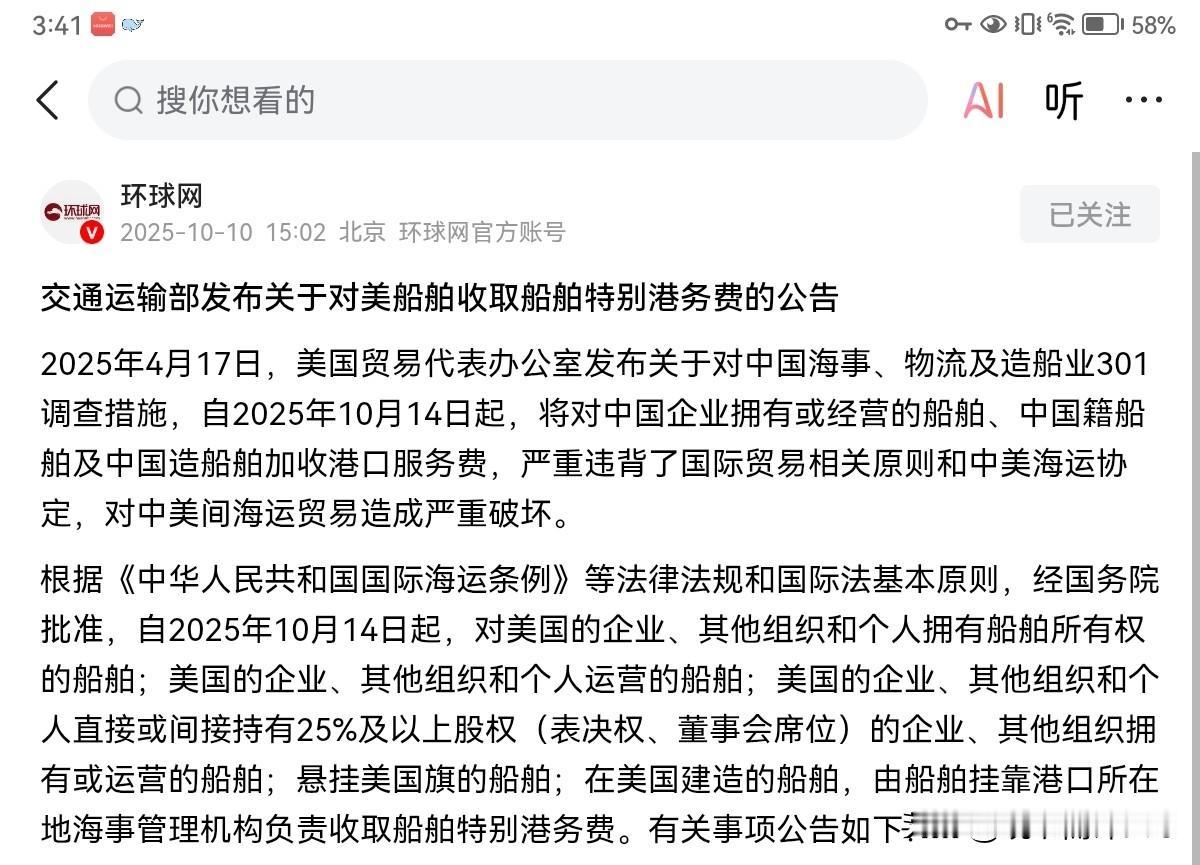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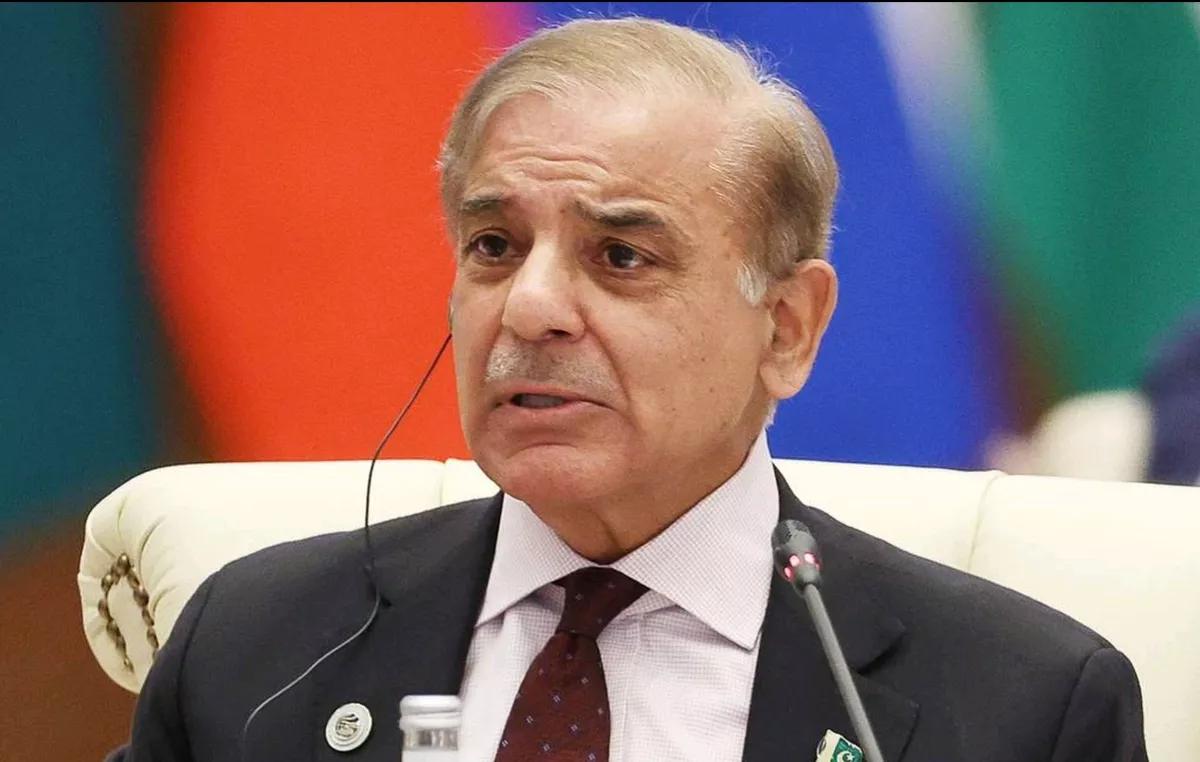


沉没的南极
社会从来不会同情任何人!!!
清风
精神病谁都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