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名臣晁错力主削藩,结果被老父亲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骂道:“削藩是皇帝家事,你一个外人掺和个屁。”晁错义正言辞:“这不是家事,乃是国事。陛下信我,正是我为陛下解忧、为国尽忠之时!” 公元前155年,在长安东市的刑场上,御史大夫晁错被绑在行刑柱上时,他还痴痴的望着未央宫。 他凌晨刚写完最后一道削藩奏疏,正等着皇帝夸他“先生又为朕分忧”,却等来了一队刀斧手。 监斩官的刀光闪过,这位曾让汉景帝言听计从的“帝国智囊”,连喊冤的机会都没留下,就成了西汉最惨烈的政治牺牲品。 其实这个悲剧的开头,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埋下。 晁错的人生底色,是他选的老师法家学者张恢。 不同于文帝推崇的“黄老无为”,他学的是商鞅、申不害那套“以法立威、以术驭下”的硬骨头学问。 汉文帝时,这个年轻人凭两策崭露头角。 一是“重农抑商”,二是“移民实边”。 文帝虽没采纳他最狠的“削藩”和“以蛮夷攻蛮夷”,却也赏识他的才学,让他做了太子刘启的家令。 刘启跟晁错投缘极了。 这个未来的皇帝爱听他讲“诸侯坐大,迟早要反,不如趁早削地”的道理,甚至私下叫他“先生”。 文帝驾崩后,刘启刚即位,就把晁错从内史提拔到御史大夫,甚至还让他管弹劾百官。 此时的晁错,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皇帝信他,旧识捧他,连宫里的宦官都得巴结他。 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实现“削平藩国、巩固皇权”的理想了。 可晁错忘了,长安城里不是只有皇帝。 汉高祖刘邦的庙墙,是朝臣们心中的“信仰红线”,那是汉室江山的根。 晁错为了方便自己上下班,居然让人在庙墙上凿了扇门,把祭祀先皇的圣地变成了自己的“快捷通道”。 老丞相申屠嘉气炸了。 这不是砸我们这些开国元勋的脸吗? 他连夜上奏要砍晁错的脑袋,可景帝只敷衍一笑:“不过是凿个门,至于吗?” 申屠嘉又羞又怒,没几天就抑郁而终。 晁错却跟没事人一样,反而更嚣张了。 既然丞相都搞不定他,那满朝文武谁还能管他? 他修改刘邦定下的宽刑法令,弹劾官员,连窦婴这种跟随文帝的老臣都跟他不对付。 有人说他“恃宠而骄”,他反驳:“我是为陛下办事,谁敢拦我?” 可没人提醒他,皇帝的宠信,从来不是“免死金牌”。 公元前155年,晁错的老父亲从沛县老家赶来,连夜闯进御史台。 老人死死盯着儿子:“你这是要把晁家往火坑里推啊!削藩是皇帝家的事,你一个外人凑什么热闹?诸侯们恨你入骨,早晚要牵连全家!” 晁错还沉浸在“为国尽忠”的热血里:“我不削藩,大汉江山就要乱!我是为了天下百姓!” 老人骂道:“刘氏安稳了,晁氏要灭门!我先走一步,省得看你死!” 说完,竟服毒自尽了。 晁错捧着父亲的遗书,只觉得是老人胆小。 他没看见,父亲的眼睛里全是绝望。 最终,景帝下了削藩令,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吴王会稽豫章二郡。 诏书刚发出去十天,吴王刘濞就联合楚、赵等六国起兵。 他们等这天等了几十年:“诛晁错,清君侧!” 长安城乱成一锅粥。 其实,晁错却犯了致命错误。 他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在京城坐镇。 这话一出口,景帝的脸当场就黑了。 你晁错怂恿我削藩,现在让我去拼命,你倒躲得舒服? 满朝文武也炸了:“晁错这是想把陛下当枪使!” 窦婴趁机把政敌袁盎带进来。 袁盎直截了当地说:“七国反的就是晁错,杀了他,叛军就没借口了!” 景帝沉默了三天。 第三天,太监来传晁错:“陛下请您去东市议事。” 晁错还穿着朝服,直到看见行刑台,才明白自己完了。 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算计了大汉的江山,却没算计透皇帝的心思。 刀光落下的瞬间,晁错的眼泪砸在地上。 他不是怕,是悔。 更讽刺的是,晁错的人头送到吴王刘濞那里,刘濞只扫了一眼,笑着说:“寡人已经是东帝了,谁要这腐儒的头?” 晁错死了,七国却没退兵。 景帝这才想起周亚夫,派他率军平叛。 三个月后,七国兵败,吴王刘濞被杀。 周亚夫成了救国功臣,可没几年,也因为“刚直”被景帝下狱,活活饿死。 原来景帝的凉薄,从来不是只对晁错。 后人赞晁错“有管仲、晏婴之才”,说他“为国尽忠”。 可他的悲剧,恰恰在于“太忠”。 他以为皇帝会为他兜底,却忘了在皇权面前,所有的“为国”都是“为君”,所有的“忠臣”都是“棋子”。 他的死,不是结束,是开始。 它告诉后世所有臣子,伴君如伴虎,最该防的,不是政敌,是皇帝的“忘恩负义”。 最该懂的,不是法家的“规矩”,是人心的“凉薄”。 主要信源:(人民资讯——如果没有晁错,是否还会爆发七国之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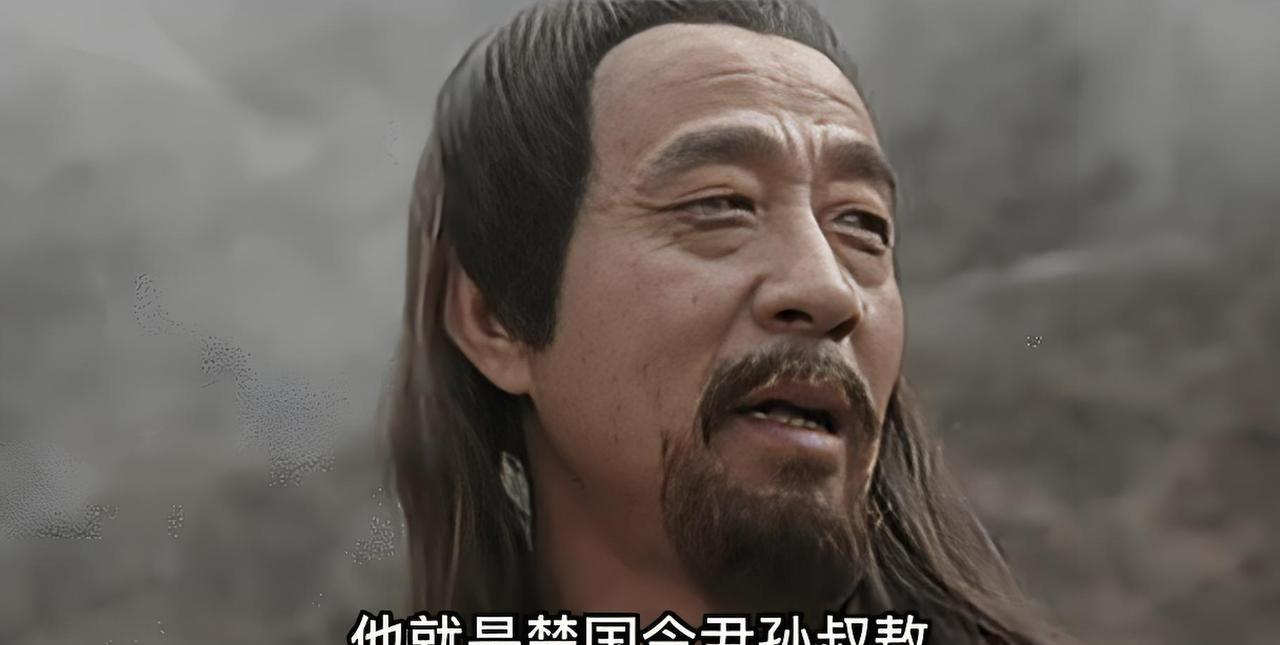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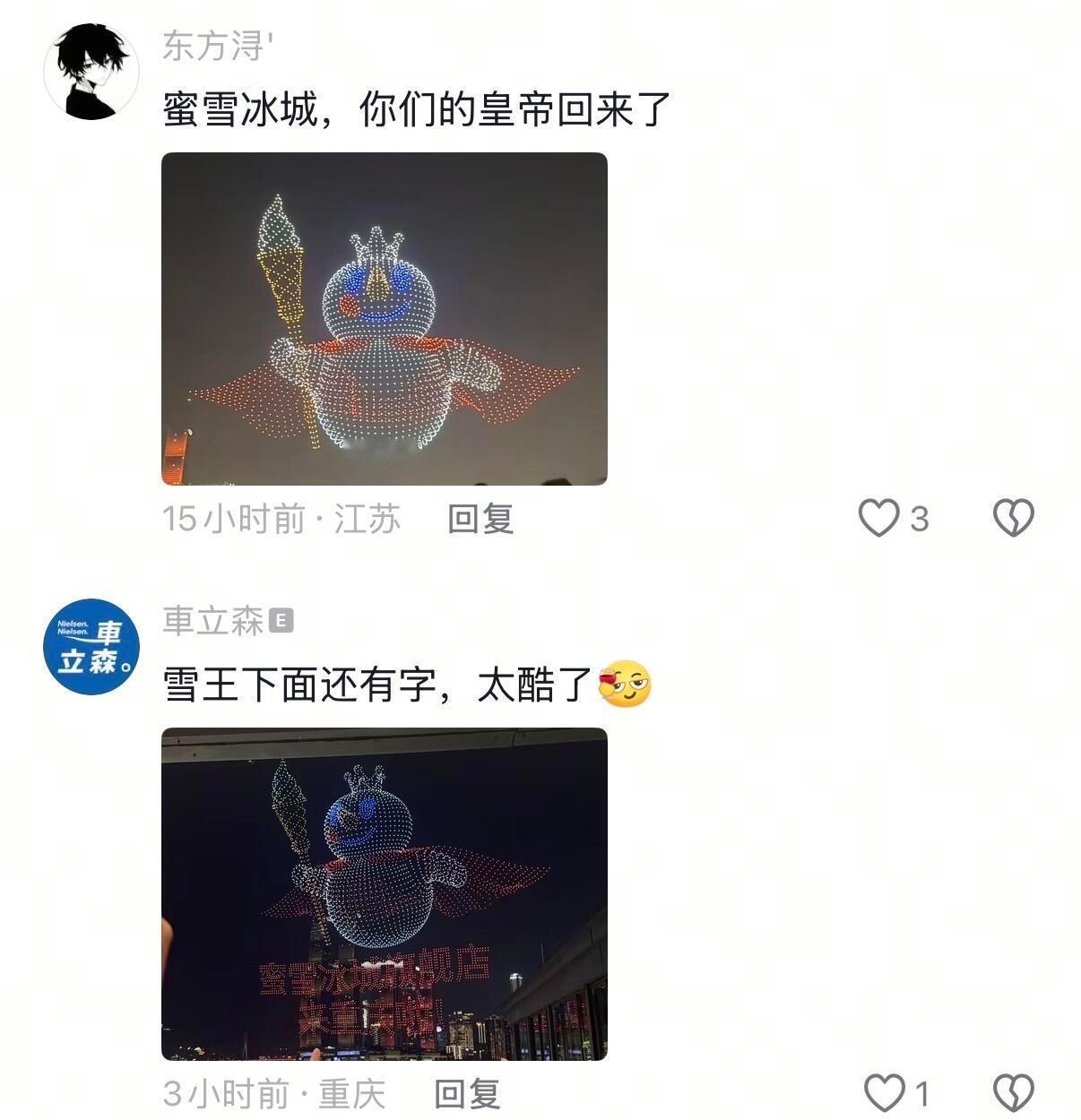
![乾隆真是职业皇帝名不虚传[吃瓜]](http://image.uczzd.cn/514115608926668554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