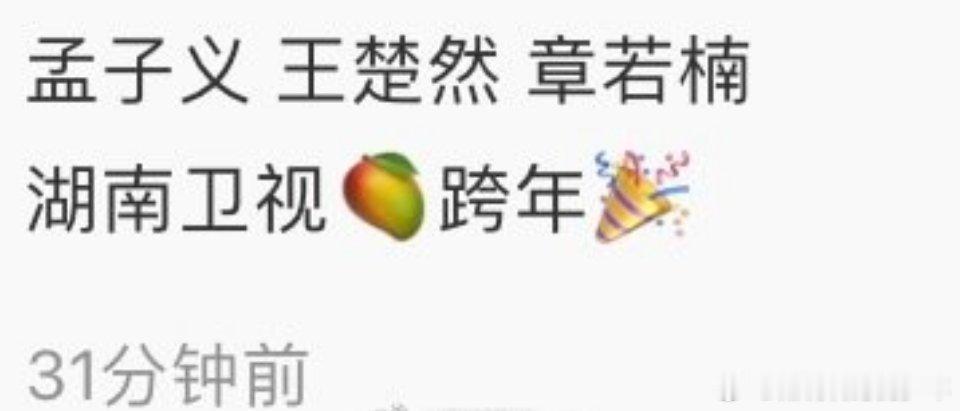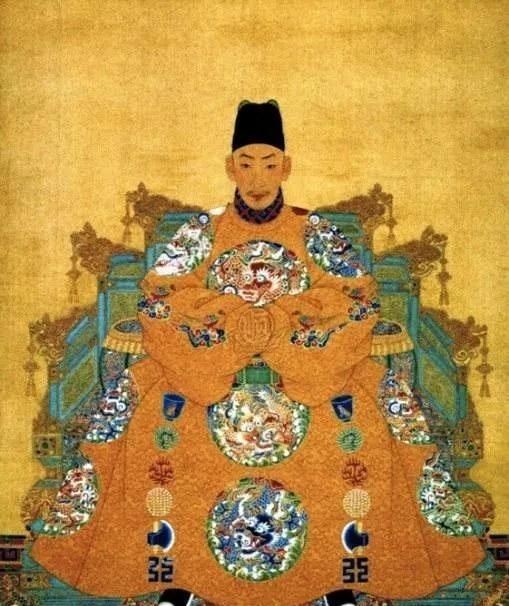清朝有一个地方大官,名叫沈秉成,极为好色,娶了几十个小老婆,却没有一个做他的正妻。沈秉成在晚清官场颇有地位,此人酷爱纳妾却绝不立正室。 同治光绪年间,若要给晚清官场那些“风流韵事”排个座次,沈秉成的名字总被好事者拎出来。 有人会说他“纳妾三十房却不立正妻”,又说被十六岁才女用计逼成“明媒正娶”。 可翻查正史与文人笔记,这故事倒像杯掺了水的茶。 茶底是真,水却兑得太满。 真实的沈秉成,是个被政绩耽误的“文艺老头”,他与第三任妻子严永华的姻缘,才是晚清官场最堪寻味的雅谈。 沈秉成生于浙江湖州,1856年考中进士,算是科举正途出身。 他从翰林院编修起步,历任道台、巡抚,最风光时官至两江总督。 这人最绝的不是官做得大,而是“能文能武”。 甚至不少老百姓感谢他,还给他立了生祠。 罢官后他隐居苏州,成了收藏界的“老饕”。 不过,这位“能吏”的婚姻轨迹却常被误读。 史书记载,他前后有三任正妻。 前两位都因病早逝,第三任才是与他相伴半生的严永华。 所谓“纳妾三十房”的说法,更像民间对“官宦多妾”的刻板想象。 晚清官员纳妾虽常见,但沈秉成的正妻之位始终虚位以待,直到遇见严永华。 严永华的来头,比故事里更惊艳。 她是湖州才女,字少蓝,号不栉书生。 要知道,清代女子有“字”已属罕见,“号”更非寻常闺阁女子敢取。 她工诗善画,尤其精于花鸟题材,朋友圈里传着她的作品,连哥哥严缁生都常拿她的画向好友“炫耀”。 沈秉成第一次见到严永华的画,是在严缁生家中。 那是幅手绘花鸟,笔锋灵动,题诗更妙,他盯着画看了半日,当场拍案:“此等才情,该是知己!” 回家后,他向第二任妻子姚氏感慨:“若有这样的女子为妻,也算不负此生。” 姚氏笑着打趣:“您倒会说,哪有这么巧的事?” 谁料命运偏要成全这句戏言。 几年后姚氏病逝,沈秉成想起前言,又想起严永华的画。 此时严永华已二十九岁,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因才名太高无人敢轻易提亲,索性待字闺中。 沈秉成托人上门,严家早知他的才名与为人,加之兄长严缁生本就欣赏他,这门亲事便顺顺当当定了。 1884年,沈秉成与严永华完婚。 这对相差十余岁的夫妻,过得比戏文还美。 严永华懂他的金石收藏,他能品她的诗词书画。 他教她拓印碑帖,她为他研墨题跋。 沈秉成有两块端砚,石纹似双鱼,他给砚台取名“鲽”,又把家中藏书楼唤作“鲽砚庐”。 “鲽”是比目鱼,寓意夫妻相倚,“砚庐”则是两人精神世界的巢穴。 后来沈秉成遭政敌弹劾罢官,夫妻二人索性隐居苏州。 在江苏巡抚张之万帮助下,他们买下前朝陆锦的“涉园”旧址,大兴土木改建成“耦园”。 “耦”是“双”的意思,既指两人相伴,也暗含“夫妇归田,并肩耦耕”的期许。 严永华常在园中抄录诗稿,沈秉成就坐在一旁治印,偶尔抬头看她,眼里全是温柔。 至于民间流传的“盛氏父女设局”故事,实是张冠李戴。 查严永华的《耦园日记》,她嫁入沈家时,沈秉成尚未有正妻空缺。 前两任妻子已先后去世,她是作为继室被迎娶的。 所谓“用聘礼捐灾民逼封正妻”,更像是后人将其他官员的风流韵事安在了沈秉成头上。 真实的严永华,从不是“被算计的小妾”,而是沈秉成主动求娶的“灵魂伴侣”。 如今的耦园,仍是苏州园林的代表。 游客穿行在粉墙黛瓦间,导游总爱指着“鲽砚庐”说:“这是沈大人和严夫人的藏书楼,当年里面藏着万卷书,还有块双鱼纹的宝贝砚台。” 最让人唏嘘的,是耦园水阁那方“耦园佳侣”的印章拓片。 当年严永华抄录的日记,如今成了文物,泛黄的纸页上,不仅写着玉兰初绽的日子,更藏着一段被岁月沉淀的真心。 不是什么“老官僚被小妾设计”,而是两个懂彼此的人,在晚清的风雨里,守着一座园子,把日子过成了诗。 历史总爱添油加醋,但有些故事,终究会回归本真。 就像沈秉成与严永华,他们留下的不是“纳妾”的笑谈,而是一段“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晚清雅事。 主要信源:(镇江金山网——清代沈秉成写金山长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