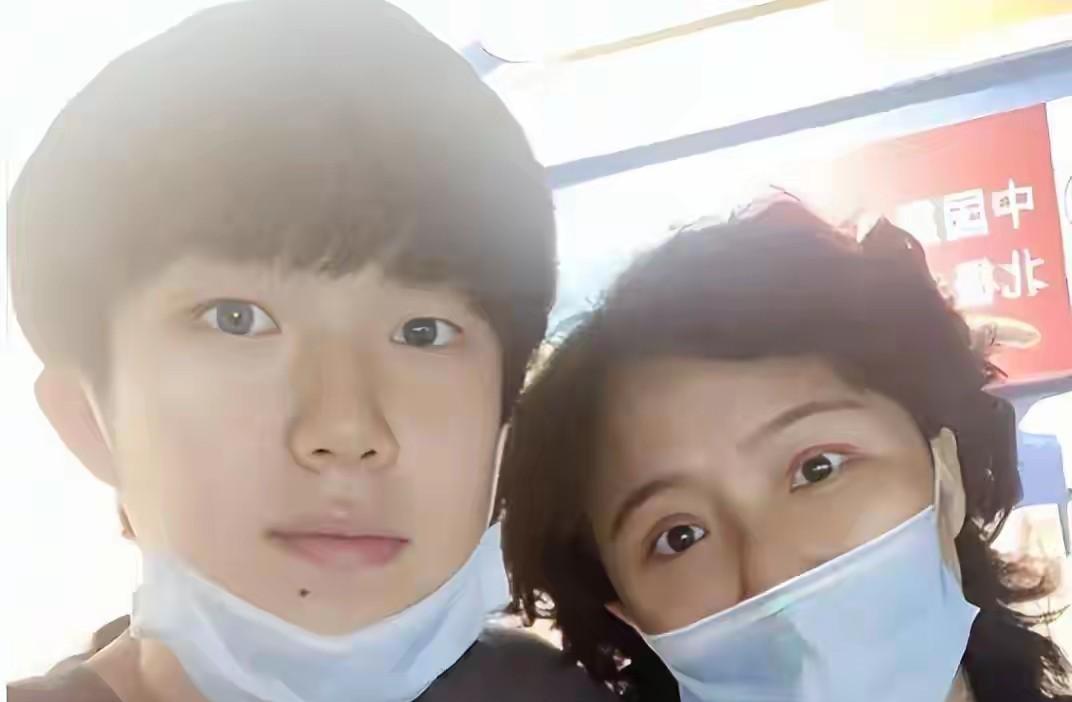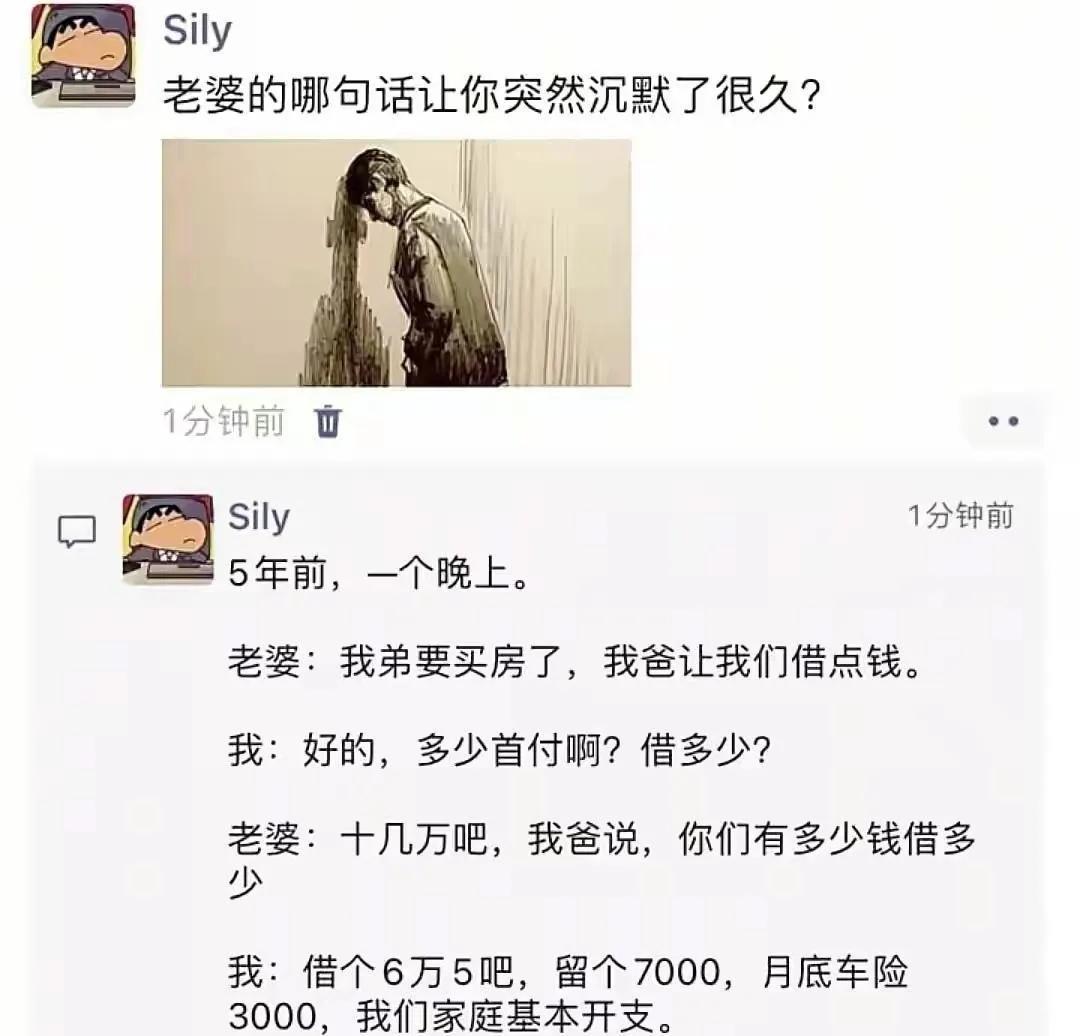1997年,48岁的耿保国不顾妻子反对,借遍亲朋好友又咬牙贷款几十万,终于凑够了120万买下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明清古宅,此后他又把后半辈子的时间,都放在了修缮复原这座老宅上面,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和这座宅子近况如何? 主要信源:(界面新闻——耿保国:120万买来的平遥第一大院隐士般地活着) 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平遥古城西大街的一座古宅前,耿保国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他手持软布,仔细擦拭着门楣上"浑漆斋"三个鎏金大字。 这座占地三亩余的明代宅院,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庄重,青砖灰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沉淀。 院中的老槐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树影斑驳地洒在青石板上。 1997年的那个春天,当耿保国第一次踏进这座破败的院落时,眼前的景象令人唏嘘。 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十一间窑洞多数已经坍塌,残破的窗棂在风中吱呀作响。 正房的屋顶破了个大洞,阳光直射进屋内的青砖地面,照亮了四处散落的碎瓦。 当地老人都说这宅子"不干净",但耿保国却在残垣断壁间看到了别样的价值——那些精雕细琢的梁柱虽然蒙尘,却依然能看出昔日的风华。 那时的耿保国正值中年,作为平遥推光漆器的传承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同时满足居住和创作的空间。 这座被世人遗忘的古宅,在他眼中恰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 尽管妻子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往火坑里扔钱,他依然咬牙凑齐了120万元,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记得签契约那天,他的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后悔,而是意识到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修复工程从清理院落开始。 耿保国带着两个尚在读中学的儿子,一锹一铲地清除积年的杂草和瓦砾。 最先清理出来的是院中的一口古井,井水依然清澈见底。 最困难的是重建主体结构,他专门拜访了当地的老工匠,学习传统的建筑技艺。 那些日子,他常常天不亮就起床,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古城的大街小巷,寻找合适的建筑材料。 在修复门楼时,耿保国别出心裁地融入了漆器工艺。 他选用上等木材制作匾额,每天在工作室里待到深夜,运用推光漆器的独特技法,经过八道工序精心打磨。 记得有一次,为了调配出最合适的底色,他连续试验了十几种配方,手上沾满了漆料。 最后用真金描字时,他屏住呼吸,生怕一丝颤抖就会破坏整体的美感。 这个过程耗费了整整五个月时间,但当成品悬挂上门楼时,过往的行人无不驻足赞叹。 宅院内的装饰更是凝聚了耿保国的心血。 他将漆器艺术与建筑完美结合,在门窗、梁柱上精心绘制传统纹样。 东厢房的隔扇门上,他绘制了"岁寒三友"图案,每一笔都透着深厚的功力。 南面的影壁则采用了浮雕技法,描绘着平遥古城的市井生活。 这些装饰不仅美观,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随着平遥古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旅游业迅速发展。 有个开发商出价千万想改建成高档会所,还有个旅游公司许诺给他分红,但都被耿保国婉言谢绝。 他记得当时对儿子说: "这宅子就像咱们家的老人,怎么能拿来卖钱呢?" 如今,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访。 耿保国总会热情地为他们讲解宅院的历史,演示漆器制作工艺。 有时看到感兴趣的年轻人,他还会手把手地教他们基础的推光技法。 两个儿子如今都已成家立业,继续协助父亲维护宅院,传承技艺。 夕阳西下时,耿保国喜欢坐在院中的石凳上,看着光影在青砖墙上移动。 这时常有邻居家的孩子跑来听他讲故事,他就娓娓道来这座古宅六百年的沧桑变迁。 他说这宅院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本书继续被后人翻阅。 二十多年的坚守,让耿保国从一位普通艺人成长为文化传承的守护者。 去年,他的小孙子在宅院里学会了第一个漆器图案,这让他倍感欣慰。 这座古宅的价值,早已超越了金钱的衡量,成为平遥古城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见证着一个传统艺人对文化的执着与热爱。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