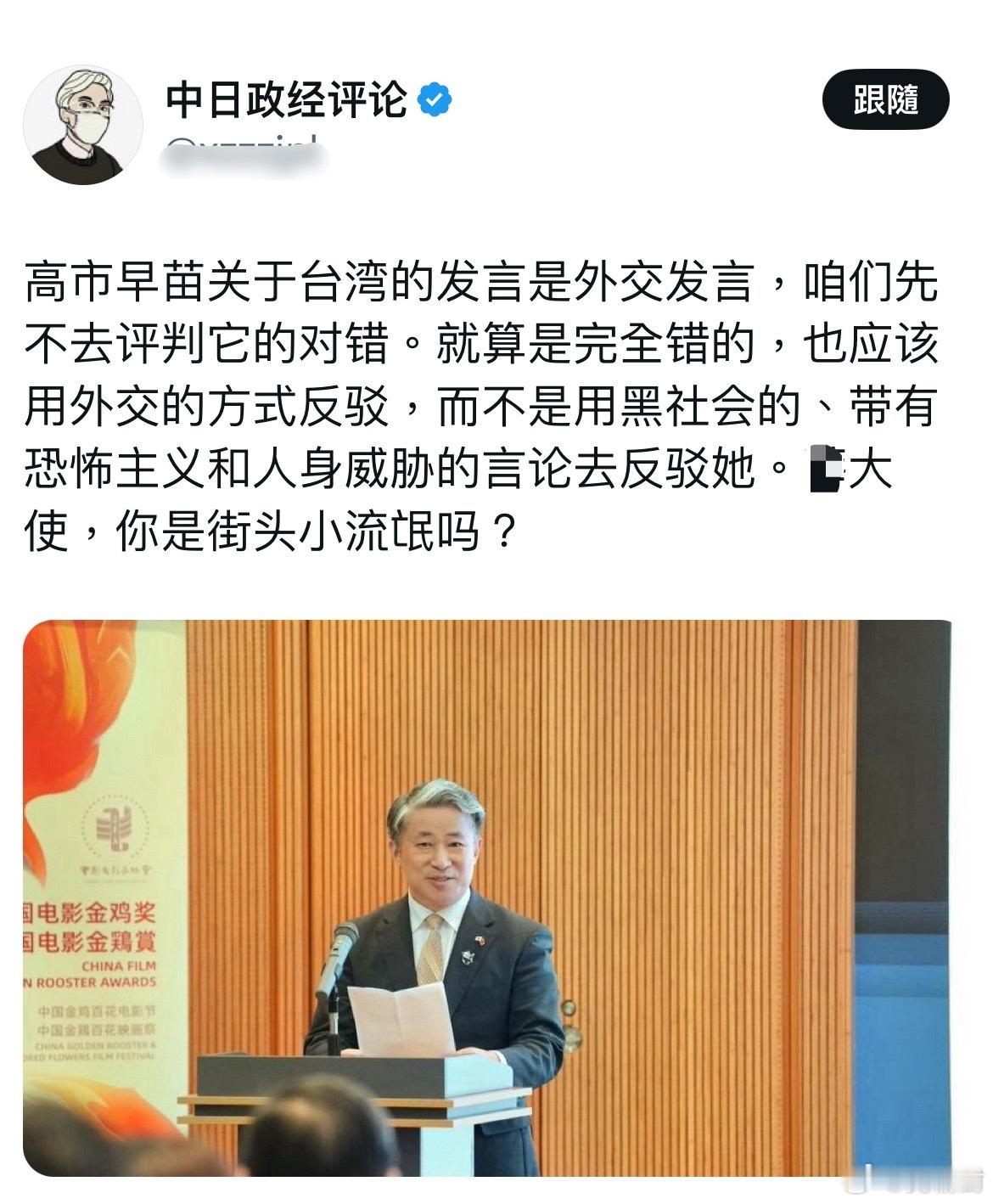煤油灯的光裹着红纸的暖,晃在土墙上,“囍” 字边角被风吹得轻轻卷,是村东头王婶剪的,剪得不算规整,却透着实在的喜兴。我(柱子)坐在炕沿上,粗布褂子的衣角被攥得发皱,手心的汗浸透了布料,黏在腿上。秀莲坐在对面的木凳上,刚掀了红盖头,鬓角别着朵干野蔷薇 —— 是她昨天上山摘的,压了小半天,还留着点淡香,衬得她眉眼比平时更软。 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虫叫,我咽了口唾沫,嗓子发紧,终是没忍住,手指头抠着炕席边儿,低声问:“秀莲,我知道你以前……以前是十里八乡的俏人儿,追你的人排到河对岸,听说还有供销社的、开拖拉机的,条件都比我好,你咋……咋选了我?”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怕戳着她痛处,头埋得更低,像个做错事的娃。 秀莲没立马答,只轻轻笑了声,那笑声软乎乎的,像春日里化了一半的雪。她伸手把鬓角那朵野蔷薇摘下来,放在手心转了转,花瓣边缘有点蔫,可那点淡香倒更清楚了。“你看这花,”她声音不高,却听得真切,“昨天在山上看着艳,摘下来压了半天,没蔫透,还能闻见味儿。有些花看着水灵,插进瓶里一天就耷拉脑袋,中看不中用。” 我抬头瞅她,她正看着我,眼睛在灯影里亮堂堂的,不像平时见着我时总躲着。“以前是有不少人追,”她手指摩挲着野蔷薇的梗,“供销社那小伙,给我送过的确良衬衫,红底儿带小白花,洋气。可后来我撞见他跟村西头二丫在河边拉手,衬衫的第二颗扣子都松了,他说是二丫帮他缝的。”她顿了顿,嘴角撇了撇,像说别人的事儿,“还有开拖拉机那,说要带我去县城住砖瓦房,可我娘让他帮着拉袋化肥,他嫌我弟腿脚不利索,说‘带着个瘸子,将来是累赘’,转头就把化肥拉给他老丈人家了——那会儿他还没跟我处明白呢。” 我听得心里发堵,想替她骂两句,又不知道咋说,只能攥紧了衣角。 “你不一样。”秀莲忽然凑近了点,煤油灯的光把她半边脸照得暖烘烘的,“去年麦收后,我家屋顶漏雨,夜里下大雨,我跟我娘拿盆接水,叮叮当当吵得没法睡。你听见动静,披着蓑衣就来了,踩着梯子上房,雨水顺着你裤腿往下淌,你也没吭声,愣是把漏洞堵严实了。第二天我娘给你煮鸡蛋,你揣兜里就跑,说‘婶子留着给柱子吃’——我弟叫柱子,跟你一个名儿。” 我猛地想起那事儿,当时光顾着堵漏洞,怕漏得更厉害,哪顾得上鸡蛋。“那、那不是应该的么……”我结巴了。 “上个月我去井台挑水,桶沉,我晃悠着走不稳,你从地里回来,二话不说接过扁担,帮我挑到家门口,扁担绳勒得你肩膀红了一片,你还笑,说‘秀莲你这劲儿得练,不然将来咋挑水浇菜’。”她说到这儿,忽然笑出了声,眼睛弯成月牙,“你话少,可你做的事,桩桩件件都实在。我娘说,过日子就像磨盘,看着笨,转起来稳当,能磨出细面。那些花里胡哨的,看着光鲜,风一吹就散了。” 她把那朵野蔷薇别回我胸前的扣子上,花瓣蹭着我脖子,有点痒。“我选你,不是选条件,是选个能跟我一起把日子过瓷实的。你穷点咋了?咱俩有手有脚,开春多种两亩土豆,冬天多编俩筐,日子总能好起来。就怕人不实在,心飘着,那才过不长远。” 我摸着胸前的野蔷薇,花瓣糙糙的,却带着她手心的温度。原来我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她都记着呢。我鼻子一酸,想说点啥,却只憋出一句:“秀莲,我、我以后都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她噗嗤笑了,伸手把我脑门上的汗擦了擦,手糙,却比我娘的手还暖。“谁要你干啥都听?咱俩商量着来。”她把红盖头往我肩上一搭,盖头的边角扫过我脸颊,软乎乎的,“灯油快没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给王婶送喜糖呢。” 我看着她转身去吹灯,背影在墙上晃了晃,像幅暖烘烘的画。窗外的虫还在叫,可我心里踏实得很,攥了半天的衣角终于松开了,手心的汗也干了,只剩下野蔷薇淡淡的香,和她那句“把日子过瓷实”,在心里慢慢漾开,比煤油灯还暖。
气象无人机,肯定是制式装备
【1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