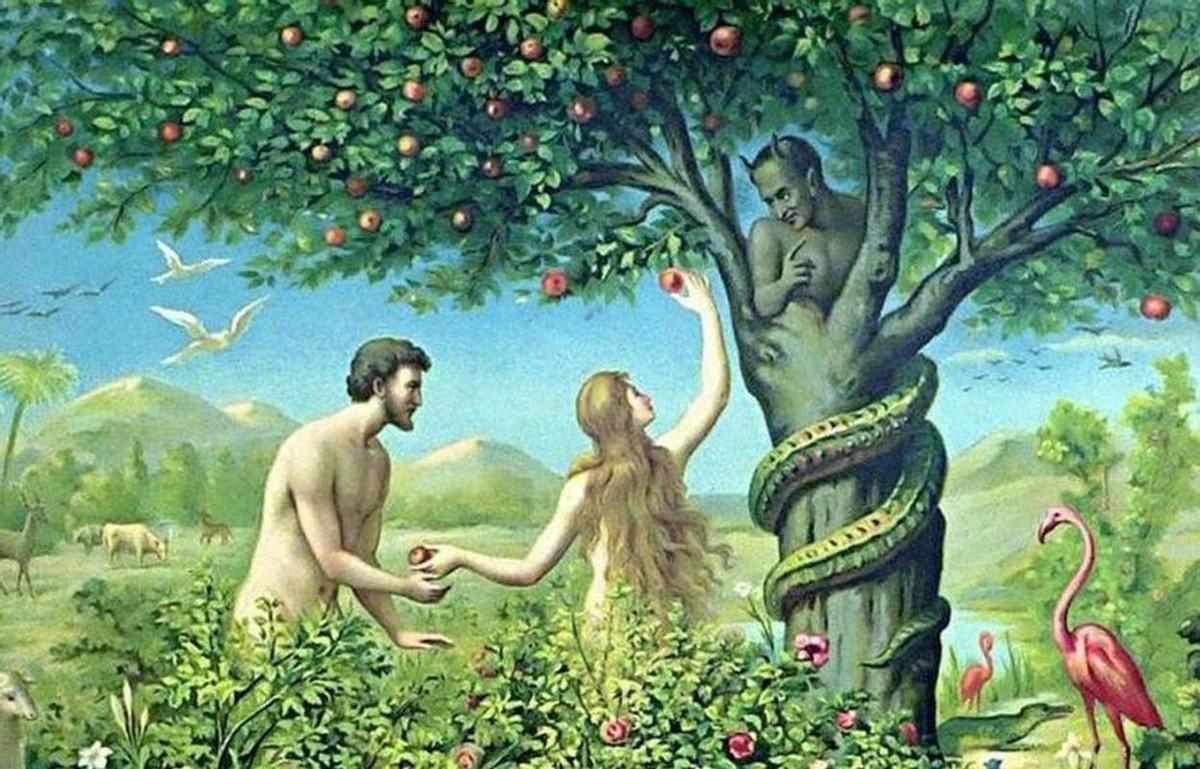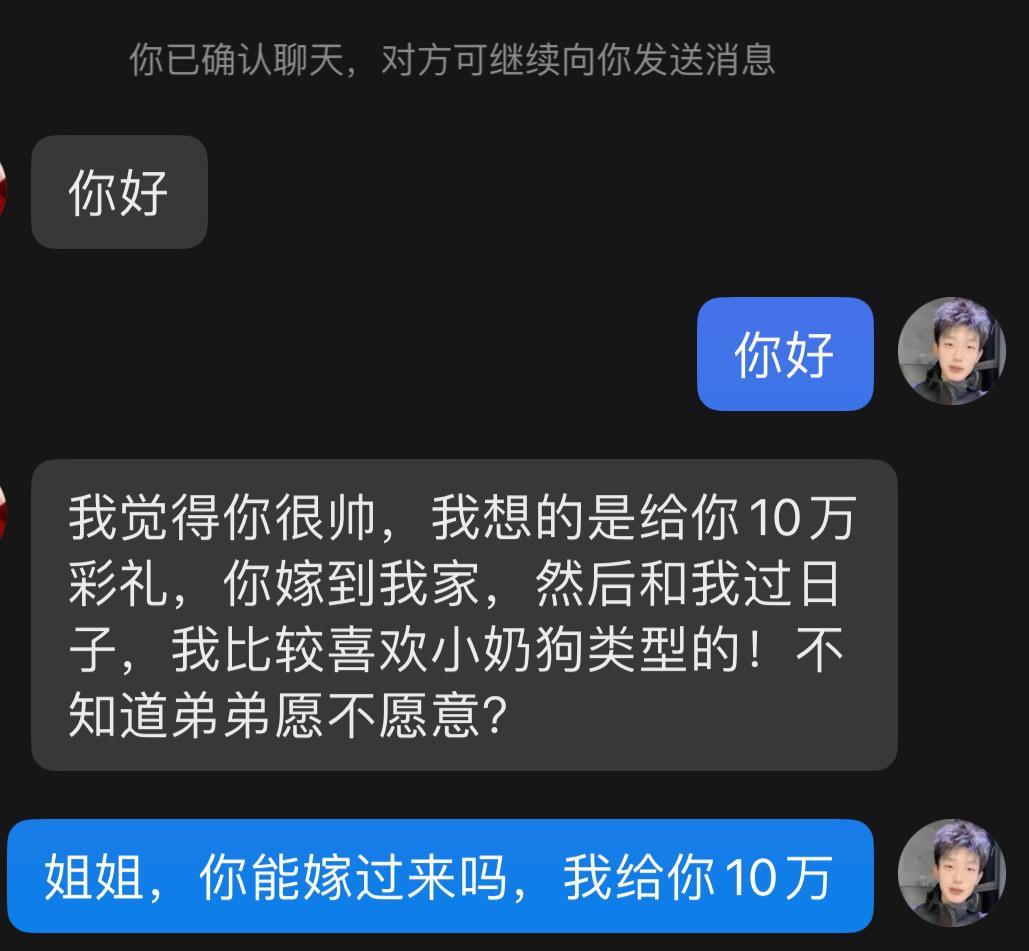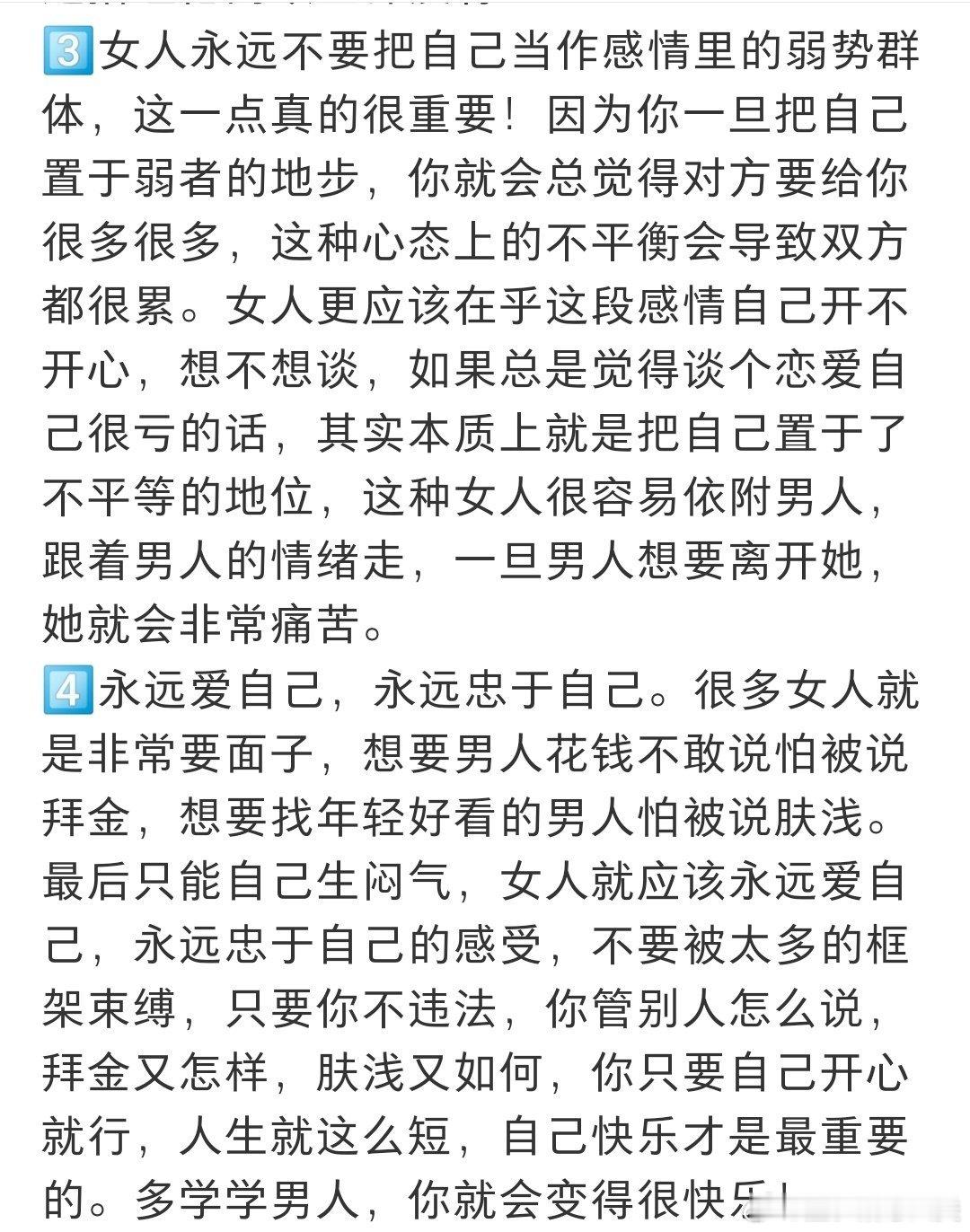人皆由女性所生,那么在人类起源前,第一位女人是从哪里来的? 每个孩子都问过这个问题。 "妈妈是谁生的?" 外婆乃何人所出?此疑问虽简,却似涟漪,于思绪间缓缓荡开,牵引我们回溯家族生命传承的幽微脉络,探询那隐匿于往昔的答案。 "外婆的妈妈。" "那外婆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最开始那个妈妈,是谁生的?" 问到这儿,大人通常就沉默了。此问题宛如一条自噬其尾的蛇,陷入无尽的循环之中。无论怎样绞尽脑汁去思索、去周旋,皆难以挣脱这无解的困局。可它真的无解吗? 神话最先给出了答案。 中国人说,女娲用黄土和水,照着自己的样子捏了一个个小泥人,泥人落地就活了,这就是最早的人。据西方传说,上帝趁亚当陷入沉睡之际,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以这奇妙之法创造出了夏娃,开启一段独特的故事篇章。两个故事隔着万里,却有同一个执念——必须给"第一个"一张确定的脸。 这是古人安放焦虑的方式。面对浩瀚的未知,总得有个说法,哪怕是想象的。 可想象终究是想象。 1859年,达尔文将《物种起源》掷于世人眼前,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千层浪。神创论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大厦,自此开始摇摇欲坠。这个放弃神学、跟着贝格尔号漂了五年的年轻人,用成千上万的标本告诉世界:人不是被谁凭空造出来的,是从更古老的物种一步步变来的。 一步步,这三个字是关键。 进化不是变戏法。古猿不会某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人。从南方古猿到能人,从直立人到智人,每一代和上一代的差异小到几乎看不见——骨盆稍微宽了一点,脑容量稍微大了一点,手指稍微灵活了一点。 这些细微的变化,在几百万年里一代代叠加,才让古猿的特征慢慢褪去,人类的轮廓慢慢浮现。 你没法在一条流动的河里,指着某一滴水说:"看,这就是第一滴河水。" 1974年,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洼地,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森有了重大发现——他成功发掘出一具化石。她生活在320万年前,脑容量只有现代人的三分之一,但已经能直立行走。约翰森给她取名"露西"。 很多人把露西当成"人类之母",觉得找到起点了。约翰森本人已清晰记述:露西并非起始之点,不过是那漫长链条上的一个节点罢了。在她之前,尚有距今440万年前的“阿尔迪”,那是更为古老的地猿始祖种。它们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独特印记,见证着生命演化的漫长进程。 那链条悠悠地向前延展,似有无尽的执着。它于时光里不断延伸,仿佛永不停歇,望不见尽头,仿若要将这未知的前路一一丈量。 那"线粒体夏娃"呢?此般名字,乍一听,恰似蕴含着答案的神秘韵味,仿佛在不经意间就会将那未知的谜底揭晓,引人遐想。 线粒体堪称细胞内的能量工厂,独具特性:它仅经由母亲遗传给后代。受精之际,父亲精子中所含的少量线粒体,根本无法进入卵子,故而难以实现父系传递。故而,每个人的线粒体DNA皆可一路向上溯源,仿若沿着一条隐秘的时光脉络,追溯至妈妈、外婆,乃至外婆的母亲,层层探寻遗传的密码。最终,研究发现,所有人的线粒体皆追溯至同一位女性。她宛如隐匿于时光长河中的神秘源头,为人类线粒体的传承铺就了最初的轨迹。 她栖居于约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大地。彼时的非洲,是生命演化的摇篮,而她,亦在那片广袤土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生存印记。 可她不是"第一个女人"。 当时地球上还有别的女性,只是她们的线粒体基因在后来的繁衍里断了——后代全是儿子,或者中途绝嗣。"线粒体夏娃"只是运气好,她的基因传承没断裂,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她并非人类演化的起点,而是“最近的共同母系祖先”。她如历史长河中一座特殊的里程碑,连接着过去无数的脉络,却绝非源头。 我们缘何如此执着于探寻“首个”?在漫漫求知与探索之途,这“第一个”似乎有着别样魔力,引得众人孜孜以求,究竟是何缘由促动这份执念? 因为我们习惯了线性思维。铅笔是工厂造的,工厂是工人建的,工人是父母生的——万事万物都该有个绝对的起点,对吧? 可生命的逻辑不是这样的。 物种演化是种群整体的缓慢迭代,不是某个个体的突然变身。就算真有一个"最接近人类"的古猿女性,她的父母还是古猿,她的后代也只是过渡形态。只有当整个种群都积累了足够多的人类特征,生殖隔离彻底形成,"人类"才真正诞生。 这个过程里,没有哪一个女性是独一无二的起点。 我们追问"第一个女人从哪来",本质上是不愿承认自己的平凡。我们总觉得人类是特殊的,该有个神圣的开端,一个标志性的"第一"。 可真相是,我们只是自然演化里的普通一环。 没有凭空出现的第一个女人,只有无数代在远古荒野里生存、繁衍、传递生命的女性。她们,或是露西,或是阿尔迪,更代表着无数湮没于历史长河、未曾留下姓名的古人类母亲。她们以柔弱之躯,在人类演化进程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她们不是起点,是接力者。 信息来源:《人皆由女性所生,那么在人类起源前,第一位女人是从哪里来的?》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