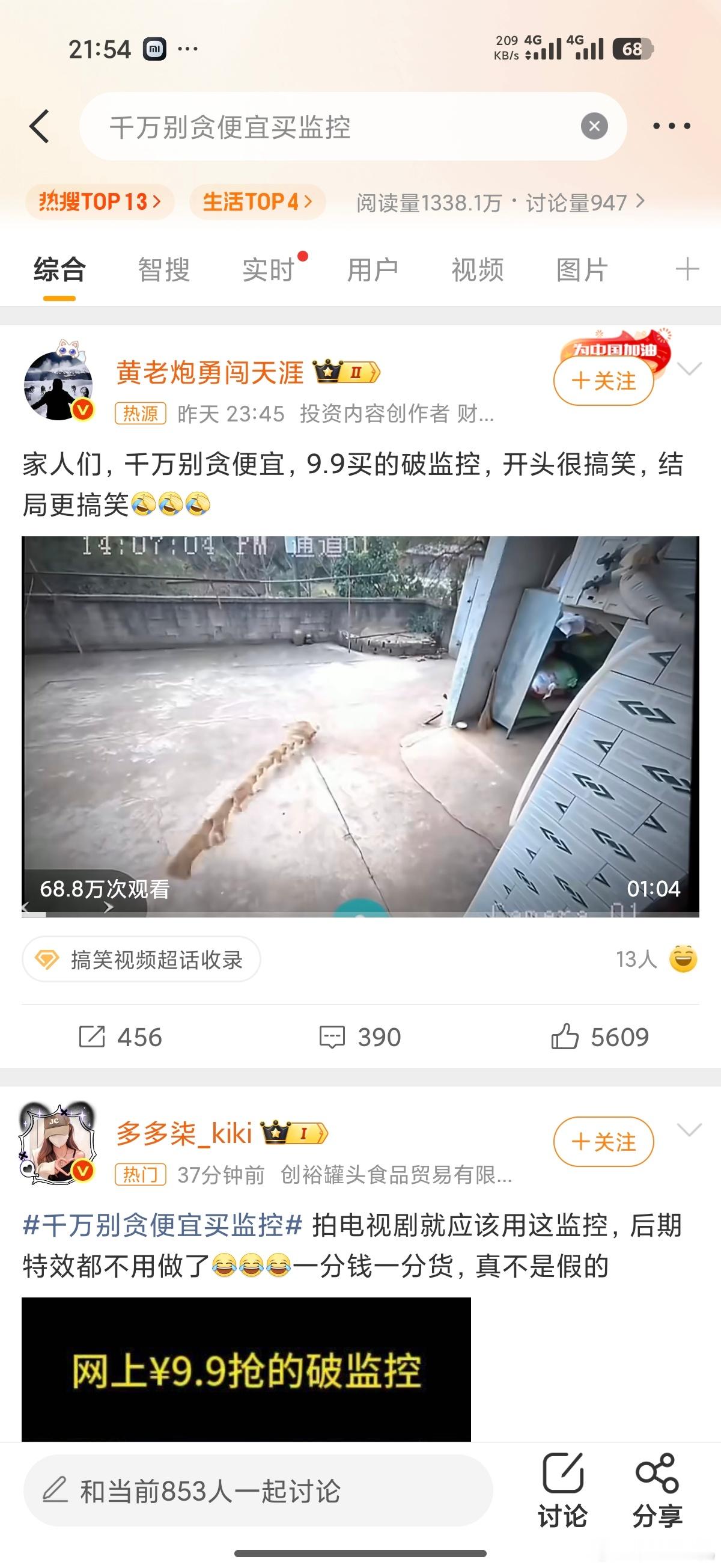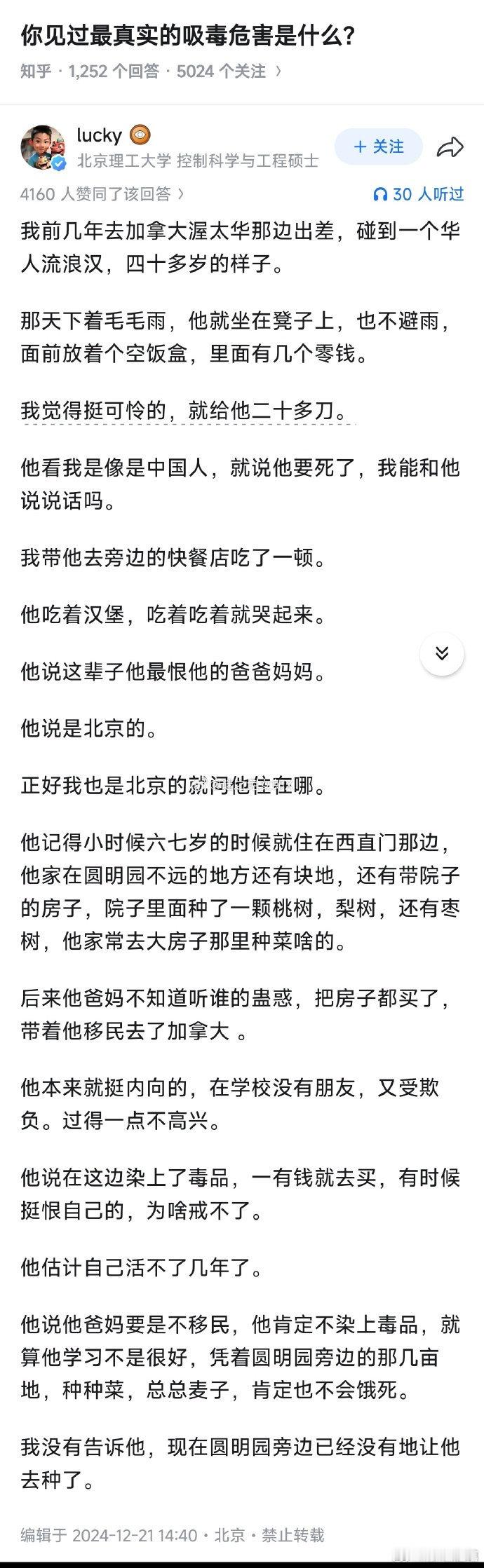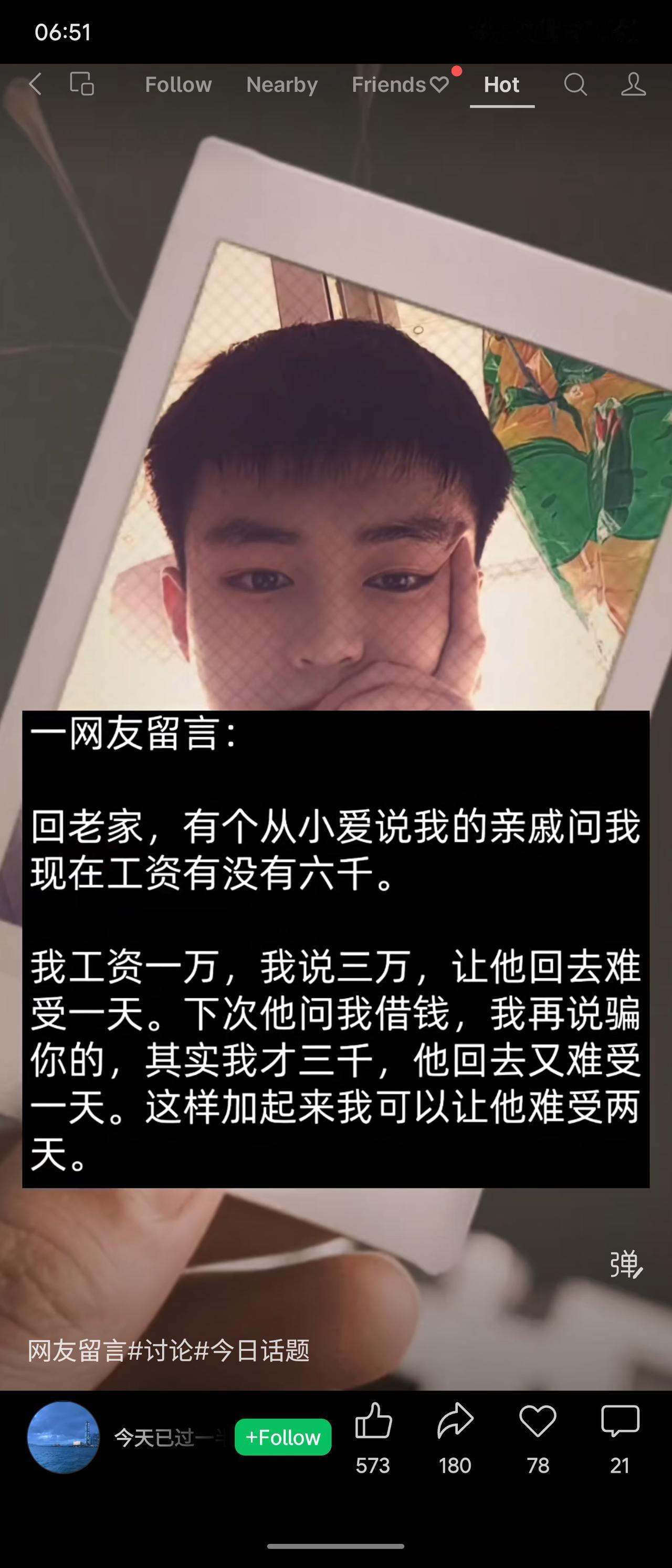1850年的伦敦,一场特别的派对正在萨维尔街的一栋豪宅里进行,空气中弥漫着陈年腐木、香料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糊味。
在几十位穿着燕尾服和紧身裙的贵宾注视下,外科医生小心翼翼地剪开了木乃伊身上发黑的亚麻布。
每一次布料的剥落都伴随着粉尘的飞扬,那是跨越千年的死亡气息,但在场的人并没有感到恐惧,反而像是在等待某种神圣的降临。
散场时,管家为每位客人准备了回礼,那是几勺磨得极细的褐色粉末,拿回家用热水一冲,就是当时上流社会最推崇的木乃伊茶。
这并不是什么荒诞的哥特小说,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欧洲日常。
我们总习惯把食人跟蛮荒、落后划等号,脑子里全是那些脸上涂着白漆的土著在火堆旁乱跳。
欧洲人呢,他们觉得自己是启蒙运动的骄傲,是理性、法律和文明的代名词。
可翻开历史那层厚重的遮羞布,你会发现这帮文明人吃起同类来,不论是规模还是花样,都让亚马逊的猎头族望尘莫及。
这种胃口甚至能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在现在的北欧和西欧,马格德林文化的人们就有一种特殊的葬礼,他们会把亲人的肉细心地剔下来吃掉。
这不是因为没粮食,而是一种极致的爱。
骨头被留了下来,头盖骨磨成了光滑的杯子,盛水或者盛汤,这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把亲人带在身上。
基因显示,这种习俗像种子一样随着迁徙散播到了整个欧洲,甚至到了中东欧。
这种仪式性的食人消失后,填肚子式和吓唬人式的下嘴方式很快就接了班。
11世纪的十字军在叙利亚打仗,饿极了的士兵直接在营火上烤起了战俘。
上级其实心里清楚,但他们选择沉默。
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你开始吃人,敌军在听到你名字的时候甚至会直接丢下武器逃跑。
恐惧比刀剑更有用,文明人在这一刻发现,恶魔的形象其实是最好用的盔甲。
到了大航海时代,这种双标被发挥到了极致。
哥伦布在日记里发明了食人族这个词,用来描述加勒比海那些他从未见过的土著。
欧洲人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大喊着那些人是低等野蛮人,我们要去拯救他们的灵魂。
可就在他们怀揣圣经、手握钢刀踏上新大陆的时候,欧洲本土的药剂店里正摆着整排的人骨粉。
16世纪的欧洲医生们坚信,人体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古希腊的医学理论被他们奉为圭臬,角斗士的鲜血能治癫痫,那现在处决犯人的血自然也能治病。
意大利的牧师菲奇诺甚至给老人开了个方子,让他们去吸青少年的血,说是能返老还童。
对人选的要求还特别高,得是那种干净、快乐、节制的年轻人。
鲜血不好保存,那就加工成人血膏。
找个身体壮实的倒霉蛋,放出血,加温熬到黏稠,切成薄片晾干,再用青铜臼捣成碎末封进玻璃瓶。
每年春天,欧洲各地的药铺都要忙着制作这种新鲜的补药。
这种对人体组织的迷恋,让红楼梦里那些复杂的药方都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人油也是抢手货。
16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营养不良,胖子被看作是福气的象征,他们身上的脂肪自然也是圣物。
荷兰的军医在战场上冲锋,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在战后第一时间割取阵亡士兵的脂肪。
他们把这些油敷在伤口上,觉得那是残留的生命力在发挥作用。
头骨则是另一种硬通货。
17世纪的英国医生发明了一种从头骨里蒸馏出来的烈酒,声称能治愈从痛风到瘟疫的一切毛病。
英王查理二世花了大价钱买下配方,人称国王的药水。
后来这方子传到了民间,大家往葡萄酒里兑,往巧克力里掺。
最讲究的得是那种长了绿毛的头骨,这种头骨苔藓被认为药效更猛。
这种全民参与的食人盛宴,在木乃伊生意面前都只能算小打小闹。
这事儿起初是个翻译乌龙,波斯语里的沥青叫姆米亚,本是入药的好东西。
结果传到欧洲,大家一看木乃伊身上那层黑乎乎的东西,就以为这就是姆米亚。
逻辑很快就闭环了,千年不腐的古尸肯定含有什么神药。
从11世纪开始,埃及的古墓就被欧洲人挖了个底朝天。
成船的木乃伊被运往欧洲,批发给药剂师。
需求量太大了,大到埃及那边的坟头都快被刨平了。
为了不断货,欧洲人开始自己动手。
他们从绞刑架上偷走死刑犯,用盐腌,用药浸,最后塞进烤箱烘干,做旧之后当成纯正的埃及木乃伊卖。
这种买卖一直火到了维多利亚时期。
除了吃,木乃伊还能拿来画画。
画家们最爱的木乃伊棕,就是用真的干尸粉末调出来的。
当你看着名画里那种深邃、沉稳的褐色调时,很难想象那是无数破碎的灵魂在画布上凝固。
这一切听起来荒诞,却又真实得让人脊背发凉。
为什么德古拉伯爵要吸血,为什么丧尸片里的怪物总在撕咬文明人,这些恐怖的想象其实都是欧洲人对自己历史阴影的投射。
当人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审视别人的时候,往往忘了自己嘴边还挂着没擦干的血。
历史一再证明,当一个群体认定自己拥有绝对文明的时候,往往是他们最不把别人当人的时刻。
2013年英国那场关于食人的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在午餐时间看着盘子里的烤鸡互相调侃。
但这种幽默感其实很脆弱,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条件允许,文明的底线可以在一夜之间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