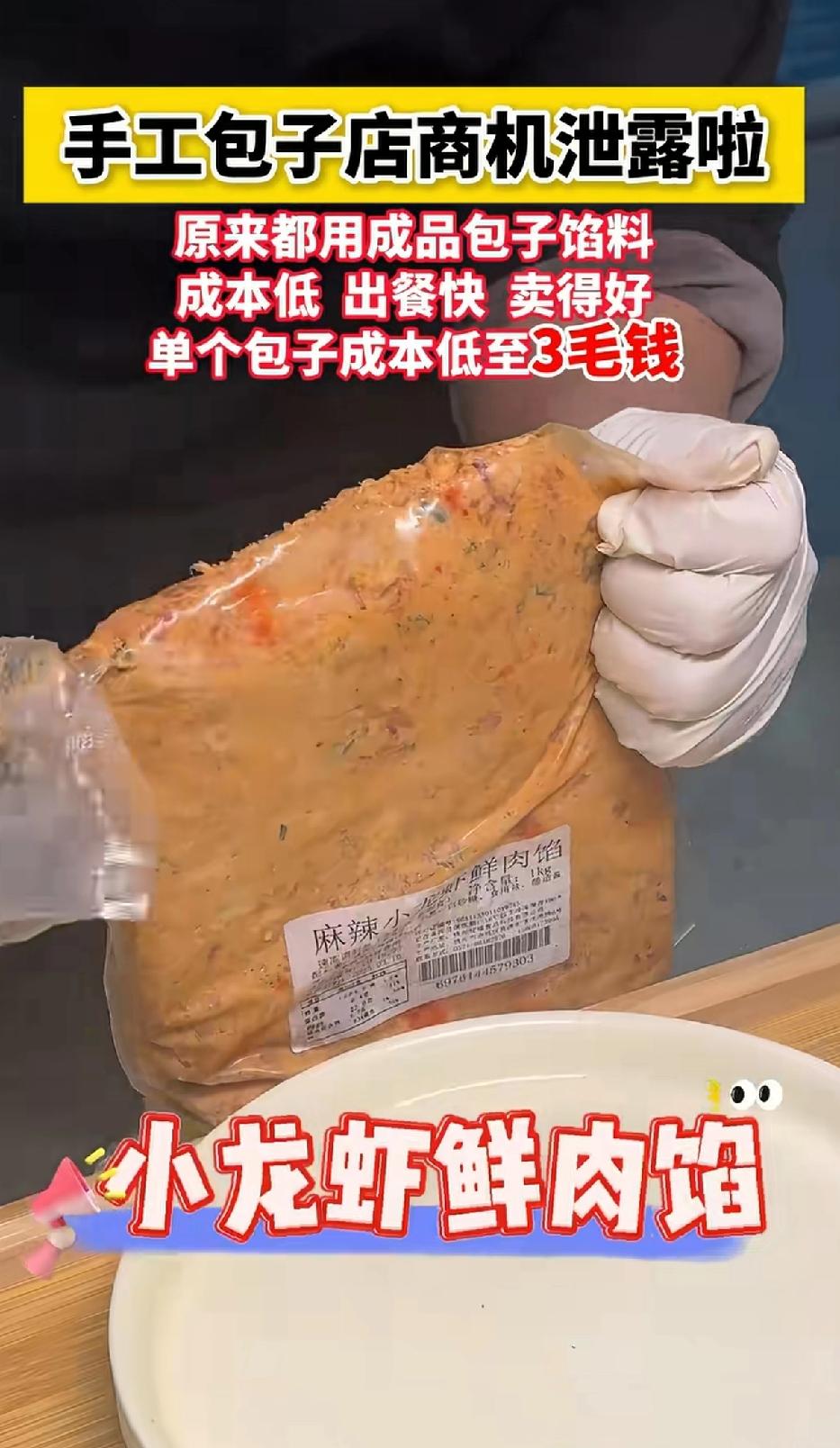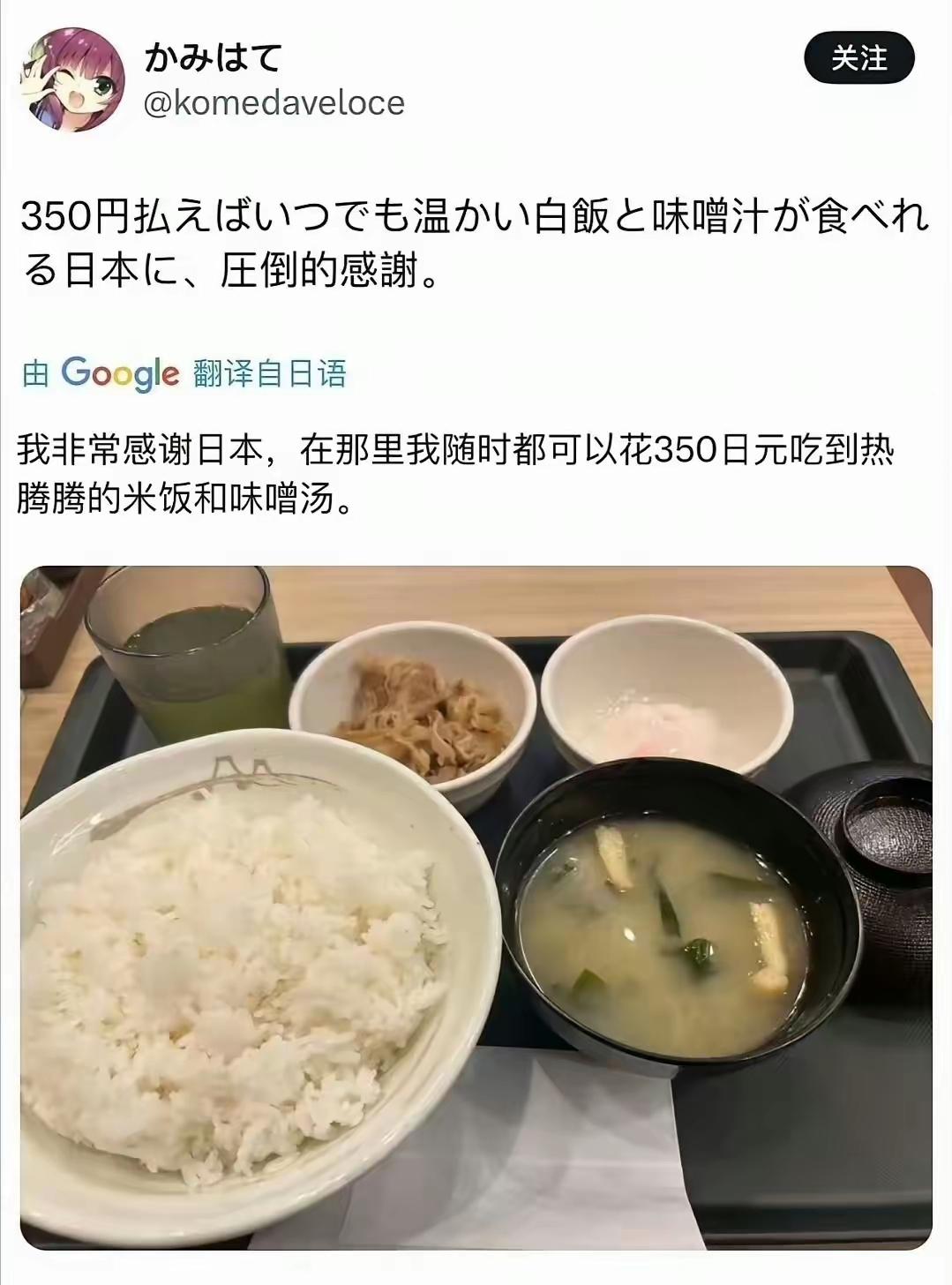1977年冬,谢炳义在胡同口买了两碗炸酱面。一碗自己吃,一碗递给蜷在垃圾箱边的哑女。她不说话,只用袖子擦碗沿,吃得很快。 那会儿知青刚返城,工作没着落,户口卡在乡下,连街道办盖个章都得托人。谢炳义腿瘸,成分不好,自己也是“半个黑户”,可他还是把人领回了家。邻居说“捡了个媳妇”,他没否认,也没承认。 十年里她叫小莲,带孩子、纳鞋底、冬天烧热水给谢母泡脚。没人查她身份证,也没人问她原名叫啥。直到1987年有人踹开谢家门,掏出一本红结婚证,说她是赵大柱的老婆。 警察来那天,她第一次张嘴,没出声,但指着自己脖子上的疤,又指指来人。法医后来写了报告,七道旧伤,最深一道在锁骨下。 谢炳义没打人,就塞了一千块钱给赵大柱,让他去办女儿的抚养手续。钱是卖了家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凑的。 最后她留在谢家,没改名,也没要新户口本。只是某天清晨,自己端着面碗坐到院门口,慢慢吃完了。 面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