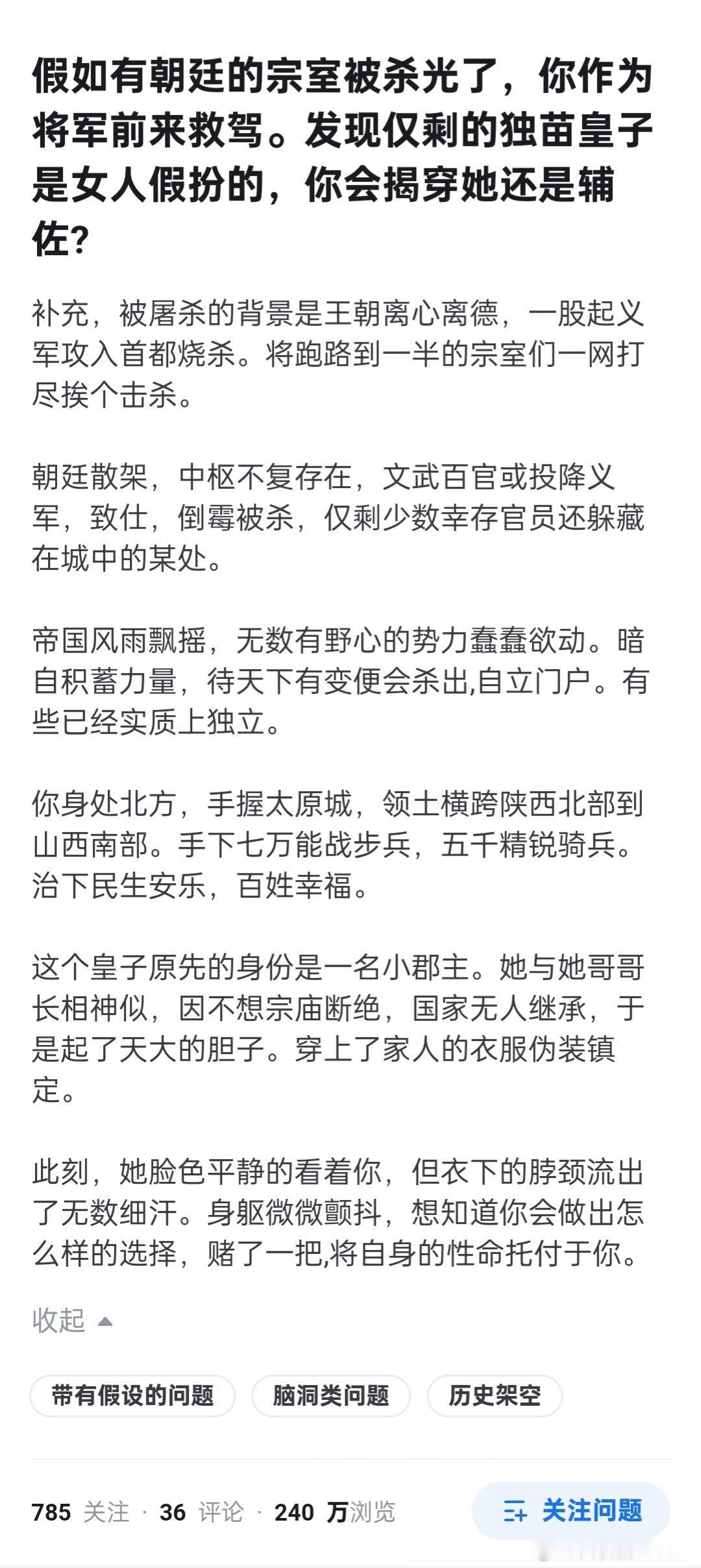前295年,赵武灵王在行宫被困整整三个月。粮食吃尽了,就爬上树掏雀雏,雀雏没了,就剥树皮啃。树皮吃完了就喝地上的脏水,没过几天,一代英主赵武灵王活活饿死在行宫。 战国中期的历史天幕上,赵武灵王赵雍,是一颗骤然爆发又遽然陨落的流星。 赵雍的起点并不平坦。 少年即位时,父亲赵肃侯新丧,魏、楚、秦、燕、齐五国各怀鬼胎,以吊唁为名,各带精兵,陈于边境,虎视眈眈,意图趁赵国主少国疑之际攫取利益。 年少的赵雍在重臣肥义辅佐下,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果决。 他并未退缩,而是针锋相对,全国戒严,外交上软硬兼施,军事上严阵以待,硬是逼退了五国联军,稳住了摇摇欲坠的江山。 这场危机公关的胜利,预示了他绝非庸碌守成之君。 此后,他的目光始终投向更远的疆场。 他敏锐地看到传统车战与宽袍博带的弊端,力排众议,坚决推行“胡服骑射”。 改革成效立竿见影,赵国军队机动性与战斗力大增,北驱林胡、楼烦,西略胡地,并最终吞并了心腹之患中山国,国土大幅扩张,成为关东六国中军事最强的存在。 此时的他,志得意满,甚至谋划着更宏大的蓝图,他曾伪装成使者亲自入秦,勘察地形,梦想着从北路云中、九原南下,直插秦国心脏咸阳。 或许正是这过于膨胀的雄心,催生了他那惊世骇俗又隐患无穷的决定。 公元前299年,正值四十六岁盛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宣布将王位内禅给年仅十一岁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而自己则退居二线,称“主父”。 他的设想看似完美,让儿子处理繁杂的国内政务,自己则摆脱君王身份的束缚,专注于对外征伐,开疆拓土,实现赵国军政分离的“二元政治”。 然而,权力如同烙铁,一旦沾手便会留下印记,绝非可以随意脱下又穿上的外袍。 这一安排首先深深刺伤了长子赵章。 赵章本是嫡长子,早被立为太子,只因生母早逝,而赵雍后来专宠吴娃,爱屋及乌,便废长立幼,将太子之位给了吴娃所生的赵何。 赵章年长且孔武有力,颇有父亲之风,如今却要对年幼的弟弟俯首称臣,心中愤懑可想而知。 赵雍或许出于对长子的愧疚,在退位后,仍让赵章享受近乎国君的仪制。 这种暧昧的态度,无疑在赵章心中埋下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引起了赵何及其拥护者的不安。 时间的裂痕在沙丘宫化为决堤的洪水。 公元前295年,赵雍携两个儿子同游沙丘宫,三人分宫而居。 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赵章与其相田不礼认为时机已到,假传“主父”之命,欲召赵何前来加以谋害。 赵何的相国肥义忠勇,为防不测先行前往,果然被杀。 事变随即演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 赵何的军队在公子成与李兑的率领下迅速反击,击败赵章一党。 走投无路的赵章逃向父亲居住的西宫,寻求最后的庇护。 这是赵雍一生中最为糊涂也最为致命的一刻。 出于复杂的情感,或许是残存的父爱,或许是对长子的补偿心理,或许是对自身权威的盲目自信,他竟然打开了宫门,将逆子藏于宫内。 这个举动,彻底将他从仲裁者变成了“同谋”,公子成与李兑的军队随即包围了西宫。 他们名义上的理由是追捕叛贼赵章,但谁都清楚,主父庇护逆子,已成法理上的共犯。 更关键的是,经此一役,赵雍与赵何父子间的信任已彻底破产。 无论是赵何,还是公子成、李兑等平叛功臣,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一旦主父安然出宫,追究起围宫之罪,或者因赵章之死而报复,所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一场心照不宣、冷酷至极的集体谋杀,在沉默中上演。 他们选择了最残忍,也最能撇清干系的方式,围而不攻,断其生机。 宫门被紧紧锁住,粮道被彻底切断。 起初,宫中人或许还能靠存粮度日,接着是搜寻一切可食之物,再后来,树上的雏鸟、新生的鸟蛋成了珍馐,树皮被剥食殆尽,最后,只能饮用地面积存的污水。 被围困的三个月,是赵雍生命最后的炼狱。 这位曾骑马纵横草原、令诸侯侧目的一代雄主,在宫墙之内,尊严与生命被一寸寸剥夺。 所有的丰功伟绩,所有的雄心壮志,在生存的本能面前都显得苍白可笑。 最终,他在极度的衰弱与痛苦中,结束了自己传奇而又悲惨的一生。 直到确认他死亡,宫门才被打开,赵何闻讯,“哭之甚哀”,并以国君之礼安葬了父亲。 这哀哭之中,有多少真情,又有多少是政治表演,已无人能知。 主要信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