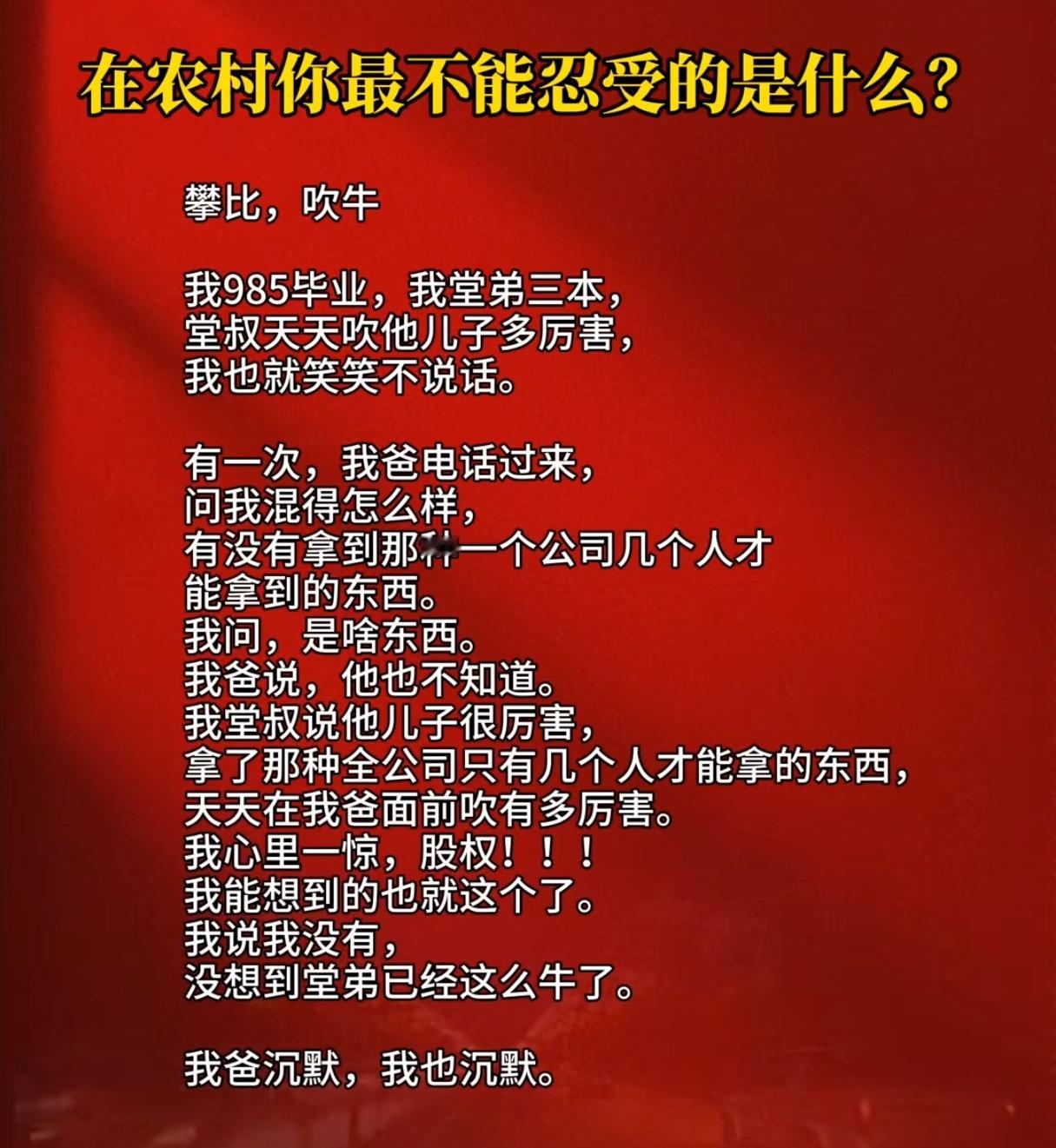这是九十年代曾志来到农村看望自己的长子石来发。此时,石来发早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当他初次看到几十年未见的母亲时感觉不到母子之间的亲情,而更多的是母子之间的陌生感。 那天的太阳晒得人发晕,石来发正在田埂上修水渠,裤脚卷到膝盖,小腿上沾着湿泥。村支书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有北京来的客人找他,还说是他亲妈。石来发愣了半天,手里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跟着支书往家走,一路上脑子里乱哄哄的——他记得八岁那年,母亲把他托付给村里的石匠,说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让他别怪她。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 推开家门,一个穿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女人站在堂屋中间,手里提着个布包。石来发站在门口,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女人走过来,声音有点抖:“来发,我是妈妈。”石来发张了张嘴,没喊出“妈”,只是闷声问:“你……你回来干啥?”曾志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双新布鞋,还有一沓钱:“我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东西。”石来发接过布鞋,摸了摸鞋底的针脚,说:“我穿这个就行,不用破费。” 石来发的童年是在石匠家过的。养父是个老实人,靠打石头为生,养母身体不好,经常咳血。他从小就帮着干活,割猪草、挑水、喂牛,十岁就会下地插秧。有次他问养母:“我亲妈呢?”养母叹口气:“她在城里当大官,忙得很,没空管你。”他信了,可心里总像缺了块什么。长大以后,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从没抱怨过。 曾志在村里住了三天。她跟着石来发去地里干活,看他弯着腰割稻子,汗水顺着下巴滴在泥土里;她去厨房帮他媳妇做饭,尝了尝锅里的红薯粥,说“比我在延安吃的还香”;她还去了石来发的老房子,摸着他小时候睡过的木板床,说“那时候你瘦得像只小猫”。可石来发还是不怎么说话,他不知道该跟这个“大官”母亲说什么——他没读过书,不会讲大道理,只会说“今天天气好”“稻子长得好”。 临走那天,曾志把一沓钱塞进石来发手里:“你养父母不在了,这钱你留着给孩子们读书。”石来发把钱推回去:“我有手有脚,能挣钱,不用你管。”曾志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我不是要管你,就是想帮你一把。”石来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常回来看看不?”曾志点点头:“有机会,我一定来。” 后来,石来发听说母亲在北京当了大干部,可他没觉得骄傲。他觉得,自己当农民也挺好,至少能守着土地,守着孩子。有次他去县城卖菜,听人说“曾志是老革命,为党做了很多事”,他才明白,母亲不是不要他,是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可这份明白,来得太晚了——等他真正懂的时候,母亲已经老了,再也没力气来农村看他。 2000年,曾志去世的消息传到村里。石来发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旱烟。他想起母亲走的那天,说“来发,妈对不起你”,想起母亲给他做的布鞋,想起母亲尝他家红薯粥时的笑容。他摸了摸身边的老黄狗,说:“妈,你放心吧,孩子们都长大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现在,石来发的孙子考上了大学,在省城当老师。他常跟孙子说:“你太奶奶是个好人,就是没时间陪我。”孙子说:“爷爷,你别难过,太奶奶的心里肯定有你。”石来发笑了,摸了摸孙子的头,没说话。他心里明白,有些感情,不需要挂在嘴上,只要记在心里,就够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