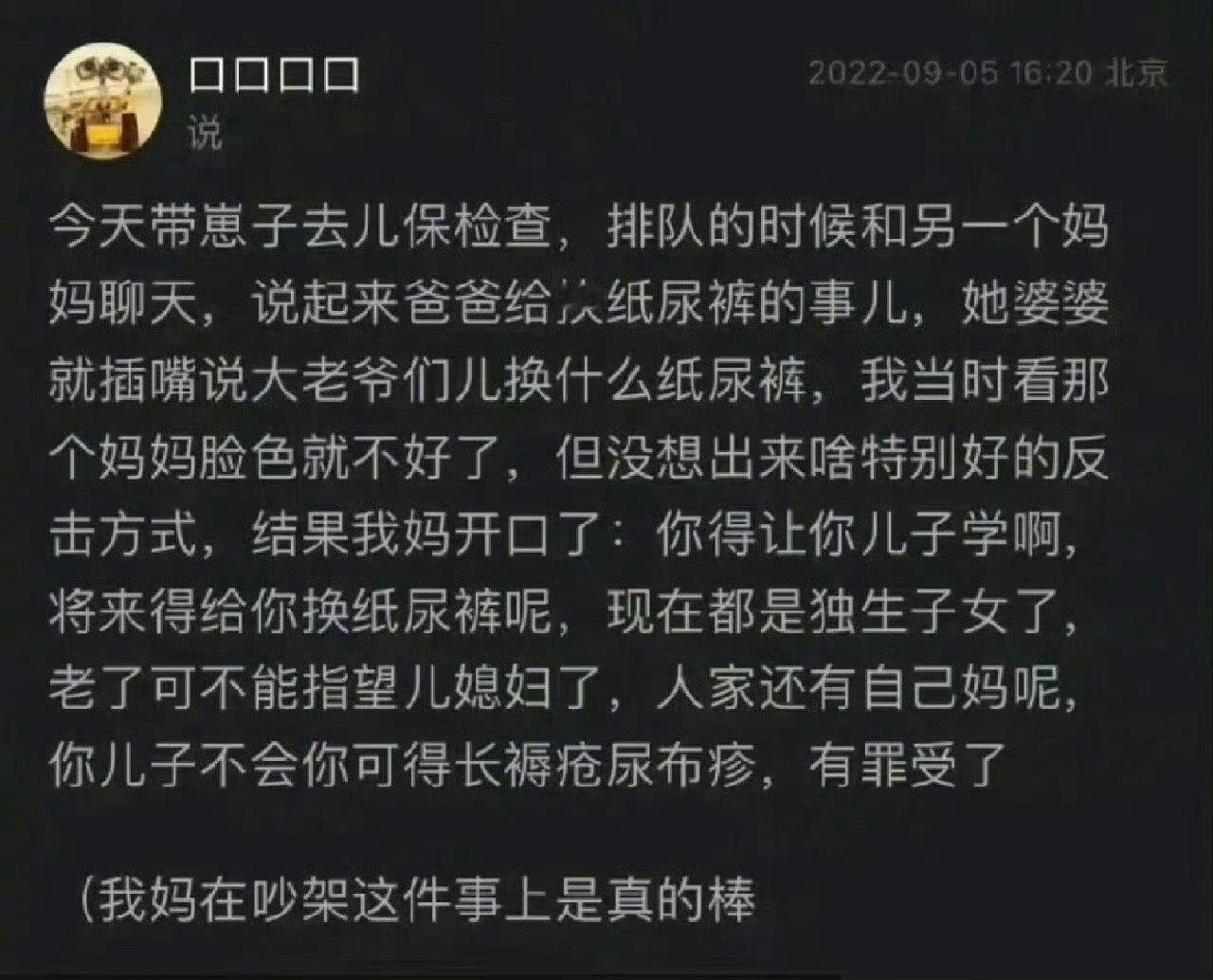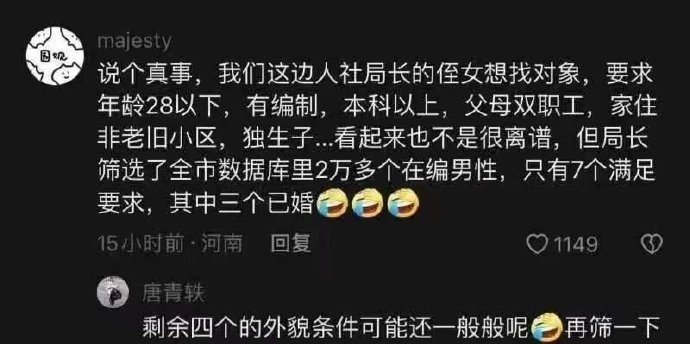大哥伸手摸了一下她光着的脚,问:妹子,这天儿,不冷吗? 就这一句话,比他献的那束花,暖和一万倍。 她是在农村跑演出的草台班子演员,大冬天,露天舞台,穿得跟个仙女似的单薄。 观众里三层外三层裹着棉袄。 她脸上笑着,估计脚早就冻麻了。 要是换个小姑娘,被人这么一问一碰,可能就恼了,觉得是冒犯。 但她没有。 她特别平静地、甚至有点感激地,跟大哥握了握手,说了句:习惯了。 习惯了。 我天,就这三个字,一下子就把我干沉默了。 这里头包含了多少东西? 多少个为了碎银几两,在寒风里咬着牙的日日夜夜? 多少次想喊“我太难了”,最后又咽回肚子里的心酸? “习惯了”,不是认命,也不是麻木。 它是一种最硬核的专业主义,是一种成年人不对生活示弱的最后体面。 说白了,她不是感觉不到冷,只是心里头有团火,必须燃着。 那火,叫“要生活”。 那一刻,大哥问的是身体的温度。 而她回答的,是生活的刻度。

![好家伙,这也是个较真的主[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6858695632556883682.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