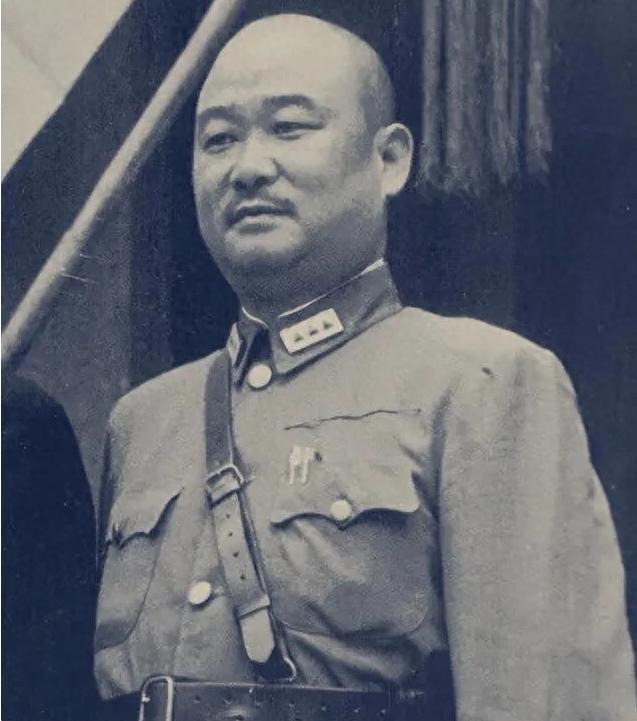顾祝同当师长时,一个连的两排士兵哗变,连长李志超当晚和几个军官打牌,竟然一无所知。旅长带人将李志超押到顾祝同面前,要求将其枪决以正军法。 屋里那盏煤油灯晃得厉害,火苗在李志超苍白的脸上跳个不停。旅长站在旁边,胸口一起一伏的,腰带勒得紧,仿佛一松劲整个人就要炸开。“师座,这种混账东西留着干什么?底下两排人都跑光了,他还在牌桌上摸幺鸡!不毙了他,这队伍往后怎么带?” 李志超被反绑着跪在地上,军装领子扯歪了,嘴唇干裂起皮。他抬头看了眼顾祝同,喉咙里咕噜一声,到底没说出话来。旁边几个参谋眼神碰了碰,又都移开了,这事太烫手,谁也不敢先开口。 顾祝同没接旅长的话茬。他绕过桌子走到李志超跟前,蹲下了。这个动作让屋里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李连长,”他的声音不高,平平静静的,“昨晚输了多少?” 这话问得突兀,李志超懵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二、二十块大洋……” “输得连哨兵换岗都听不见了?”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灯芯爆开的噼啪声。顾祝同站起身,从桌上摸起个搪瓷缸子,慢慢喝了口水。那年月军队里乱,当兵的吃不饱穿不暖,半夜拖枪跑路不是新鲜事。可整整两排人悄没声儿地没了,带头的居然在牌桌上浑然不觉,这事儿传出去,整个师的脸面都得丢光。 旅长又往前踏了一步:“师座!军法十七条明明白白写着……” “我知道写的什么。”顾祝同把缸子搁回桌上,搪瓷碰木头的声响闷闷的。他转过身看着墙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旗子边角已经磨得起毛了。“民国十六年我在蚌埠带兵,手下也有个连长,因为克扣伙食费被士兵绑在树上打。后来怎么着?我罚他挑了三个月大粪,挑完了照样当连长。” 这话说得轻,落在屋子里却有分量。参谋堆里有人轻轻“啊”了一声。那年顾祝同还没当师长,带的是个独立团,闹饷的兵差点把营区掀了。后来他没杀一个人,硬是把事情按了下去,这故事在嫡系军官里传过,真真假假的,今天倒是头回听他亲口提起。 “可这回不一样!”旅长急得额头上青筋都出来了,“这是哗变!是携械潜逃!按律当斩!” 顾祝同终于转过脸来。煤油灯的光从他侧后方照过来,半边脸在暗影里,看不太清表情。“王旅长,你说要正军法。那我问你——那两排兵为什么跑?是因为李连长打牌,还是因为三个月没发饷?是因为长官吃空额,还是因为伤兵躺着等死没人管?” 一连串问题砸下来,旅长张了张嘴,没接上话。 屋子里更静了。窗户外头传来巡逻队换岗的口令声,短促,僵硬,像刀切在冻肉上。那时候的军队就这样,上头拨下来的饷银经过层层盘剥,到当兵的手里能剩几个铜板都是造化。当官的各有各的财路,吃空饷的、倒卖军需的、甚至还有和地方烟馆勾着的,这些事大家心照不宣,可从来没人敢在师部里这么摊开来说。 李志超忽然哭出声来,不是嚎啕,是那种压抑着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他额头抵着地面,肩膀抖得厉害。“师座……我家里老娘病了,等着钱抓药……昨晚那几个,他们说有一局快钱……我糊涂,我该死……” 顾祝同走回桌后坐下,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敲着。一下,两下,三下。敲到第七下的时候,他开口了:“李志超玩忽职守,撤去连长职务,编入敢死队。若能活着完成三次突击任务,准予戴罪复职。”顿了顿,又补上一句,“这个月全师军官的新饷,扣三成补发给士兵。从我开始扣。” 旅长眼睛瞪得滚圆:“师座!这……这不合规矩!” “规矩?”顾祝同忽然笑了,笑得有些涩,“要是规矩管用,那两个排的兵会跑吗?”他摆摆手,不想再争,“去查查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传话下去,愿意回来的,既往不咎。不愿意的……把枪留下,让他们走吧。” 后来有人私下议论,说顾祝同这手太软,带兵不狠镇不住场面。也有人说他是老狐狸,那年头当师长的,哪个手上没几张牌?杀个连长容易,可杀了之后呢?欠饷的事儿能解决吗?吃空额的人会收手吗?倒不如拿个人情,既稳了底下士兵的心,又在军官堆里立了个“体恤”的名声。 不过这话也没全说对。那个李志超后来真进了敢死队,据说在淞沪会战时抱着炸药包炸过日军碉堡,居然三次都没死成。民国三十年在湖北再见顾祝同,已经是个瘸着腿的营副了。这是后话。 乱世带兵,有时候军法这把刀太利,砍下去痛快,却未必能斩断乱麻。顾祝同那晚没杀李志超,或许不是心软,是看得明白,枪毙一个失职的连长容易,可那两排士兵卷走的,又何止是几十条枪呢?那是人心,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军队最后一点体面。留个活口,给条生路,有时候比一纸枪决令更难,却也更有分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