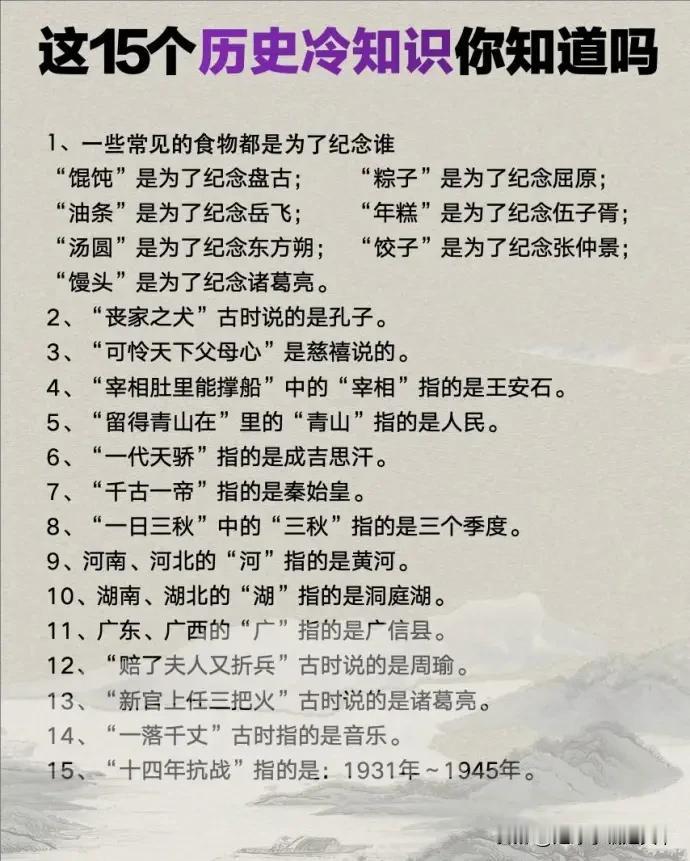西藏到底有多富?上世纪五十年代,军队刚进去的时候,那些头人不卖粮,喊穷,想困死大军。但实质上,头人的粮仓中,青稞太多放得太久,已经碳化不适宜人吃了,数以百吨千吨计,连做饲料几乎都不行了。当然,这不影响成千上万农奴饥寒交迫。 在那片空气稀薄的高原上,曾经存在过一种极其荒谬的物质形态——“黑石头”。它们并不是矿产,而是几十年前被遗忘在贵族庄园深处的青稞。 当你把这种东西放在手里一捻,这些坚硬的硬块瞬间就会化作黑灰色的粉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西藏,这种已经完全碳化、连牲口都没法吃的陈年粮食,以数以百吨、千吨的体量,拥挤在头人老爷们那些不知多少年没打开过的粮仓角落里。而与此同时,仅一墙之隔,无数衣衫褴褛的身影正在为了哪怕一碗野菜麸皮糊糊而拼尽最后一点力气。 这就是当时的魔幻现实:一边是粮食多到烂在地窖里化成灰,另一边是活生生的人饿得前胸贴后背。 当年那支头顶着积满灰尘红星的队伍刚踏入这片土地时,遇到的最大敌人根本不是严酷的天气,而是这种令人窒息的“人为饥荒”。队伍里的年轻战士大都来自内地,长途跋涉翻过雪山,行囊里的干粮早就见了底。甚至在还能看得见布达拉宫的地方,许多战士的干粮袋倒过来晃荡,只能听见空荡荡的风声。按照“不吃地方、不拿群众”的死命令,他们把拌着雪水的青稞面当成了仅有的热量来源,而哪怕这样简陋的补给,也即将断绝。 市面上原本该有的烟火气,仿佛在一夜之间被人为地掐灭了。街道变得空荡荡,偶尔有带着沉重头饰的贵族经过,也是眼神闪躲,那是对某种无形压力的恐惧。商铺关门,小贩摇头,整个拉萨似乎都在执行一道无声的“封锁令”。在那些紧闭大门的深宅大院里,像是那个叫做鲁康娃的代理司曹之流,正在算盘上拨弄着恶毒的计谋:既然枪炮挡不住,那就用饿肚子让这群外来者低头。 这种对峙显得格外残酷。战士们脸庞被紫外线晒得漆黑,身形瘦削脱了相,为了严守纪律宁愿忍饥挨饿;而在这座城市的暗处,那些掌握着权势的旧贵族却锦衣玉食,任由仓库里的粮食发霉变黑也不肯流出一粒。 在他们的逻辑里,粮食、土地和那成千上万弯着腰的农奴,都只是彰显权力的私产。对于像扎西这样十几岁的小农奴来说,世界是绝望的。他的父母仅仅因为交不上高达七成的租子就被活活打死,他自己也要裹着破羊皮缩在牛棚里,稍微干活慢点就会招来鞭笞。 在这些农奴眼里,那一堵堵高墙内的粮仓比天上的星星还要遥远。那些真正种粮食的人,吃着混杂草根的稀粥,甚至肚子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而鼓胀;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宁愿把粮食屯成这一文不值的“黑石头”,也要把这当作政治博弈的筹码。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那堵墙都是铁板一块。有些见多识广的贵族商人在夜深人静时开始心里打鼓。他们看到了这支队伍的坚韧——这不是一群会因为饥饿就劫掠的旧式军队,也不是一群能被轻易饿垮的人。如果在自家地盘上真把这几千人饿死,引发的后果恐怕谁也兜不住。 僵局最终还是被一丝务实的光亮打破了。如阿沛·阿旺晋美这样的爱国人士开始从中斡旋,在无数次的试探与商谈后,那种将死人困死的封锁终于松动。这不再是单纯的施舍,而是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平等买卖。有远见的寺庙和贵族开始以公道的全部价格“卖”出一部分库存,政府的粮仓也打开了缝隙。 更有生命力的场景出现在拉萨河畔。那是一种此前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的“反击”方式——不是用枪,而是用锄头。战士们勒紧了裤腰带,在这片从未有人耕种过的河滩荒地上开垦出了“八一农场”。当来自内地的菜种在稀薄的空气中顽强地冒出绿油油的嫩芽时,一种新的生存逻辑在这片高原扎下了根:尊严不是靠囤积和压迫得来的,而是靠双手从土里刨出来的。 与此同时,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路上,甚至尚未完全通车的川藏线上,驮着粮食的牦牛队和汽车正如血脉般重新联通。那些曾经试图把人困死在高原孤岛上的算计,彻底落了空。 如今回头再看,那些腐烂碳化的青稞简直就是旧时代最讽刺的墓志铭。它们见证了一个荒唐年代的终结:在那里,粮食的价值不是用来果腹,而是用来制造苦难。随着之后民主改革的大潮席卷而来,像扎西一样的农奴终于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用再担心劳作一年换来全是“黑石头”般的霉烂陈粮。那些曾经只能跪着求一口饭吃的人,终于能挺直了腰板,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出真正能吃饱肚子的庄稼。这片土地上的贫富不再由出身和囤积决定,而是回归到了劳作与创造最原本的公平。 信源:中国教育新闻网——西藏农垦事业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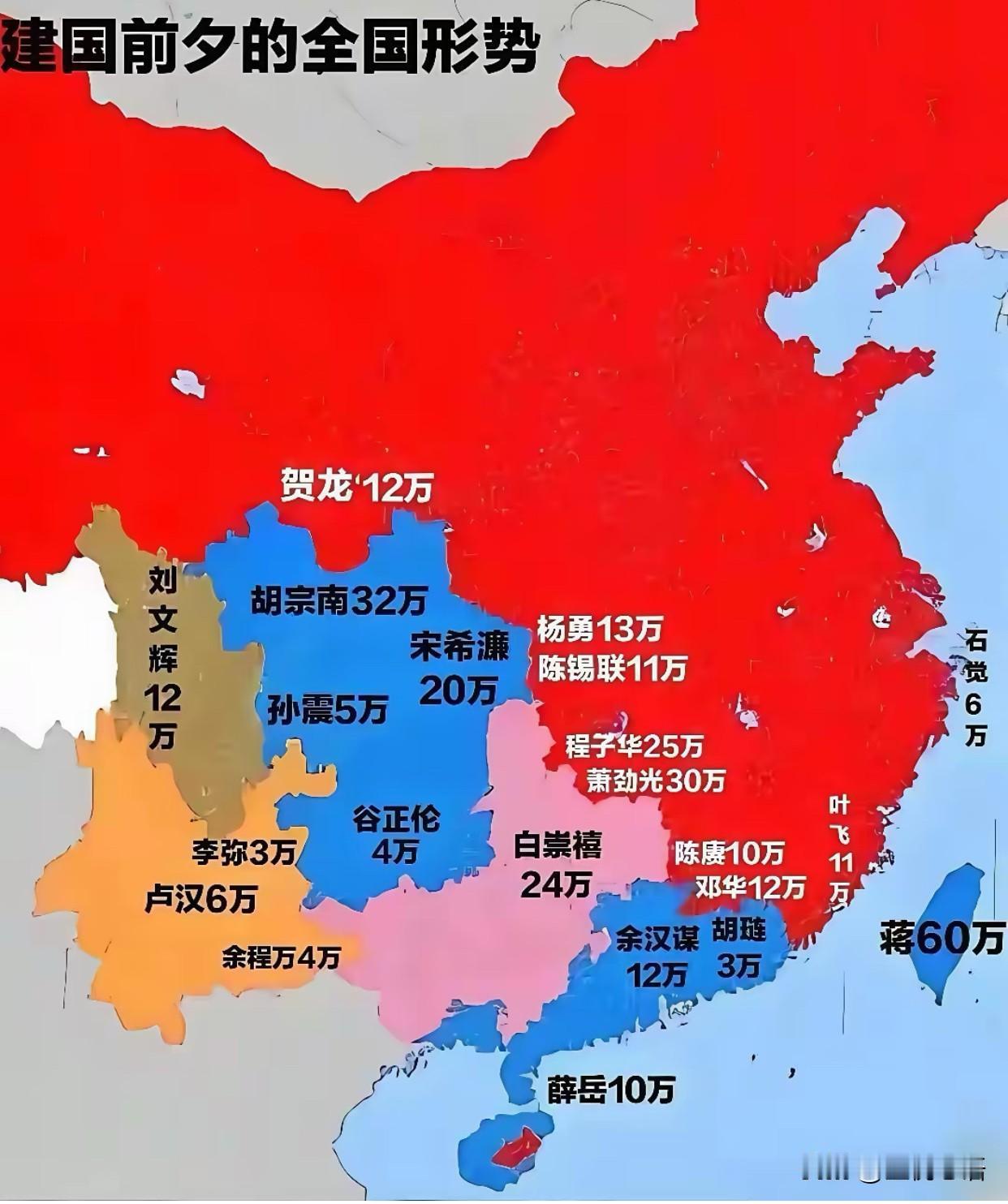

![我也算怪人哈,特别喜欢像辛弃疾啊、李清照啊这样的古人…[捂脸哭][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7115708612372983601.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