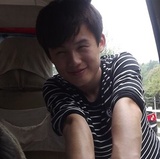1941年,一辆轿车开进重庆郊外。 车里,戴笠的秘书周志英,仔细补了补妆,镜子里映出的脸,写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她以为,车的终点,是她和戴笠的婚房。 车停了。车门一开,没有新郎,没有红毯,只有息烽监狱冰冷的铁栅栏和看守面无表情的脸。 她脸上的笑意,一点点僵住。 一切,要从六年前说起。1935年,浙江警官学校,刚毕业的周志英留校当事务员,年轻,漂亮。而戴笠,是学校的“政治特派员”,一个能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名字。 他以谈工作为名,把她一次次叫进办公室。办公室的门一关,公事就变成了“交个朋友”。在那个年代,这种“朋友”,就是一张收网的信号。 她没拒绝。她算得很清楚,这张网背后,是重庆半山别墅的夜晚,是经她手处理的、连蒋介石都要掂量再三的绝密文件。她以为,用青春和服从,能换来一个“戴夫人”的名分。 她开始在他耳边提,要一个名分。 戴笠只是摆摆手,“抗战时期,军统有家规,不准结婚。” 她信了。但耐心总会耗尽。一天晚上,她枕着他的手臂,用一种自以为是的撒娇口吻,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你要是不娶我,我就把你的名声全毁了!” 空气安静了。戴笠脸上没什么表情,甚至还笑了笑。 他没发火,反而一口答应,说要给她办一场秘密婚礼。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送她去“新房”的,不是戴笠,是他的另一个秘书。关上牢门的,也不是仆人,是冷冰冰的狱警。 两年后,1943年,她不知为何被放了出来。 所有人都以为她会远走高飞,找个地方销声匿迹。可她偏不。她重新打扮得漂漂亮亮,直接冲到戴笠的公馆门口,被卫兵拦下。 她不走,就站在门口,放声大哭。哭声传进公馆,也再次踩到了戴笠的底线。 他让人把她带了进去。 偌大的客厅里,面对她撕心裂肺的“一日夫妻百日恩”,戴笠一言不发,只是面无表情地抄起墙角的鸡毛帚,对着她死死抱住自己大腿的身子,一下,又一下,皮鞋的闷响混着鸡毛掸子抽在皮肉上的脆声,在空旷的屋子里来回弹。 她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不松手。在她扭曲的认知里,打,也算一种纠缠。 最后,两个卫兵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她从戴笠的腿上掰下来,架着胳膊,直接扔回了那个她刚离开不久的地方。 这一次,医生来检查过,只留下一张纸条:“局座吩咐,不准刑讯。” 她攥着那张纸,咳得肺都要出来了,心里甚至还有一丝感激。她觉得,他还念着旧情。 直到1946年,戴笠的飞机在雨中化为一团焦炭。军统总务处长沈醉整理旧物时,才在一个发黄的卷宗里,翻出了“周志英”这个名字,顺手签了释放令。 她终于走了出来。但当年那个英文流利、心气高傲的女秘书,已经彻底被毁了。 她赌的是感情,可戴笠的牌桌上,从来就没有这个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