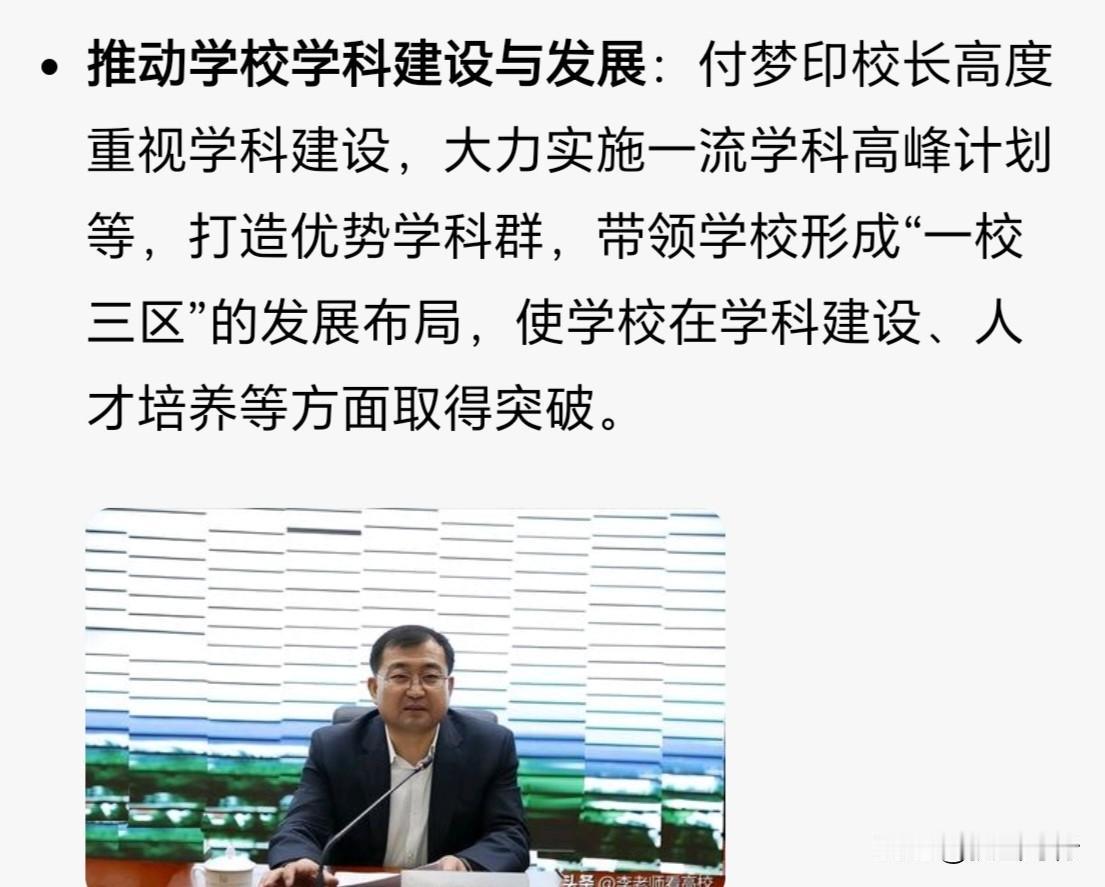困窘和脆弱被照亮,不必站在闪光灯下 ——记南京理工大学付梦印校长 [文|狐山诗行] 一个清贫学子的他,捧起了那碗汤,碧清的汤面上,几星油花,几缕蛋丝,淡得几乎看不见。他却喝得极认真,仿佛那不是一碗食堂里随取的、最普通的“神仙汤”,而是什么都需要细品的琼浆。然后,是那一大盘白米饭,顶上盖着一小撮最朴素的炒青菜。这便是他一天天的餐食了。他没有看见,几步之外,刚打好饭的老校长,目光在他身上停了许久,又移向窗口内相熟的打菜阿姨。阿姨会意地、极轻微地点了点头。空气里只有筷子偶尔碰到餐盘的轻响,一种巨大的、沉默的懂得,却在无声地传递。 创作训练营2期开营啦 后来,他回忆那个黄昏,总觉得像一场梦。指尖划过冰冷的刷卡机,屏幕上的数字,凭空多了四百元。没有通知,没有仪式,像一阵春夜里细密无声的雨,在他浑然不觉时,悄然润湿了他慌乱的心田。他连忙去找辅导员,年轻的老师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声音压得很低:“这是学校的一点心意,可安心用。” 就这么一句话。没有探究,没有追问,更没有让他把那些深夜里咀嚼过千万遍的、关于“困窘”的词汇,再当着谁的面掏出来晾晒。他转过身,食堂喧嚣的人声忽然退得很远,眼前只有那碗永远清澈的免费汤,汤里模糊地映出他自己的脸。他没忍住,泪就落了下来,咸的,滚烫的,砸碎在那片沉默的、保护了他全部骄傲的“心意”里。 翻开学校的论坛,那里沉睡着许多没有署名的月光。一个说,打饭的阿姨多给了一枚卤蛋,假装是手滑,他配合地假装没发现,走出几步,却觉得那蛋壳的热,烫到了心里。另一个写,每月总有那么几天,饭卡余额焦虑得让人失眠,可它总会在见底前,悄悄地“饱满”起来,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守护神,算准了他所有脆弱的时辰。那个安徽的男生,帖子写得最平静,他说爸爸的药瓶、妈妈的叹息、奶奶的期盼,是他大学时光最沉静的背景音。他最熟悉的,是一块钱的特价窗口。从某个月开始,守护神也准时叩响了他的门。他唯一能做的,是把每一次实验数据做得更准,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当作每日的收获。 他们没有被叫到台上,去背诵一份精心修饰过的“感恩”;没有在众目睽睽下,接过那封装着补助金的、仿佛烙着“特殊”二字的信封。他们的脆弱,没有被当作展示同情心的展品;他们的困境,没有被兑换成一场公开的“美德教育”。付梦印校长只是吩咐,用大数据那双洞悉一切却又无比矜持的眼睛,辨认出那些在生活困境的棱角上小心翼翼行走的灵魂,然后,默默地在他们必经的路上,铺下一层柔软的温暖的垫子。 这便是一种最高级的善良吧。它不是聚光灯下慷慨激昂的施与,而是暗夜中并肩而行的提灯。它不说“我懂你的苦”,它只是让你的苦,不必再成为需要言说的额外负担。它保护那在贫困中愈发显得金贵的、年轻人的“气节”——那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而是在风雨中竭力挺直的脊梁。学校要培养的是扛鼎未来的栋梁,而栋梁之材,首先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土壤。 于是,爱便这样悄无声息地流转起来。那一笔笔不署名的捐款留言,是所有故事最好的见证:“母校没有揭开我的伤疤,却为我包扎了伤口。” 当年那个喝着免费汤的年轻人,后来把工资寄给了山里的孩子;那个计算着一日餐费的学子,将智慧用在了广袤乡野的振兴蓝图里。他们终将长成参天大树,而他们的根,曾深深吮吸过一份没有特意“放大”的养分。这份爱,教会他们的不是如何感恩戴德,而是如何将光与暖,同样不动声色地,传递给下一个在寒夜里前行的人。 南理工的食堂,秋日的阳光正烈,毫无偏私地洒在每个人的肩上。让学子想起那位已然荣休的付梦印校长。他离开时,是否也有目光在默默相送?那目光里,没有送别领导的喧哗,只有无数被他曾默默“看见”过的学子,在学子心里行着最庄重的注目礼。 南理工校园的梧桐大道上,年复一年,总有人怀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重担走来。但他们会知道,在这里,有一双温柔而有力的手,会接住学子的坠落,托起学子们飞翔——在困窘中无需开口的默契,校园已然接纳了所有的脆弱,并把它化成前行的风。 分享城市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