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是以歌颂工农兵为主题的,艺术水准也极高。那些遗老遗少、残余投节对样板戏恨之入骨,不足为奇了! 这话说得挺直白,感情色彩也浓。咱们今天聊这事儿,得先把手里的“帽子”——比如“遗老遗少”——暂时放一放,心平气和地看看这“样板戏”到底是个啥,为啥它像一块烧红的铁,几十年过去了,一碰还能溅起争论的火星。 说它“艺术水准极高”,确实有道理。咱们就拿最熟的几部来说,《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那是真下功夫。唱腔上,它把传统京剧的皮黄体系,跟现代交响乐、合唱队揉在一块儿,既有老韵味,又有新气势。你听李铁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那板眼、那劲头,是精心设计过的,感染力很强。舞台上,灯光、布景、服装,都摆脱了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写意,追求逼真恢弘的视觉效果。更关键的是,它把工农兵、革命者推上了绝对的主角位置,形象高大,斗志昂扬,这在以前的戏曲里是少见的。从专业角度看,它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戏曲程式化表演体系进行现代化、精致化改造的极致尝试,说它是“艺术品”,技术上站得住脚。 那为什么总有人,未必都是“遗老遗少”,对它感觉复杂甚至反感呢?原因恐怕不止“阶级立场”那么简单。关键在于,样板戏不是单纯的文艺作品,它是在一个特殊年代里,被推上“样板”位置的政治文化符号。问题就出在“样板”这两个字上。所谓“样板”,就意味着唯一,意味着标准,意味着除此之外,别的花花草草最好别长。那十年里,全国上下,八亿人民,翻来覆去主要就这八部戏,所有的舞台、广播、电影都被它们占满。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化垄断。你喜不喜欢,接不接受,几乎没有选择。这种强制性的、排他性的普及,本身就带来了一种审美上的压迫感和疲劳感。人们反感的,或许不完全是戏本身,更是那种“只能看这个”的文化窒息状态。 再往深里说,样板戏塑造的英雄人物和世界观,是高度提纯、非黑即白的。敌人必定凶残愚蠢,我方必然英勇万能,矛盾尖锐,结局光明。这种艺术手法,在特定时期能起到强大的鼓舞作用。但生活本身要复杂、灰色得多。当这种极度简化的叙事被树立为唯一的文艺标准时,它就挤压了表现人性复杂、命运曲折、生活琐碎的艺术空间。几千年的中国戏曲,有忠奸争斗,也有才子佳人;有家国大义,也有儿女情长。而样板戏的世界里,后者几乎消失了。有人说它“干净”也“单调”,有人觉得它“有力”也“干瘪”,这种艺术评价的分歧,远远超出了“进步”与“落后”的简单划线。 我父亲是个老票友,能哼全本《铡美案》,也对《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唱段津津乐道。他有过一句朴素的评价:“样板戏是好东西,打磨得精光水滑。可你不能让全中国的戏园子只准唱这个,这就好比天天让你吃红烧肉,手艺再好,也想着来盘青菜豆腐换换口。” 这话挺在理。人们对样板戏的复杂态度,一部分是艺术审美的天然多样性,另一部分,是对那段文化单一、万马齐喑的历史记忆的连带反应。 所以,今天我们再看样板戏,或许可以尝试一种“剥离”的视角。把它作为一项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高超工艺水准的“艺术工程”来欣赏和研究,承认其在戏曲现代化探索上的成就。同时也理解,它承载的沉重历史记忆和引发的争议,其根源在于艺术被绝对政治化、工具化后所带来的后果。这二者,其实可以分开看。 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应该容得下《贵妃醉酒》的婉转,也容得下《红灯记》的高亢;既可以回味《梁祝》的缠绵,也能欣赏“穿林海跨雪原”的豪迈。把某一种风格树为“样板”,本身可能就是对艺术多样性的一种伤害。当年恨它的人,未必恨艺术,或许只是恨那种不容分说的文化专制;今天赞它的人,也未必全赞同过去,可能只是珍惜其中凝聚的艺术匠心。 说到底,样板戏像一面特殊的镜子,照见的是一个时代极端的美学追求与政治激情。它的艺术价值,值得我们摘下有色眼镜去细看;它带来的历史教训,更值得我们放下简单褒贬去深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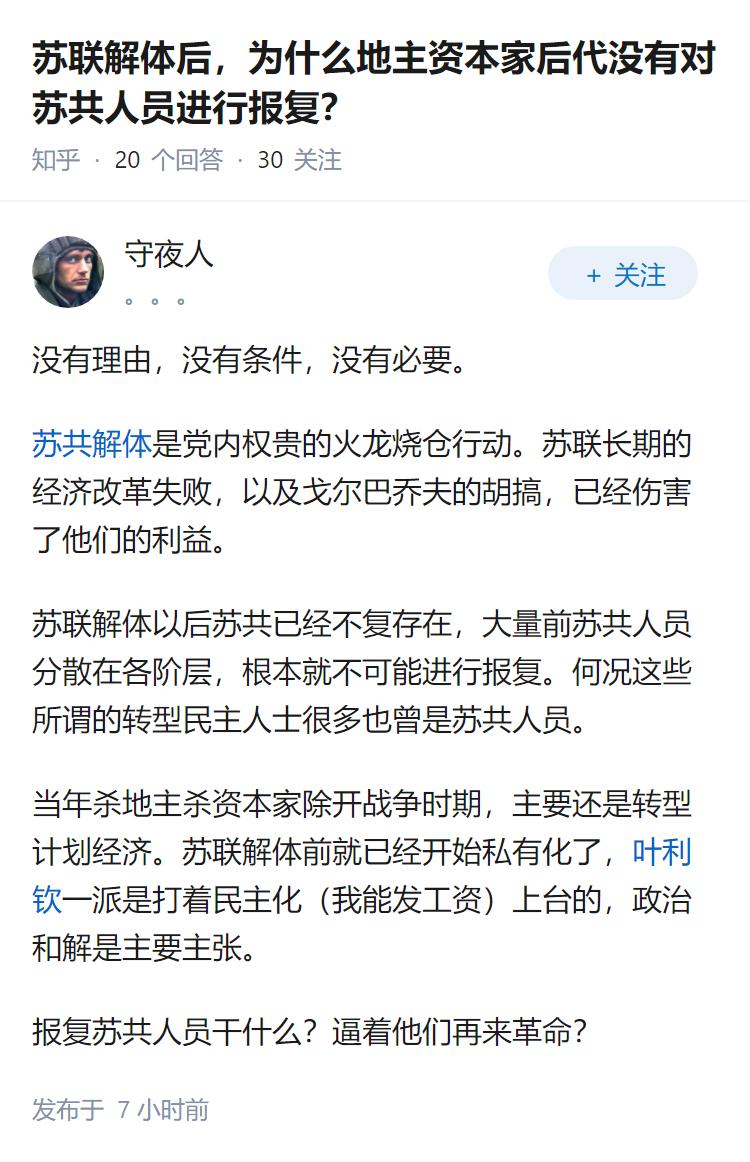





![这,居然是@冯琳…[比心]](http://image.uczzd.cn/1230813071137454452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