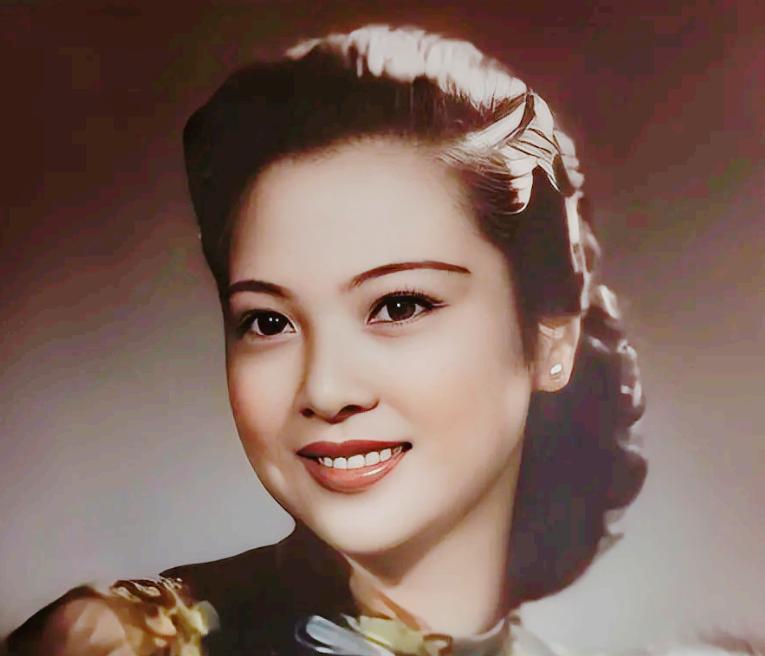1968年,知青朱启龙参军出发前夜,他的女友解开衣衫,誓言:“不论多久,都会等你回来!”不料,2年后,她等来的却是他已结婚的分手信。50年后,她上门做保姆时,又见到了他。 1968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北方的风像刀子一样,从土坯房的缝隙里钻进来。煤油灯摇摇晃晃,把墙上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朱启龙背着已经打好的行李,站在门口,手却迟迟没有去拉门闩。 那一晚,他就要随部队出发。 院子里静得出奇,连狗都不叫了。杨芳坐在炕沿,低着头,手指反复绞着衣角。她今年十九岁,扎着两根麻花辫,脸被寒风吹得微红,却始终没抬头看他。 “启龙……”她先开了口,声音发颤,“你这一走,是不是就回不来了?” 朱启龙心里一紧,却还是强笑:“胡说什么,当兵是光荣的事。” 可他们都知道,那是动荡的年代,战事、演习、边防,哪一样不危险。村里已经有人再没回来,只留下烈士证和一块木牌。 沉默了很久,杨芳忽然站起身,反手闩上门。她走到朱启龙面前,手指微微发抖,却一颗一颗解开了棉袄的扣子。 朱启龙愣住了,下意识后退一步:“你这是干啥?” 杨芳却抬起头,眼里全是泪,却倔强得很。 “你要上战场了,我怕你回不来。”她声音很轻,却一句比一句坚定,“今天,就当我们结婚了。不论你走多久,我都会等你。” 那一夜,没有誓言,也没有红烛。只有寒风、土炕和两颗惶恐却紧紧靠在一起的心。 第二天天还没亮,朱启龙就跟着队伍走了。杨芳站在村口,看着他一步步消失在晨雾里,直到眼睛再也看不清。 她等啊等。 头两年,还有信。信纸粗糙,字迹歪歪扭扭,说部队生活苦,说想家,说“你要照顾好自己”。 可两年后,她等来的,却是一封分手信。 信里只有短短几行字—— “我已经结婚了,你不要再等我,各自过日子吧。” 那天,杨芳把信攥在手里,站在院子里发了很久的呆。邻居来问,她也只是笑笑,说:“当兵的人,变了心,很正常。” 可那一晚,她第一次失声痛哭。 她不再等了。后来,经人介绍,她匆匆嫁人,日子却并不顺。丈夫脾气暴躁,生活清贫,孩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几十年下来,她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从不提当年的事。 她以为,那段感情,早就死在了1968年的冬夜。 直到五十年后。 那年,她已经六十九岁,为了补贴家用,经中介介绍,到城里一户人家当保姆。雇主说,男主人是位老兵,身体不便,需要人照顾。 开门那一刻,杨芳整个人僵在原地。 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头发花白,脸却熟悉得让她心口一紧。那双眼睛,她一眼就认了出来。 “启龙……”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朱启龙抬起头,看清她的脸,整个人猛地一震。轮椅轻轻晃了一下,他喉咙发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那时,杨芳才发现,他的双臂,从肩膀处齐齐截断,只剩下空荡荡的衣袖。 后来,她才知道真相。 原来那年战斗中,朱启龙为掩护战友,被炮弹炸伤,双臂当场失去。重伤后,他昏迷了很久,醒来时,已经成了残疾军人。 他不是结婚了。 那封分手信,是他咬着牙写的。他怕杨芳跟着他吃一辈子苦,怕她守着一个没有双臂的男人,被人指指点点。他宁愿她恨他,也不想拖累她。 “我这辈子,对不起你。”那天夜里,朱启龙终于说出了憋了半个世纪的话。 杨芳坐在他对面,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却一句责怪都没有。 五十年,太久了。久到他们都已白发苍苍,久到错过的人生再也无法重来。 可至少,真相没有再被埋进土里。 后来,杨芳没有离开。她继续照顾他,做饭、洗衣、推他晒太阳。邻居只当她是个普通保姆,却不知道,那是一个迟到了半生的“妻子”,在完成一场没有仪式、却贯穿一生的守候。 有些誓言,没写在纸上,却用一辈子来兑现。